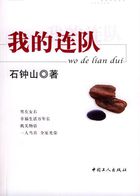泽旺邀请我们暑假到白玉县作客,说那儿的春天如同山外的阳春三月:“风儿是那么的柔:天空是那么的明净;朵朵红的、白的云与地上红的花、白的花默默相对,似在相互倾诉那许许多多不愿人知晓的什么秘密;站在山岗上,你可以领略到山外阳春三月也不曾有过的美妙,你还可以听到不远处寺院传来的袅袅钟声……”泽旺的这一番描述,的确勾起我对雪域白玉县的向往。
与妻商量了几天,终于决定前往白玉县,看望老同学并旅游、避暑。
泽旺是一个很热情、豪爽的藏族小伙子,读大学时,与我关系特好。他喜欢写诗,更喜欢喝烈性酒。而酒,他又对“剑南春”情有独钟。他说:“如果谁送我两瓶‘剑南春’,我将为他写一百首赞美诗!”于是,我特意买了四瓶“剑南春”作为给泽旺的礼物。妻说:“你的这位同学岂不是要给你写两百首赞美诗?”
汽车一进山,凉风便迎面扑来,霎时,头上、身上、脚上,每一个毛孔都感到舒服。
“这才叫‘爽’嘛!有些人什么事都大叫‘爽’,简直糟蹋了‘爽’这个词了!”
妻本是出名的美人,此时由于脱离了燥热,由衷的高兴,艳若桃花的脸便开放了灿烂的欢笑。见到她笑,我的感受比凉爽更为惬意。
妻觉得山里什么都新鲜,几天的路程,许多旅客都疲倦了,可她仍十分兴奋,如饥似渴地观赏着沿途的山水、房舍、寺庙和偶尔见到的一群群、一个个身着奇异服装的藏民。其实,藏民的装束平时在电视中就见惯了,可她总时时指着路上的行人对我说:“这很好看!”“这种难看死了!”
车停了下来,司机说前面塌方了,已堵住了四五辆各种大小客货车。
山道狭窄,一边是望不到顶的山崖,一边是见不到底的深渊。据说这儿本不是常塌方地段,不知何故午后不久这儿就塌方了。
“各位乘客,十分抱歉!”看了险情后司机向大家说,“由于清理路障的工人还没有赶过来,今天可能无法通过了,这儿距麻城已有两百多里了,无法再回去,所以,今天晚上只有在车上休息了,请大家相互关照,有什么困难,请对我们说,我们尽量想法解决!”
话音刚落,车中就闹开了,有骂“鬼地方”的,有骂“养路工白吃干饭”的,有抱怨司机早上在麻城“耽误了四十分钟”的,妻也开始急躁了,频频下车又频频上车,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请问,你是刘杰吗?”
我和妻子都转过了身,只见一个浑身尘土、二十多岁的藏族小伙子站在路边,殷殷地望着我们。
“是呀!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我和妻子都十分诧异:这儿怎么会有熟人?可这个看似聪明诚恳的藏族小伙子我却不认识呀!
“那么,这位就一定是欧阳雪了?”小伙子眼望着妻子,脸上笑得如同开了花,那原本黑红的脸膛更显红艳了。
“对呀!请问您……”
“我是泽旺老师的同事,丹巴。泽旺昨天到昌都去了,他不能来接你们了,他说十分抱歉,特委托我来接你们。你看,这儿塌了方,我在白玉听到消息,赶忙跑来,怕你们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着急,况且你们对这儿一点也不熟悉。”
“哦!”
“不相信我么?看,这不是你们夫妻的照片,还有泽旺的诗集《雪域魂》,泽旺说你们一见到这两样东西,绝对会相信我的!”口气十分肯定。
是呀,那照片还是我与妻子的结婚照呢!泽旺没有参加我们的婚礼,非要我们的结婚照不可;而这本厚厚的诗集《雪域魂》,不正是泽旺的呕心之作么?这本集子收有他近十年的诗作,其中有百分之八十都写的是雪域民族纯朴、坚强、勇敢,省内一个著名诗人为他写了序,说这本诗集是“难得的脏器风情画”。泽旺将诗集邮寄来时,我为他高兴,为他激动,当夜就打电话向他祝贺,这月的电话费就较上月多了四五十元呢!
“刘老师,泽旺老师早就盼着你们了,可是这一趟公差又非他去不可,因为关系到我们白玉县文化馆的声誉啊!”丹巴一脸焦虑。
“哦!出了啥事?”我不由得紧张了起来。泽旺刚被提为文化馆长,难道就遇到啥麻烦事了?
“唉!事情倒是不大,可那边的人只认泽旺老师的帐,唉!”
“到底是啥事?丹巴老师?”
“唉!到了白玉,泽旺老师明后天一回来你就知道了!”丹巴一脸忧郁,两眼定定地望着山头快落的残阳。看得出,他在为文化馆焦虑,为泽旺焦虑。这真是一个好小伙子,我在为泽旺焦虑的同时,又为泽旺高兴:有一个好帮手。
可丹巴不说,我心里始终难以平静。
“丹巴老师说得对,到了就知道了,你急啥呀?”妻为我理了理挠乱的头发。
“刘老师,让那们二位在这儿过夜,我与泽旺老师都不会心安。这样吧,从这儿走小路,翻过山有一个寨子,叫金月寨,我们到寨子小学亚码老师家去住一晚吧!“丹巴用手指着右边那青翠欲滴的大山说。
“有多远呢?”我心里觉得丹巴这个建议好。
“大概十里左右吧。如果走快点,也许天黑前赶得到。”
“那明天咋走呢?”妻子显然有些焦虑。
“明天在金月寨旁可赶上亚罗开往白玉的车。”
“好吧,我也真想看一下藏区村寨小学的办学情况。”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你是不是还想写一篇调查报告?或者到这儿来招点学生回去?”妻子最烦的就是我工作休息不分,每当这时,她都会埋怨我的。
“那金月寨其实在我们白玉县还小有名气呢!因为那儿有一块奇怪的石碑!”
“石碑有啥奇怪的?”
“石碑本没有啥奇怪的,可那石碑是无字的,上面只弯弯曲曲刻了一些符号,既不是藏文,也不是汉文,无人认识,前些年泽旺老师请省里的一些专家来辨认,他们也无可奈何!拍了些照后,到几天也无定论。”
“石碑离寨子远不?”妻子问。
“就在小学后面的山洞中!”
于是,我们决定前往金月寨。
丹巴是个很热情的藏族青年,他非要帮我背背包,我怎好让人家背呢?坚决不答应,最后,只有将妻子的背包抢了过去。
这山上的小路(其实啥路也没有,只是一些略可踩脚的石窝)实在难走,可丹巴竟然如走平地,我真佩服这些无所不能的藏族同胞,他们惯会在那本无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可我们才走不远,已累得不行了,特别是妻子,更感苦不堪言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果然,前面山坳中出现了几点灯光。
“金月寨到了!”妻子刚才还歪着嘴咒山石荆棘,可看见灯光,居然孩子般雀跃了起来。
“那不是金月寨,金月寨还在前边!”
“还有多远?”妻子一下子僵住了。
“大概还要走一两个钟头吧!”
我一下子蔫了下来,妻子索性坐在山石上,喘着粗气,“我们今晚不去金月寨了,就在这儿找个人家住吧?”妻子可怜巴巴的央求着丹巴。
其实,我也明白:山区路程是“当面能呼应,相逢得半年”,路难走,转弯、上下山,再加上我们是没有山行经验的山外人,就更不易走了。我们也确实走不动了。
“将就一下吧!”我也望着丹巴。
这时,看不清丹巴的脸,不知他是在嘲笑我们无能,或是为我们今晚的住宿而内惭。
丹巴终于把我们带到了一幢全石片垒砌的房子外,他敲开门,用我们听不懂的藏语和房主谈了一阵,房主终于把我们让了进去。
房主是一个满脸沟壑的藏族老大爷。
房内陈设十分简单,正面一个神龛,神龛上燃着巨烛,神龛正中挂着两幅神像。看着神像,我不由得一惊:其中一幅是毛泽东的画像。而今,居然还有人在家中,而且在神龛中挂毛泽东的画像,看来,这位藏族老大爷一定是翻身农奴了。
藏族老大爷用十分生硬的汉语对我们说:“对不起!耐一耐!”他给我们端来了大碗的青稞酒、煮土豆和一盘干牛肉。他见我看着毛泽东的画像,顿时十分虔诚地上了香,合掌念了一阵后说:“毛主席,伟大!”
这晚上,的确我们吃得不好,特别是那干牛肉,妻子总是咽不下,可丹巴却赞不绝口。我觉得经历了这一生也未必再经历的事,心情好极了,因此饭食的粗细,我也不太在意。
第二天,丹巴把食宿的钱坚决塞给了老大爷,我们就上路了。我想:到了金月寨看了石碑,说不定还能赶上去白玉的班车。
将近中午了。仍未见金月寨,甚至后来连一个小村寨也看不见了,而这座山也象永远也翻不完越不过丝的。丹巴见我们着急,也急得满脸是汗,额头的筋胀得鼓鼓的。
“好像是迷路了!”他烦躁地说。
“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急了。
“再走一段看看!”
无奈,我们只有走,我们边走边和丹巴说几句话,他答得很少,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好受。可后来,他索性啥话也不说了,只顾走。
我心里陡然生出许多疑问来:金月寨旁真可以乘上去白玉县的车吗?丹巴不是说只有十里左右,可我们走了半天零一晚上,咋就走不到呢?丹巴为啥老把我们向这无人烟的地方带?他安了啥不可告人的心吗?可我们身上并无多少钱财,值得他这么长途跋涉奔波吗?若说丹巴用心不良,那泽旺又为什么让他来接我们,还把我们的照片交给这个人呢?一路上也看不出他有啥坏心眼呀!他不是还主动抢着帮我和妻子背背包吗?
我越想越想不通,妻子的眼色告诉我:她也感到诸般不对。趁丹巴不注意时,我在妻耳边悄悄说了一句:“提防点!”妻用力捏了一下我的手。
“真倒霉!刘老师,你看我怎么就迷了路呢?那好吧,我们吃点东西就往回走吧!实在对不起!”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包干牛肉。
我十分奇怪:妻子的包中哪里的干牛肉呢?
“昨夜,老大爷硬将这包干牛肉塞给我,他说:路上饿了充充饥。这不,还真用上了,只是没有酒!”丹巴抱歉地对我和妻子说。
“将就吃点吧!还喝啥酒呢?”妻子并不为丹巴的道歉所感动。
于是,我们就着涧水,吃了起来。我真饿了,不管这干牛肉是否嚼碎嚼细,囫囵地吞了下去。妻子紧皱着眉头,只吃了几小块就不再吃了。
丹巴边殷勤地劝我,边不断地向我们道歉。
可听着听着,这丹巴的声音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弱小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喝骂声让我醒了过来。我想揉揉眼睛,可手却抬不起,我这才发现被牢牢地绑在一棵树上,妻子也双手被紧绑着。丹巴,这个原来和蔼、热情、坦诚的小伙子,这时却目露凶光,明晃晃的藏刀在他手中旋转着,地上,我们的包全被打开了,我和妻子的几件衣服被甩得老远。
果然这小子不是好人!
“还不说么?你们带的无价宝在哪儿?快交出来,老子就放了你们,若不说,就把你老公给花了,丢在涧中,不出两天,骨头就没有了。嘿嘿,你这个欧阳雪,你这个美人,就只有让我慢慢享受了!”说着,淫邪地伸手去摸妻子。
妻将身一闪,愤怒地说道:“我们去看朋友,哪有啥无价宝,你想宝想疯了吗?”
“还骗我么,如果不是泽旺这小子亲口说的,我会花这么多功夫和你缠?”
泽旺?泽旺会说我们带有“无价宝”?我越想越想不明白。
丹巴说什么也不相信我们的话,他将两个包又搜了一遍,又把我的衣裤一件件用藏刀割下,搜了个遍,还是一无所获,他脸上也很茫然。随着,他狡黠地一笑:“如果这么轻易就搜出来了,还叫无价宝吗?我也不跟你们歪缠了,快,把包背起,跟我走!”说着,把两个包全挎在妻子背上。昨天下午、今天上午还抢着背包的热情劲儿,早已无影无踪了。
“刘老师,你就在这儿吧。放心,可能会有人到这儿来,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不会葬身兽腹的。你的妻子欧阳雪么,我要把她带到我家去。把她的衣裤脱干净慢慢搜查,嘿嘿,即使搜不出无价宝,也让我享受一下这么美的人儿呀!”
我气愤地恨不得咬他几口,可高声叫骂,低声解释,都不能让这个家伙回心转意。我真想不到有这么阴狠贪婪的人。
妻子满脸愤怒满脸泪痕,苦苦哀求,无济于事;她又骂,把她所知道的粗话都骂了,这是她平生第一次骂人呀!可她只能满脸绝望、无奈,还是被丹巴一手提刀,一手拉着下了山坡。
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挣,挣不脱;跳,跳不起。“泽旺呀,泽旺!我的好同学,你在哪儿呀?你怎么有这样的同事哟?你怎么会让这个心如蛇蝎的丹巴来接我们呀?”我急得呼天抢地了,可这人烟绝迹的地方,又会有谁能听得见呢?
我可怜的妻子呀,你千万要挺住,要想法对付这个凶狠的家伙呀!你从未与我出过远门,第一次与我进山看同学就遇到这该死的塌方,又遇到这该死的丹巴。
一顿饭功夫,要在平时,只是弹指间,可此时,却如同过了几年。
“那边有人的叫骂声,快,过去看看!”浑厚略沙的声音传入我耳中。泽旺,是泽旺!几年过去了,声音任然没变。
“是泽旺吗?我是刘杰,快过来呀!”我的喊声有惊有喜,还有伤感的哭声,完完全全失去了平时在学校的风度。
转过山岩,一行五人跑了过来,走在前面的果然是泽旺,后面跟着三个警察和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
“快,快去救我的妻子,丹巴把她劫走了!”
三个警察迅速向我手指的方向追去。
这时,我才明白:这个小伙子根本不叫丹巴,他是前几天因盗窃而被泽旺解聘的临时工,成都人,名叫李小东;我明白了这白玉县根本没有“金月寨”,也没有什么无字碑,甚至连“亚罗”这么个镇也没有。丹巴,不,李小东,这小子真会瞎编。
原来,泽旺收到我的信后,十分高兴,“我的好同学刘杰和欧阳雪五天后要到我这儿来,还给我带来了我梦寐以求的无价珍宝啊!”也难怪他高兴,泽旺回白玉几年来,几乎没有山外的同学去看过他。他翻出当年我寄去的照片见人就说。
这天晚上,文化馆财务室的门被撬开了,还好,馆里一个员工发现了,马上叫起来泽旺,小偷打着手电筒正在撬出纳办公桌的抽屉,被堵了个正着。原来这个小偷就说临时工李小东。
鉴于李小东认错态度诚恳,况且没盗走钱财,泽旺和几个同事商量后,没将其送派出所,只将其解聘,令其离开白玉县。
昨天下午,泽旺算好我们应该到了,这才发现办公桌上的照片连同夹照片的《雪域魂》都不翼而飞了。又听说离城六七十里处的地方塌方了,泽旺依秩向每个司机、每个旅客打听、问询,听说两个成都口音的男女青年旅客,被一个藏族青年引着翻山去了。“见鬼!翻这座大山那是往哪儿去呀?”又听工人们说:“这儿本不是塌方地段,很有可能是有人在这儿爆破所致。”泽旺更感觉有些不对劲,便请执行完任务归来同时被阻的公安干警一道,顺着有人踏踩过的似路而非路的一线印迹追了过来。
“这小子是冲着‘无价宝’来的,对我们又是威逼又是搜身,可我们哪儿来的什么‘无价宝’?对了,他说是你对他说的。”
“这家伙想钱想疯了!你确实带了‘无价宝’的,你不是在信中写了吗?不过,这对我是‘无价宝’,而对他,对其他人就未必是‘无价宝’了,这‘无价宝’就是你带的‘剑南春’呀!”
哎呀,这个泽旺,你这种不着边际的比喻差点要了我们夫妻的命,况且此时,我妻子还不知是凶是吉呢!愿祖宗、愿天王老爷保佑保佑,保佑警察快快抓住这个自称丹巴,一副诚恳,却心如蛇蝎的李小东吧!
可无论我多么着急,无论我怎么念佛,警察追过去的路上,却始终不见一个人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