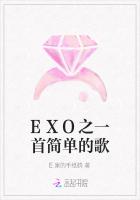廷尉的话对于多数官员刺激不大,然而卫国帝后和心腹大臣多是知道二娥与、栗特康夫妇与阿拉耶识的渊源的,此刻俱各吃惊,同时瞪着廷尉等他下文。
阿拉耶识发觉二娥没来当差,以为生病,派人去家中探视。结果来人发现其家中门户紧闭,问左邻右舍,都说夫妇二人昨晚都在家中歇息,今早也未发现屋中人出来。龙腾侍卫警觉性强,遂翻墙入内,发现二娥倒在卧室血泊中,栗特康半醉中右手边是染血长刀。户内门窗闭合无外来痕迹,邻居反映夫妇两人经常争吵,案发当晚吵得厉害,推测是栗特康酒后失手杀了二娥,已经把栗特康就地锁拿。
听完廷尉定案陈述,阿拉耶识二话不说跳上凤辇要去看现场,冉闵紧随着也钻进来,与她并排而坐,面沉如水不说话。阿拉耶识瞟他一眼,也不好吭声。朝臣因帝后小夫妻拌嘴,打破太尉李农引发的僵局,笑话还没看完就碰上近臣杀妻血案,李农儿子被杀一事就此揭过,竟无人再提。
冉闵跟着去杀人现场,多半因为栗特康的原因。整个邺城的胡人连一千人都不到,栗特康是卫国唯一留在邺宫当差的胡人,作为内应投降卫国的胡人留在皇后身边,算是对他最大的信任。这样一个人竟然有杀妻恶行,大大扫了冉闵的颜面。凤辇中的冉闵虽正襟危坐,内心却惊怒交加,充满对栗特康的鄙夷和不齿。栗特康是阿拉耶识近卫,喝酒乱性能杀妻,也极可能对阿拉耶识不利。胡人当真野性难驯,他越发痛恨自己连番的判断失误,不仅葬送父亲的心血飞龙军,更加对不起阿拉耶识。他在朝堂上讥讽阿拉耶识,不过是被嫉妒冲昏头脑罢了。郊祀之前,他寻她告别却发现李文吉竟然又跟她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男的还闭着双眼靠在她身上说着软绵绵的话。李文吉以前的恶行为冉闵深恶痛绝,让他随意出入邺宫也是看了嬴归尘的面子,况且阿拉耶识非要给他这个特权,冉闵只得应允。但是,他接连两次亲眼见到阿拉耶识与李文吉独处的暧昧情状,任是再大肚的丈夫也是不能忍的。他不想当着李文吉与阿拉耶识争吵,强忍进屋分开二人的冲动,愤然而去。他第一件事便是找来宫人询问皇后情况,得知对嬴归尘和李文吉师兄弟十分亲近,探望嬴归尘病情就盘桓一个上午!更气人的是,昨日又与李文吉独处良久,冉闵觉得自己快疯了!以往她与未央书院弟子言笑晏晏,虽感酸楚难当,却也清楚她的心不在自己身上。现在已是夫妻,她竟在举国议论其异行的当口依旧我行我素,心里当真有自己这个夫君么。当阿拉耶识一反常态以臣妾自称的时候,着实把冉闵气得不轻,满脑子想的都是她与自己生分了,缘尽了。当栗特康杀人消息传来,无异于又是一记闷拳擂在心窝,蒙太后刻薄中带着威胁的话飞快地在脑海里钻进钻出。
“一个没有福气的男人,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东西,是要倒大霉的!”
“我女儿只有天子才配得上,你是胡人养孙岂有真龙的命,凭什么和人争,你根本保护不了她。”
“你若真爱惜我女儿,就切莫拐她去赵国。老身虽不理朝政,四海事情还看得清楚。赵王那十几个儿子个个如狼似虎都盯着皇位,你自身尚且难保,阿拉耶识去了邺城,还不被那些胡蛮子活吃了!”
“你行差踏错都是命,可不能带累我女儿!”
蒙太后言犹在耳,似诅咒似规劝,钢针般扎得冉闵心头滴血,他的拳头握得更紧,指甲深陷入肉亦不觉得痛。
恍惚间凤辇已到栗特康家中。栗特康的府邸在邺城西边胡天殿附近,前赵时此地原是胡人聚居所在,因前赵容纳的胡人众多,邺城胡人官贵居所虽然豪华却不甚大,况且胡人本就对居室格局大小不如华夏人讲究。栗特康住的是一五品官员宅邸,只有一进宅院,进了院子就是一排主家的房子。
阿拉耶识心急,当先跳下凤辇直奔主屋,冉闵紧随其后。看守的官差见帝后驾临,统统跪成一片。卧室地上淌着一滩深红干涸血迹,二娥的尸身用白布掩盖起来,栗特康被五花大绑捆好靠墙蹲坐;环视屋中杯盏堕地,马扎、桌案移位,明显屋中有过抓扯争斗痕迹。谁看了这副情景都认为是夫妻争吵失和所致。
地上的栗特康见阿拉耶识来到,挣扎着跪下,睁大圆眼看着她和冉闵,嘶声道:“我没有杀二娥,请陛下、皇后明察!”
冉闵俊颜带煞,沉沉道:“栗特康,你酗酒恶习不改,终铸大错,还敢狡辩!”
阿拉耶识寒着脸没有多看他一眼,而是蹲地掀开白布察看尸身。死者是二娥无疑,她能从凶残胡人手中逃脱却凶死在自己家中,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令人唏嘘。二娥胸腹斜着一道长长深及脏腑的致命刀伤,鲜血浸湿衣裳淌了一地。
见二娥衣衫完好,阿拉耶识蹙了眉问廷尉可曾让仵作验尸,廷尉一愣之后回答:“经查,栗特康与其妻唐二娥素来不和,昨日醉酒滋事,与唐二娥争执不下,失手杀人。事实清楚明白,便没有让仵作验尸。”
“胡来!”阿拉耶识绝色娇容拉得老长,语气严厉:“所有案件必须按照规定程序完成,不得随意更改。无论自杀、他杀何种情状,杀人案必须由仵作验尸、差役勘察现场并记录在册。栗特康说他冤枉,你可问过详情?”
这廷尉原是新晋的官员,本身是华夏族中世家子弟,卫国张榜纳贤便来投靠。他虽有经纶武艺,人品中直却不熟悉刑律,见着内室杀人,早先入为主定了栗特康之罪。此时见皇后过问,才觉惶恐。
“回皇后,臣盘问过嫌犯,他承认与妻不和,昨晚也确曾争吵。他说昨夜饮酒醉倒,不曾杀人。今日官差上门时,他还倒在地上睡觉,用了一瓢冷水才将其泼醒。这等醉汉行凶也是常有的,醒来个个都不记事,也难得认罪。臣以为,栗特康杀妻事实确凿,纵然抵赖也是枉然。”
“好,就算栗特康杀妻,你可问过当晚他夫妻因何事争吵?他们夫妻不和究竟是何缘由?”
廷尉立刻被问倒,他没有办案经验,浑不知还要问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
阿拉耶识重重地冷哼,“依照卫国律法,杀人情状分缘由定罪,你弄不明白杀人缘由,凭何定罪?还有,栗特康酒量多少,昨日饮了多少,到底醉是未醉,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你能判定?”
廷尉听得冷汗直流,直直跪下请罪。他刚才急着进宫呈报,原是因为这夫妻二人皆是皇后身边的人,栗特康还是解救皇后的功臣,卫皇对其颇为关照,才专程请帝后圣裁,是以没对案子深究下去。
“封锁整个院子,无干人等不得进出。桌上酒杯内残余的酒送去查验有无下药,死者的尸体由我亲自来验!将栗特康关在廷尉府大牢听候审理,着人将邻居传唤到廷尉府大堂等我出来问话。”阿拉耶识有条不紊地下达指令,廷尉府差役忙不迭分头行事。
原本冉闵对此案并未多想,阿拉耶识一连串讯问让他想起她在秦国掌仵作、训差官,断李文吉连环杀人案的功绩,见她再次拿出天巫的魄力做事,心中又气又爱,要留下来看她施为。
阿拉耶识先将二娥尸身从头至尾细看一遍,未见其他可疑处。这才动手解开其衣衫,露出洁白细腻的身子来,粗长的伤口格外刺眼,有二尺来长。在脱二娥衣服的时候,冉闵早背过身去,阿拉耶识着实生他的气,见他赖着不走便黑着脸使唤他,让他过来辨认伤口可是龙腾卫士的佩刀所伤。冉闵除了阿拉耶识哪里见过别的女子身体,让他辨认伤口一万个不愿意。
“做不来啊?做不来就离开,无关人等不要妨碍办案,留在这里把现场都破坏了!”
“你!”冉闵紧咬下唇,无意中流露清纯男儿的羞恼姿态,“朕岂能算无干人等,休说凶案现场,便是龙潭虎穴也是去得!”
“皇帝做皇帝的事,仵作才验尸。你既然帮不了我,我叫其他人来,还请陛下回避为好,免得女尸污了眼。”
“董秋滢!”冉闵几乎要拍碎正面壁的墙,切齿恶声:“这辈子除了你,其他女子我连正眼都没瞧过!二娥身上不着寸缕,我怎能羞辱了她,浊了自己的眼!你这般强人所难,究竟是不是我冉闵的妻?”
阿拉耶识吃他痛责,这才后知后觉对方纯洁得可爱,不禁失笑,憋了几日的郁恼顿时消了大半。她将衣衫盖住二娥,仅留出刀伤部分,拉拉冉闵龙袍,和颜悦色哄道:“栗特康的佩刀是你所赐,与普通龙腾卫的佩刀不同。杀人案事关重大,最重细节和证据,若是你来查看刀口我才放心。我已将二娥身体盖住,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是你的妻子,当然不喜欢你看其他女人的身体。”
冉闵被她小手拉住衣服扯两扯后,心肠早就化作一团绵软,得了台阶还不放心,偷眼见二娥上下都搭着衣衫,这才凑到跟前辨认伤口。
这确实系栗特康佩刀所为,伤口深可见骨,达于肺腑,属一刀毙命。
阿拉耶识疑惑地问自己:“怪了,我与栗特康在羌胡军中相处半月,他胆大心细,精明坚韧,遇事沉着冷静,素有节制。羌胡兵荒诞无稽如斯凶恶,也从未见他失态,反是醉酒对妻子下手,这不像他的行事风格。”
她声音虽轻,却被冉闵听个真切,竟不晓她与栗特康在羌胡军中有旧,而之前两人居然对此只字不提,难道又是将栗特康招惹了不成?难怪,栗特康不要外放官职非要进宫做侍卫。冉闵妒火直冲顶门,不由得四下张望,恰好看到二娥手中死死攥着一物,掰开取出却是一方上华贵丝帕,淡香浮动,上绣拈花手,并旁侧手写“唵嘛呢叭咪吽舍”七字真言,最后的“舍”字是阿拉耶识专门添上去的,亲传给自己,说是“舍”字在往生时特别重要。冉闵认出这方丝帕正是袭人绣花,阿拉耶识用鸦翅沾笔金汁亲书真言的丝帕,自己来信索要未果之物,不想竟到了二娥手中。
阿拉耶识冷不防瞧见自己的丝帕在凶案现场,怔了怔方才想起那日引出栗特康心结后,拿给他拭泪了。手帕是女子闺中私密物件,她嫌弃别的男人用过,便没要他归还。如今手帕出现在二娥手中,还被攥的如此紧,手帕上全是皱褶。
冉闵剑眉也皱了起来,“二娥偷了你的丝帕?”
这种事情当然要实话实说,阿拉耶识没有多想便道出手帕来龙去脉。冉闵的脸是越来越黑,他揣着手帕,一言不发便去了廷尉大牢。阿拉耶识这才醒悟要坏事,也追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