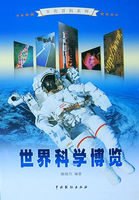“非也非也,被气死之人该是我吧!”秀竹长身而立,双手负于身后,既然揭破脸皮就再无顾忌,笑容转瞬即没,凛然逼视阿拉耶识,“天巫好大架子,毁诺食言不说,国礼相迎亦不屑一顾,让我怎么办?”
乍见此人,早让阿拉耶识心如擂鼓,万料不到他竟能突破吕氏围剿和石氏父子的监视,在石闵和自己眼皮底下混进身旁,而自己与他相处近十日还懵懂无知。她感到心虚,尴尬得手脚没地搁:“慈心,你不在商洛山藏身,贸然下山太危险——”
“既知我下山危险,却为何逼我如此?”秀竹便是慈心装扮,他撕去面部鲛皮后真容反比女子时更俊秀。提起阿拉耶识所为,他已是怒不可遏。一旁的桂枝是邓通所扮,见主子与天巫势同水火,立刻知趣遁出房间,留下他们二人独处。
“隐蔽商洛山以待时机是你目前最好的出路,我去不去汉国有何干系,难道你还能跳出来接我不成?”阿拉耶识被娇宠惯了的人,第一次见识慈心疾言厉色问责,面子早挂不住,何况她自认行得正坐得端,当然要反驳于他。
“有干系!”慈心牙齿咬得咯咯响,清秀的脸颊是上肌肉跳动,十分激动。“你要救石闵折返去赵国我没话说,可你这样口是心非耍弄男子感情便是你们中国女子的习气?”
“你血口喷人,我何时耍弄男子感情?”
“呵,你还不承认!”慈心口气咄咄逼人,双手抓住阿拉耶识肩头迫使她与自己双目对视,“我来问你,你与秦皇打造的订婚戒指是怎么回事?”
“那是麻痹他的,是计策!”
“就算用美人计,可你与他在巫殿卿卿我我,演戏要到这个地步?”
阿拉耶识眉心微皱,慈心的耳目不可小窥,连巫殿都有他的眼线。“那算什么,何况都是他主动,我要是不配合岂非前功尽弃!”
慈心冷笑连连,“好,秦皇的事就算你有理,你和石闵呢?”
“咹,棘奴又怎么惹你了?”
“少装蒜!”慈心从胸前摸出同济商号少东家的玉牌悬于她面前,“你熟读四书、知礼义廉耻,这玉牌是你与我订婚信物,你却当成何物?女子悔婚另嫁是重罪,你想清楚。”
这下阿拉耶识彻底毛了,她最见不得用中土习俗惯例来管制自己的那套东西。“我就是悔婚了,你去告我啊?”
慈心瞳孔紧缩,针一样扎在对方身上,口吐恶言:“勿怪嬴少苍也说你水性杨花,就连做梦也叫棘奴的名字,轻易让我们几个为你神魂颠倒,不知羞耻!”
“你胡说,我才没梦见棘奴——”阿拉耶识顿时急眼,分辩的话刚说出口马上觉得不对,惊怒中瞪着慈心,“你是如何得知我做梦不做梦?”
慈心当即哑口无言。阿拉耶识稍稍动念便明白定是“秀竹”借伺候自己的时机,夜里进房中窥见自己做梦。那么,前几日自己究竟是梦到棘奴还是慈心与己缠绵?此念一出,冷气从脚底凉到脑门,阿拉耶识立即呆住,粉红樱唇自然张成圆圈,完全惊悚了。
两人从刚才激烈争吵到突然冷却,看着对方都傻掉了。良久,还是阿拉耶识先开口问询情况:“你和邓通的身份早被棘奴识破,只瞒着我而已?”
“我们的易容术乃许负夫君裴钺所授,当不会轻易被人识破。石闵第二日在襄国的眼线中打探一遍便推出我们来历,为防走漏消息才顺着你的意思将我们‘收房’,其实夜里不是下棋便是打架,故意做出动静气你。”
“你们知道我在观察?”阿拉耶识用文明的“观察”替代“偷听”,掩饰自己的心虚。
“你没有武学根基,脚步和呼吸在我们听来沉重得很,隔着老远便知你消息。”
偷听行径于他们而言纯属掩耳盗铃之举,阿拉耶识羞得耳根通红,赶快将话题转移到慈心的去留上。“别说那些有的没的,先说你打算怎么办?”
“跟我上商洛山。”慈心执拗地握住她的手,坚决表明态度,“石闵不同你去杨越,你还不死心吗?现在他的危难已解,你留下反而束缚他手脚。”
“我上商洛山就束缚你的手脚了。”阿拉耶识甩开他的手不满道。
慈心重新牵了她手,认真地看着她说:“石闵与我都在等待新君即位,他在明,我在暗,相较而言,我那里比他更安全。石虎死后,石闵先撑一阵没问题。我这边只要刘长即位便能公开行动,届时还可与你一道相助石闵,此为上上之策。”
阿拉耶识缓缓摇头,慈心急了,咬牙切齿问道:“大牛,我如今只要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笑话,如果没有记住你汉文帝刘恒,我怎会如此待你。阿拉耶识瞟了他一眼,轻轻问他对母亲薄姬如何,是否经常为母亲尝汤药?慈心想也不想便点头承认,因怜母亲多年深宫孤苦无依,还要看宫女脸色行事,便对母亲极尽孝顺。
“大牛勿虑,母亲一定赞成我们在一起。”
“也赞成你把孩子母亲赶出家门?”
“大牛,府中美人的事我们以前谈过,秦皇能遣散六宫,我当然也能送走她们。”
“可你不是秦皇,他娶我是为了巩固君权,是帝王心术。若我使你的孩子没了母亲,才是真正造恶业了。”阿拉耶识看着慈心的眼神同样坚定,她刚才问慈心母亲薄姬便是最后确定慈心与历史上刘恒是否具有同样心性。史载刘恒仁厚至孝,中国传统美德“二十四孝”故事中,“亲尝汤药”说的就说刘恒为母试药的孝顺故事。其母薄姬为人胆小本分,克勤克俭,自己就算想嫁给刘恒,薄姬绝对不敢认天巫做儿媳,光是各方政治压力就会吓破她的胆子。就算不为埋没汉民族,也要避免异日刘恒落入“老妈和老婆二选一”的陷阱。阿拉耶识推开慈心,从容平静地表述意见:“刘恒,以前你以于世无扰的商人身份与我私定终身,你欺骗我在先,我悔婚理所当然。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你回商洛山去,不要再纠缠我。”
她退让到房门口做出请走的姿势,坦然注视对方。慈心沉下双眉,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再看看自己身上的艳丽女裙,凄然一笑:“这算哪门子的理由?我隐瞒身份骗了你,你装成个丑怪男人骗我怎么说?你迫不得已,我亦是形势所逼……”慈心拖着沉重步履来到她面前,拍着胸脯愤懑地倾诉不公:“在津台你都愿意跟我走,现在又翻脸不认。你排斥帝王却怂恿我登基,不喜欢我为何要同我夜宿百福,雨夜定情?你亲口许诺非我自愿,绝不驱赶我离开,如今你故技重施,你可恶,可耻,你枉为人师!”
慈心高声谴责阿拉耶识,后者心惊肉跳,东明观中全是赵皇耳目,石宣和石韬两人离开与否还未可知,他这般闹将起来行藏败露,性命堪忧。阿拉耶识情急之下顾不得害臊,匆忙用手捂住慈心的嘴,低声责道:“想死啊你,被赵国人发现你就完了,我也保不住你!”
不料慈心反而像狂了一样质问她:“你的免死金牌正好排上用场。在哪里,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看看我值不值你垂怜施救!”
“疯了你!”阿拉耶识气得七窍生烟,两手齐上也捂不实慈心的口,反被他捉住双手。
“我就是疯了。把金牌拿出来,知道你是为石闵准备的,舍不得呢。你现在缺男人了,那种‘他在我心中就是个孩子’就是睁眼瞎话,你喜欢他我成全你……”
慈心清秀的面庞因嫉妒和愤怒而扭曲,肺腑之言呐喊而出,阿拉耶识脑子轰地乱套,突然踮起脚尖将自己双唇贴到他的嘴上堵住他的话,慈心的声音嘎然而止,全身都僵了。阿拉耶识继续用唇死死封住他的口,慈心愣了片刻忽然将她双手反剪在墙壁,身体重重地叠在她娇小身躯上,低头含住她的樱唇大口痛吻,火一样的热情滑向她咽喉深处,搅动唇齿芳菲。这是阿拉耶识主动惹的祸,她不能也不想避,放任他的唇舌肆意而为,在这寄托了她对绝对恋情的美好遐思的初恋身上,她短暂妥协,让自己沉迷于爱的纠缠中。她开始回应他的吻,慈心放开她的双手,搂上她的纤腰,她则双手勾住他的脖子,正如一对热恋中的爱侣释放激情。
静悄悄的窗外,静悄悄的后院,静悄悄的人。
石闵颓然靠在墙壁上,无声地哭泣。屋中男女的激吻彻底摧毁了他的希望。自打她强行指派给他通房婢女后,他与慈心便夜夜暗中较劲,仿佛那样才能得到答案。每天他都仔细分辨她的心情,多盼望她能吃醋,能闯进房来阻止他的“荒唐”,可惜她没有。她明明在偷听,却始终不越雷池一步。慈心很满意,挂着胜利的笑容离开。前半夜,慈心与自己上演闺房大战;后半夜,慈心则扮演忠心的秀竹守在她床边。他警告慈心,慈心却出示订婚玉牌给他看,他退却了。是啊,他没有立场拦住两人中间。津台事变时,他已亲手将滢儿托付于慈心,他策划水灌邺城也是为了成就慈心和她。本来他不存奢望,可是她竟然舍汉赴赵,舍杨越回邺城,才有了他在渠边恣肆的爱意狂潮,结果依旧不敌慈心旧情。
就在刹那间,他做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