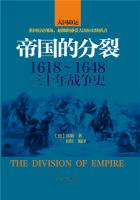当天晚上,玄宗派人请王源去散花楼见驾,王源却并不想去见玄宗,此刻的见面会十分的尴尬,而且王源需要好好的想一想事态如何发展,自己如何应付这个局面。
于是王源便推脱身子不适,躲在书房里不见来请的内侍。来请的内侍很是踌躇,因为来时玄宗要他一定要请王源去见驾,否则他便要挨板子,故而那内侍被回绝之后却并不离去,站在王宅的前院里搓着手不肯走,不断的哀求黄三.去通禀。
黄三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去求公孙兰去劝劝王源,这家中恐怕只有公孙兰能劝得动王源了。公孙兰本已经快要睡下,和儿子久别重逢,自然是要陪着儿子的。听黄三说明了情形后,公孙兰皱眉想了片刻,便将儿子交给侍女哄睡,自己去往书房来寻王源。
书房中,王源正百无聊赖的哗啦哗啦的翻着一本书,但其实他什么也没看下去。公孙兰推门而进,轻轻的在王源的面前坐下。
“表姐还不睡么?这几日表姐也甚是辛苦,今晚该好好的睡一觉才是,很快我们又要离开成都了。”王源放下书本微笑道。
公孙兰怔怔的看着王源不说话。
王源被她看的发毛,笑道:“怎么?我脸上有花么?”
公孙兰柔声道:“不是二郎脸上有花,而是我看着如今的二郎,想起了当年我们初见面的时候。梅园之中第一次见面,那时候的二郎还是个懵懂少年。一晃都五六年过去了。”
王源笑道:“是啊,五六年了,表姐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成为我的妻子,和我都生了平儿吧。”
公孙兰面色微红,微笑摇头道:“如何能想到?当年我对你可并无好感。你偷看我练剑,我差点一剑宰了你。然而如今,二郎已经不再是永安坊中的少年,而是顶天立地担着天下的大元帅了。”
王源叹了口气道:“大元帅,是啊,谁能想到我有今日?然而大元帅似乎也不能让我开心起来,我反倒有些怀念过去那些简单的日子。”
公孙兰摇头笑道:“二郎言不对心,谁会怀念过去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二郎也说过,你生来就是不甘平庸之人,叫你去和我们隐居山林,你会闷死的。况且你常说你也脱不了身了。”
王源点头道:“是啊,脱不了身了,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了。”
夫妻二人沉默了片刻,公孙兰道:“你当真不去见陛下么?”
王源摇头道:“我不想去,去了不知道说什么。今日的事你也知晓了,现在见驾会很尴尬。我想陛下其实也并不想见我,只是房琯今天被处死了,他想看看我的反应罢了,或者是告诉我,他对我极为信任,虚情假意的说些话罢了。”
公孙兰想了想轻声道:“二郎,有句话叫做强极则辱,你听说过么?”
王源愣了愣道:“表姐何意?”
公孙兰道:“有些事其实需要用智慧,而非是强硬的面对。我知道你是有智慧的人,你现在的状态却叫我不解。譬如现在,你去见陛下,恰恰表明你光明磊落,你不去一则是怠慢陛下,二则会被牵强附会之人说成心中有鬼,惹人非议。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你都应该去见陛下,而且和他好好的谈一谈。”
王源皱眉道:“我何尝不想好好的谈一谈,然而我知道,陛下心中的那句话可能已经挥之不去了。我去见了,也谈不到深处。”
公孙兰道:“我明白,相互不交心的谈话最是伤人,最是无趣。然而你现在的位置却要你有大肚量来容忍。眼前之事平叛为大,陛下杀房琯也是为了你能替他平叛,所以你们的目标目前是一致的,暂时还可以相容。所以你不必担心其他。”
王源道:“那以后呢?若我当真平叛成功,以后该如何?我从此刻便已经嗅到了风雷之声了。表姐不妨点拨我一下,我现在脑子很乱。”
公孙兰静静看着王源道:“我不知二郎心中真正的想法,若二郎心怀大志,我便什么都不说了。但若二郎只是为以后的事情担忧,从而想解决问题的话,我倒是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
话不必说的太明,公孙兰口中所谓心怀大志之意大家都明白。王源有些纳闷,自己难道给所有人都是这种感觉了么?为何人人都会这么想?难道自己行事强势了些,便被怀疑将来一定会有异心?公孙兰都这么说,也怪不得外人说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表姐,你是知道我的,只要不是将我逼上绝路,我是绝不会做出惊天之举的,我还是希望能安安稳稳的和你们过日子,但前提是我能保护你们,任何人都别想打我们的主意。”
公孙兰微笑道:“我知道,你不必解释。你做任何决定,我们都会支持你,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而正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我才要提醒你,有些事凭你的智慧完全可以解决,而无需走上那条路。”
王源笑道:“表姐说说该怎么解决?我的智慧比不上表姐的智慧。”
公孙兰轻啐一口道:“你莫自谦,或许你现在脑子乱了,心乱了,一时没想到罢了。好吧,我来提醒提醒你,说的不对之处,还请二郎指出。”
“来,坐这里说。夫君我洗耳恭听。”王源拍拍大腿道。
公孙兰当然不会像王源的其他妻妾那般坐在王源的大腿上说话,事实上她绝不允许自己放浪形骸,即便在夫妻生活上也很有节制。数日一次,绝不贪多。只是这一次她会极尽温柔,让王源得到极大的满足。
相较于其他的妻妾一味的纵容王源的行为,公孙兰把握的很好。正因如此,王源对她也很敬重。但以王源的脾气,口花花无人时胡乱挑逗是免不了的,公孙兰却也习惯了他的这些挑逗行为。
“二郎心中所忧的无非是将来平叛之后的事情。将来若平叛成功,天下太平,朝廷也恢复正常的时候。二郎虽功勋卓著,但功高震主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情。况且将来二郎手中握着重兵,这也是陛下的心头大患。有安禄山叛乱的例子在前,即便二郎无异心,朝廷恐也极为担忧。而二郎又肯定不会交出兵权的,这便是矛盾之所在。”公孙兰沉声道。
王源微笑道:“你很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不握重兵在手便是死路一条,我若握重兵在手,又将成为他人的心病。难就难在他们不愿相信我即便手握重兵也不会对他们不利。当然,换做任何人都不愿有此隐忧,特别是今日房琯说出那句话之后,便是捅破了窗户纸了,我想陛下心里一定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他杀房琯这么干脆,便是做给我看的,他担心我一怒之下真的对他不利,所以他选择了隐忍。这时候越是隐忍,将来的清算便越是猛烈。”
公孙兰点头道:“确实如此。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你和陛下之间已经有了隔阂,再无建立真正信任的可能,这才是最要命的。”
王源叹道:“是啊。这才是症结所在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说起来容易,但却是最难的一件事。”
公孙兰道:“然则既然和陛下之间再无建立信任的可能,你又何必去伤神。有时候未必需要正面应对,侧面迂回也是一种手段。我所要建议你的便是,何不放弃和陛下之间的纠葛,重新寻找可以建立信任之人。”
王源一愣,皱眉看着公孙兰清丽的面孔道:“你这话是何意?”
公孙兰低声道:“陛下年迈,原太子李亨忤逆,又……又不见了踪迹。在此情形下,储君之议很快会提出来。国本不立,人心难安。既然你和陛下之间难以建立真正的信任,为何不去在这上面想一想。若新君和你能建立信任,那些你担心的事情便不会发生。当然前提是,那是真正的信任。而建立这种信任的唯一办法便在于你能否让他倚重,能否在关键之时助他。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王源当然听的明明白白,公孙兰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她要自己放弃玄宗,利用自己现在的影响力推举一个能对自己绝对信任的太子。当这个新太子即位为皇帝,那么自己和这个新皇之间便是一种牢固的信任关系,因为是自己助他登上皇位,便是所谓的从龙之功。到那时很多事比玄宗在位要好办的多。
不得不说,这个办法确实可行。不换思想便换人,玄宗既然跟自己藏着掖着不能推心置腹,那么自己确实没有必要和他多费脑子,还不如曲线救国,重新建立和新皇的密切关系,这或许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
“你觉得如何?”公孙兰。
王源皱眉思索道:“我不确定这个办法是否有效,要想让继位的新皇和我之间建立信任,光是靠拥戴他成为太子未必便能达成。一旦选择错误,将来会更麻烦。”
公孙兰道:“当然需要斟酌。我认为需要满足两个前提,这件事便可进行下去。第一,这个太子的人选必须是毫无争夺皇位的希望,但他本人却又极度渴望成为大唐皇帝。在这种情形下,你帮了他成为太子,他才会真正的感激你。第二,光是成为太子还不够,新皇必须很快的继位,起码要在叛乱平息之前便要成为大唐的新皇。否则陛下继续享国,太子又将成为摆设。平叛之后,陛下回驾长安之后,事情也许会变得很复杂。到那时指不定又有什么人冒出什么事情来,导致功亏一篑。最好是能在成都期间便能新皇登基,因为在这里,事情会变得可控。”
王源低声道:“这两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难了。”
公孙兰微笑道:“不难的事情又怎会轮到你来做?以二郎的才智,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到。至于怎么做到,我却不知了。”
王源微微点头,不得不说公孙兰还是有些政治头脑的,实际上刚刚公孙兰所说的事情,王源早就已经有所考虑。只是忙着平叛,一直没有细想此事。但出了今日这件事后,王源不得不开始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推举新皇,看似无奈之举,但也有可能使得局面更新,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而王源对玄宗也确实有些感情的因素,但这些好感已经随着这段时间的密切接触和玄宗的所作所为而磨灭干净。王源几乎能百分百的肯定,在平叛之后,玄宗会和自己翻脸。既然如此,还不如早点做出应对。
“多谢表姐指点迷津,和表姐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啊。”王源笑道。
公孙兰啐道:“呸,少来取笑我,我要说的说完了,我可要回房去陪平儿了。我怕他醒来不见了我,会哭闹起来。”
王源点头道:“辛苦你了,我也要去见陛下了。”
公孙兰笑道:“怎么?想通了?”
王源道:“你说的对,越是此时,我越不能小家子气,否则会授人以柄,说我藐视圣上,说我心中有鬼。而且刚才和表姐一席谈之后,我更觉得要多和陛下接触,哪怕是浮于表面的交谈,或许也能安他之心,或许能从他口中听到些关于册立新太子的想法。我若知道陛下属意于谁是太子的人选,那么我便知道该去推举谁了。”
公孙兰轻笑道:“陛下属意谁,你便不会推举谁,陛下厌恶谁,你便考虑推举他,是么?”
王源哈哈大笑,负手往门外走去。公孙兰在后叫道:“披上披风,夜露深重,骑马风凉,二郎要爱惜身子。”
王源一笑转身,任公孙兰替他披上披风后,阔步出门而去。
……
散花楼玄宗的卧房中,百无聊赖的玄宗正在烛火下闲敲棋子。每当外边有脚步声经过,玄宗都会抬头看一眼,沉声问道:“是王源来了么?”
而每每得到的回答都是:“启奏陛下,王源还没到。”
就这样等了足足一个时辰,玄宗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这王源是彻底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自己宣他觐见他都不来,这已经是居心昭然了。房琯说的一点没错,他就是曹操,他就是借马嵬坡救驾,将自己挟持到了成都,用他手中的兵马控制住自己,然后为所欲为。这个人将来必定是第二个安禄山,一定是。
然而,这时候还不能跟他翻脸,一切都要隐忍,一切都要小心。一旦回到长安,脱离他的控制,自己便要和他彻底清算。这一点一滴的每一次怠慢和蔑视,都要化为一刀刀的血肉。此刻的王源对自己有多少次的怠慢和蔑视,将来他便要挨多少刀的凌迟。
玄宗恶狠狠的想着,手中的棋子被他瞧得稀里哗啦散落一地,在旁伺候的内侍惊慌失措的看着玄宗铁青的脸色,不知道是否该上前收拾满地乱蹦的棋子。
正在此时,门外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一名内侍沙哑的声音响起:“启奏陛下,王源来了。”
玄宗一惊,脸上愁容退散,深深呼了口气站起身来,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冠带,这才沉声道:“请他进来。”
片刻后,一袭黑色披风,身材修硕面容平静的王源出现在门口。
“臣王源,参见陛下。”王源沉声拜倒在玄宗面前。
玄宗看着面前跪拜在地的王源,嘴角露出笑意来。
“免礼,王源,快起来,免礼。”
王源道谢后站起身来,玄宗笑容满面,指着面前的椅子道:“坐下说话,朕还以为你有事耽搁了,不来见朕了呢。朕都打算睡下了。”
王源躬身道:“陛下恕罪,臣连日赶路,身子略有不适。适才内侍去传旨时,臣正在房中昏睡,本想请内侍回禀陛下明日再来觐见,但一想到明日清早便要离开成都赶赴军中,却又不敢耽搁行程,于是便强撑着来了。”
玄宗哎呀了一声,仔细看着王源的脸,点头道:“果然是清瘦了不少,白日里朕竟没注意到。早知如此,朕便不派人去请你来见朕了。你该好好的休息一晚才是。是朕的疏忽。”
王源笑道:“无妨,见到了陛下,臣感觉好多了。”
玄宗闻言,呵呵笑了起来。
君臣落座,内侍奉茶。玄宗目不转睛的看着王源道:“王源,朕下旨斩了房琯的事,你必已经知晓了吧。”
王源没想到玄宗如此的开门见山,见面便说此事,愣了愣沉声道:“臣听说了,只是没料到陛下下旨这么快。”
玄宗冷声道:“房琯死有余辜,竟敢挪用军粮,破坏平叛大计,这是动摇我大唐的基业,朕岂能容他。”
王源点头道:“确实该死。臣得知此事也是怒火中烧,但今日白天臣被怒气冲昏了头脑,举动有些出格,不该当着陛下的面追杀于他。在此,臣向陛下谢罪,臣的举动实在不妥,陛下请降罪于微臣。”
玄宗哈哈笑着摆手道:“你有何罪?你是心中急切之举,恰恰表明你对平叛之事看的极重,朕知道你的焦虑,朕不会见怪的。”
王源道:“多谢陛下理解。陛下虽不怪臣,臣却自己心里过不去。臣自罚俸禄一年,以赎臣之过错。这一年的俸禄全用于赈济百姓。”
玄宗愣了愣,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微笑道:“好吧,只要能让你心里好受,朕准了你便是。”
王源道:“多谢陛下恩准。”
玄宗道:“至于寿王之过,虽然此事他受房琯蒙蔽,但他也难辞其咎。朕已经命他解散所募之兵,并且革去了他河西节度使的遥领之职,严令他在家闭门思过三月,不许出门。你看朕的责罚可还合理么?”
王源淡淡道:“臣岂敢对陛下的旨意有所评判,我只能说,陛下恩赏分明,不避亲贤,行事公正,此乃圣君之行。臣佩服的五体投地。至于寿王的过错,倒也不是什么大错,若不是房琯怂恿,寿王怎会如此。错本不在寿王,其实无需惩戒。”
玄宗呵呵点头道:“难得你还维护寿王,他知道了岂不要羞愧死。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犯了错便要受惩罚,他的惩罚是免不了的。”
王源点头道:“遵圣意而决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