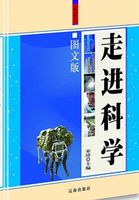海神庙门前人影搅动,老人和孩子们早早来到这片广场上,等待着午后祈雨庙会的大戏开演。更多的成年人是来这里交流沟通这大旱年的日子怎么个度法。大戏要等到祈雨的队伍返回来,在戏台对面龙王大殿前安放好龙王爷才能开演。等待开戏的人们在戏场上来回穿梭。戏场两边摆杂货、玩杂耍、卖小吃的还真不少。戏开演前的当儿,正是他们忙碌的时候。爷爷、娘娘(奶奶)领着孙子、孙女逛庙会,总要给买个手里耍的、头上戴的。老人们一年辛苦攒下几个铜钱,庙会上总要给小辈们花上些。男娃娃耍的莲花落、木枪、木棒;女娃娃要的红绸子、绿带子、绢花之类都有卖的。卖吃食的摊子、铺子有卖羊杂碎的,也有卖年糕、粉汤、丸子汤、麻花、大烙饼的。老人们领着娃娃寻找他们想要玩的,喜欢吃的;成年人逛庙会也要瞅瞅挑挑,看有没有他们可心的东西。穿梭于两边的人流此刻似乎还没觉得饥饿的恶魔正向他们袭来。这个时候虽说是民国了,可在这个地方什么样的铜钱还都管用。小摊小铺,什么康熙钱、雍正钱、乾隆钱还能花得出去,民国铜钱、银元、袁大头,只要是铜钱和银元都在一起混用。唯独那纸币没人敢收,更不收那地方上印制的币、券、元之类的纸钱,生怕今天收进来了,明天又不让用了,亏了老本。
这里的人们对羊肉一类的饮食有特殊的偏好。这大概是缘于这里适合养羊,也缘于这里的天气人们需要吃羊肉。每年的九月过后,到来年的四月间,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寒冷的。而十月到二月间,又是冰冻三尺、滴水成冰。这个时候人们出外,都要穿上皮衣,有的还要蹬上羊毛毡靴、戴上羊毛毡帽。要能吃一碗羊肉,既美味又御寒,那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了。四五月以后,也许是天气转热,羊肉又太热的缘故,也许是宰了羊,吃不完,存放成了难事,一直到九月之前,普通的人家也就没荤腥味可沾了。想沾点肉腥肉沫,又舍得掏几个铜钱的,只有到庙会上去吃。
由于人们的喜好,庙会上卖杂食小吃的总少不了羊肉、羊杂碎。尤其六七月份天大热的时候,平常人在家沾不上荤腥味,庙会上就卖得好。往日里卖羊肉、羊杂碎的依旧摆开摊子,支起锅灶,吆喝着招揽客人。细心的人们发现,这一回的庙会和往年大不一样。往年的小吃摊、铺,卖面的、卖饼的,卖蒸馍、卖年糕、卖粉汤的少了许多,显得有些单调。倒是卖羊肉、羊杂碎的多了起来。那逛摊买吃的的人和往年也不甚一样。往年年景好的时候,辛苦劳作了近半年的人们总要借赶庙会的机会串串亲戚,会会朋友。老人、娃娃和婆姨们也要打扮一新,齐聚到庙会上来。他们总免不了到卖吃食的摊铺上,捡自家不甚会做的和老人娃娃爱吃的,过过口福。小吃摊前,总是人群不绝,熙熙攘攘。今年却不同,摆小吃摊、铺的比往年要少,却也只是偶有老人带着娃娃们光顾,显得人气零落了许多。
二人们常说,有卖的总还是有买的。几个人掀开了韩家羊杂碎铺子的门帘,坐到了桌子前的长凳上。这是韩家铺子今天开张的头一拨客人,韩憨娃欣喜得心花怒放,赶紧让座迎客,下意识拿起手中不甚干净的抹桌子布在桌面上来回抹了一遍。
“哎哟,来客人了。几位快请坐,想要吃点儿甚?”韩憨娃高声让着客人,一是礼节上的招呼,一是给炉灶旁的婆姨打招呼,告诉她有客人到了,准备搭锅待客。
“韩家兄弟,不用歪文了。不就是卖一碗死肠烂肚子,还有甚好吃的呢?”
“嗨嗨……,这不是财神到了么!你们这是头一拨客人,给我光彩的哩。要吃点甚?尽管点,我这儿甚都备着哩。羊杂碎、嫩羊肉、羊骨食、糕、豆面还是荞面?”
“就吃羊杂碎吧。本来这天气热了,又旱得慌,羊肉是吃不得了,可还是想吃上一口。吃了又招不住上火。哎……,这个时候吃了这一口,谁晓得甚时候还能好好再吃得上。”
说话的人姓刘,叫刘喜贵,是寺前村的铁匠。在庙会上摆了个廉刀斧头锅勺之类的铁器家具小摊,让两个伙计叫卖。同来吃饭的就是他的两个伙计。寺前村就在庙的西南头清水川入黄河的口子处,只孤零零几户人家临水居住。一眼望去,村子跟前除过看得见摸不着的河水,就是悬崖巨石,无寸地可种。村子里的男人们有的从小在水里耍大,会几把水,靠着这黄河维生,也有的走村串户做些肩挑手推的生意。刘喜贵学了一手打铁的手艺,靠的是做些刀、叉、镰、斧铁器家伙维持生计。
“看你老人家说的,这方圆几十里地,饿得了谁也饿不到你刘大铁匠。再有多大的灾,你有那手艺,谁能离得开?上羊杂碎。要不再来碗面还是年糕?”憨娃一边说着一边高一点声给炉灶边的媳妇安顿着。
“先上羊杂碎,谁还想吃甚再要。这年头看来是要放个大年馑了,说揭不开锅就揭不开锅了。你看你这羊杂铺,往年时节庙会上多红火,谁不想来吃一碗。今年就不一样了。如今大半后晌了,也就我们几个人来捧个场场。有几个零钱怕也都想着买粮呀还是逃荒做盘缠呀,谁还有心事到这些场合零花。我那铁匠铺的炉火说不上哪天也得熄火了。还能想吃个甚!”
“哎呀,你师傅不开炉了,我们这些帮下手的可吃甚喝甚呀?”
“天旱了也不能不用刀、斧用具吧?”几个同来的年轻后生插嘴说。
说话间憨娃的媳妇已做好了羊杂碎,每人一碗端了上来。摆放在几个人的面前,说:“快吃吧,看调和行不行?”
“啊呀呀,那不是嫂子?!我们坐了半天了,也不见嫂子出来支应一声。”
“这不是就为你们几个忙着哩,外头有当家的支应着。快看看味道行不行?”
“行,行。嫂子调得准行。没个不行的。”刘喜贵的两个伙计嫂子嫂子地一边叫着,一边吃了起来。
韩憨娃住在寺后村。寺后村往西北与张家寨隔清水川相望,东边不远处就是海神庙,西南和寺前村隔着二三里地。寺后村虽说也只是乱石丛中住了几户人家,却比寺前村好了许多。寺后村村头有一股泉水,村子里的人在周围的沟沟岔岔砌出大大小小的石头堤堰,从远处运来黄土垫平,造出了几块园子地。垫土造出的地虽说都不大,有的小得巴掌大,只能插几棵葱,可有这股好水,寺后村人吃菜不发愁。有的还种上几畦胡麻,到秋来收了麻,麻籽换油。麻杆沤过后,剥了皮搓绳子,也能换几个零用钱。这水浇上的园子地,是寺后村几户人家的宝地,逢天旱年头,就是他们的救命菩萨。憨娃家也有几畦园子地。憨娃除经管这几厘巴掌大的园子地外,还养了一群羊,天天要上山放羊。临了庙会,杀羊支锅赶庙会,方圆一二十里的庙会上,总能看得见韩憨娃的羊杂碎铺子。
韩憨娃的父亲早年学会了熟羊皮、揉皮子和缝皮活的手艺,日子过得顺畅。憨娃长到十八岁,娶进了村里张姓家的大女儿巧巧做了媳妇。这巧巧的娘家和张家寨张家本是同族同宗,巧巧的父亲张榆生和张家生字辈算起来刚刚出了五服。榆生的老辈和老宅子张家老辈人一起做过生意,积攒了一些家底。子孙们却没守住家业,代代靠吃祖宗过日子。人说再厚的家底,只有出的,不见进的,只有败家的,没有持家的,富不过三代。到了巧巧的父亲张榆生手上,家里败落得没甚家当了,就在寺后村的北梁上买了几垧地,勉强度日。家随地走,人也就搬到了寺后村的北梁上住。张榆生也没甚本事,可生了一双花一样的女儿。大女儿巧巧从小和村里冯家的喜喜娃耍大,情同兄妹。喜喜家开着油坊,家里不愁吃穿用度。喜喜大巧巧两岁,人生得机灵乖巧。张冯两家都乐得两个娃长大后成了亲家。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喜喜的父亲一场病送了命,张家就再也不提两家要结亲的事了。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张榆生就盘算着给女儿找个不愁吃穿的好人家。他选来选去,看上了村里的韩皮匠家。张家在坡头上住,韩家在坡底住,相隔有几里地,相互没甚交道,不甚往来。可巧巧的父亲是个有心计的人,他看着韩家有几畦子水浇地,又养着一坡欢实的羊,还会一手皮匠手艺,一年到头东也请,西也叫,想着自己过的苦憔日子,觉得眼馋。他觉得韩皮匠的儿子憨娃人憨厚诚实,干活不偷懒,又不失机灵。巧巧许配了他日子总不会苦。只是炕上躺着个病婆娘,不晓得能不能好起来。榆生暗里叫人打听,憨娃还没说下媳妇,问了生辰八字,恰和巧巧相合。想着女儿寻上这么个人家,日子肯定差不了,就做了主张,托人打问这门亲事。憨娃的父亲知晓张家巧巧长得水灵乖巧,张家又是大门大户的支脉,乐得高兴,赶紧应下这门亲事。这韩家本是小门小户人家,没甚讲究;张家也穷得讲究不起来。韩家按常规请媒人,下聘礼,换帖子。接着就把人娶了过来。巧巧本有心上人,一千个不乐意这门亲。可拗不过父辈的安排,大哭了一场,进了韩家的门。
这巧巧不独人长得水灵秀气,性情温顺,还学会了做得一手好茶饭。巧巧的父亲日子过得紧巴,平时常带着女儿到张家老宅子去走动,希图得到张家老祖宗的怜悯和眷顾。同宗同脉,老宅子里远房的兄嫂姐弟们也不敢慢待了他父女两个。再说那张家老祖宗常姓老太太打心眼里喜欢巧巧那机灵劲,只要巧巧一来,这老祖宗总要说:“你看这小老命(老人对小孩的昵称)圪垯多心疼人,有甚好吃的赶紧去拿来。”巧巧自小就有心计,她觉着自己家做的饭没在老祖宗那儿吃得的香,去了老宅子就跑去灶房,瞅厨子做饭。不管是做年糕、擀豆面,还是炖羊肉、羊杂碎、烩豆腐,她都要问些窍道,记在心里。张家老宅院请来做饭的厨子看她水灵可爱,见她专心学人做饭,有时逗她说:“你看这么水灵灵的宝贝蛋,喜好上了做饭的营生,怪可惜了。”厨子们这么说,却也教了一些做肉烧菜的窍道。憨娃的父亲有那皮毛的手艺,这庙会上卖杂食小吃,就由憨娃和他的媳妇巧巧张罗。巧巧过门后没两年,就在庙会的小铺上操起了勺头。
俗话说,花艳了招蜂,人水灵了招人。韩家这羊杂碎铺子自从巧巧操了勺,真个红火了起来。有的到这铺子里吃一碗,真是觉得味道不一样;有的可就是图看上一眼巧巧那一张嫩脸蛋,叼空里说几句逗趣的话。
憨娃看着几个人吃着羊杂碎,又凑上来问:“都是出大力的,光吃这个怕不行啊。要不再来碗豌豆面?”
“行啊。就吃豌豆面,要嫂子擀得又细又薄的。”几个年轻的大声喊着说,分明是要那里边灶台边的巧巧也听到。
“好嘞!一人一碗豌豆细面。”憨娃高声叫着。
刘喜贵吃得碗里已剩不多了,放下筷子说:“韩家小老弟呀,你家里做的这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口味好。也不知甚时候再能吃上。先头你说饿不到我姓刘的,饿是照样要饿,别人家是存着粮不敢吃,就早早地挨上了饿。我这没存粮光棍汉一样的人可顾不了那么多了,能吃上就要吃饱,不做那看粮仓的饿鬼。你看眼下又不能耕地,又不用开镰,谁家还买个镢头、锄、镰干甚用啊。饿不死也让人等得闲得心慌死。”
“唉,说得也是呀。日子不好过!我们家这几十只羊,眼看没甚喂的了。就是有喂的也不行啊。羊这东西贱,吃百样草。开了春到如今羊放出去地里没草,光跑了道,不光吃不饱,还得掉膘。再过两个月不下雨真没法子了。这不,庙会上也就多宰了几只,可吃的人不旺啊。”
憨娃憨实,几句话就把这庙会上卖羊肉、羊杂碎多的奥妙端出去了。布帘子那边正在下面的媳妇听他这么一番说道,心里想,这个憨憨圪垯,一点儿也不老沉。这哪是做生意的人该说的话。她一边想着,一边把锅里煮好的豆面捞了出来,调上臊子,用盘子端了出来。随着巧巧端着豆面盘子走到刘喜贵几个人跟前,一股香醇的豆面气息扑面而来。
“哎呀呀,嫂子半天不出来,我们吃着怎没有一点点香味呀!”几个年轻人又说起调笑的话来了。
“不香?不香是没饿到。再饿饿保准吃着香。”
“有嫂子在这儿,吃得就香了。”
“热肉汤还没把你们几个的嘴烫得闭上。回去让媳妇把你们的嘴缝上。”
“哎呀嫂子,我还没媳妇呢,这可怎办呀!”那年轻的一个笑着说着又作了一个鬼脸。
“我们晓得,嫂子没那么狠心。”另一个接着说。
“行啦,行啦,少贫嘴滑舌吧,快吃面吧。”
几个人暂时息了口水,吃起了面来。吃了几口,又有人喊了起来。
“韩老哥哥,韩掌柜……”
憨娃就在跟前,他赶紧笑着问:“面没做好?”
“掌柜的,你来尝尝,这面可是少盐缺油,清汤寡水,没一星儿香味呀。”
“不会吧,你老人家才吃了那羊杂碎,羊杂碎又辣味又重,这面味轻些,口味还没倒过来吧。”
“老人家,老人家,我们还没那么大,你也不用装孙子。这面可真不够味,你看这臊子,尽是些山野(土豆)丁丁,这谁家家里不天天吃?”
韩憨娃听出了味道,这是嫌面里放的肉少。往年这几个人也常来吃,也是这么个挑剔劲。
“好,好嘞。给几个取点调和。”
憨娃话音未落,巧巧已掀起布帘子端出一碗碎羊肉。她也知晓往年庙会上这几个人的样子,已经预先切好了一碗细肉。
“来,各人碗里再和上一点儿,不用起哄了。”
“嫂子嫌我们起哄呀,我们可是头一拨客,坐了这大半天了,也没听嫂子一句好话。面不香有嫂子在跟前说几句可心话,这面也好吃下去。就不重给兄弟几个和和?”
“将就往下咽吧,你几个一人一碗的,也不知道哪碗不香。”
“我们刘老哥那碗也不香,都不香。”
“好啦,快吃吧。你们几个话也可以了。”几个年轻人起哄,刘喜贵在一边看热闹。这会儿插话阻止了他们。
“好,吃。刘老哥哥说了,将就吧。这冷也罢,生也罢,吃得不顶对(不舒服)了嫂子给我们看病。”几个人说着把筷子伸向碗里,夹起面往嘴里送。
“那可真说不好,死肠烂肚和死肠烂肚搅和在一垯(一起),说不定就不顶不对了。”
“哎,我们就爱听嫂子骂一声了。”
众人们多吃了几口肉,好像喝了两盅烧酒,话多了起来。憨娃站在一旁不说话,光憨笑。其实,他心里清清亮亮,这几个村里的邻居,人都厚道,却也爱说爱笑。他也知道,巧巧做的豆面谁家也比不了。
清水川的黄土地干旱贫瘠,却能长各样豆子。豆子种得多了,就成了人们的主要食粮。把豆子压成面,是他们的日常吃法。因此上,清水川的人家家家会做豆面。这做豆面却大有讲究,各家做出来的面大不一样。上好的豆面算是豌豆面,其次是小豆面。无论是豌豆面还是小豆面,和豆面的时候先要把沙蒿籽用水泡成糊状,用沙蒿籽水去和。面要和得硬,踩(揉)得到,醒得久,擀得薄。擀成的上好豆面像麻纸一样薄,白里透黄,均匀布满棕黑色的沙蒿籽。再将这麻纸样的面折叠起来,按各人的喜好,切成不同宽窄的面条。这样做出的面,吃到嘴里既有豆面和蒿籽的香气,又很有咬头。这种面不是一般人都擀得好的。既要擀得薄,又能切得细,能下到锅里,煮出一碗上好的豆面,绝非一日之功。连有的男方家找媳妇都要问一句女的会不会擀豆面。巧巧能做得好豆面,也难怪憨娃喜孜孜在一旁憨笑了。
“唉,我说韩家兄弟,你看今年这年馑,已然是放下了。凭你家那几只羊也难养活家里那几口子人。你大大(爹爹)那手艺,这个时候说没营生就没营生了。你有甚打算?”刘喜贵吃完了面看着憨笑着的憨娃说。
“嗨,嗨,我能有甚打算呢,走一步看一步吧。”憨娃憨笑着说。
“你心里没个盘算?我不信。跟我的这俩哥们兄弟如今看着也没甚营生了,铁匠炉子迟早要关门熄火,他们都打算出去了,你就没找几个兄弟商量出去走走?弄好了兴许还能赚几个回来,再不济也混个饱肚子,给家里腾出些口粮来呀。”刘喜贵不紧不慢地说。
“刘叔你走到哪,有手艺,也有亲朋,饿不着。我呢,两眼摸黑,又没手艺,除过种地放羊,还能做个甚?出去也找不着个好活路,和在家饿着还不是一个样!”憨娃还是一脸憨笑,神情中露出一种无奈。
“看你说的甚,放羊也是手艺。我可走过口外,早些年我去过大佘太、小佘太,那里养的羊就多,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家是骑着马放羊。出去寻个放羊的营生还用愁?只怕是舍不得离开媳妇吧。”刘喜贵的一个伙计接着说道。
“哪里的话啊,我不是没盘算过出去的事。你看,老妈跟前离不得人,老父又常不粘家,我真不晓得该怎办。”憨娃急着说。
“你大大那手艺也是几天的事。如今不下雨,谁家也没心事喂羊了,这几个月羊杀得多,你大还能有几天营生?过些时候谁家还熟皮子、铲皮子?说没营生就没了,迟出去不如早动身,还能给家里省几口粮。”刘喜贵的另一个伙计接着说。
“唉,那倒是。”
“盘算好了,要走就找几个兄弟一垯走,说不定路上还有个呼应。”
“嗯。好,好。”
韩憨娃和刘喜贵仨你一句我一句说起了走口外的事。说到了走口外,众人那说笑的闲情也没了。铺子里一时少了刚刚那说笑逗乐的气氛,不时听得见几个人在叹息。张巧巧开始还和几个年轻人吊嘴,听着两个人说走口外的事,转过身掀起布帘子坐到灶台边的凳子上,双眼发起瞠来。一会儿成串的泪珠儿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