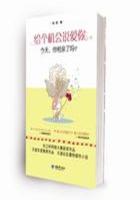“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装什么狐仙!”驸马撩起衣袍坐在了太师椅上,抖展开衣袖,气定神闲地说:“沙茶酒馆每日出入的江湖人有数百人之多,大多数都是冲着老掌柜数十年间在江湖上积攒的好名声而来。如若大家知道,沙茶酒馆的掌柜小姐无视道德和正义,一味地隐瞒真相、偏袒恶人,使得恶人逍遥法外,无辜的人蒙冤受辱。你觉得沙茶酒馆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生意兴隆吗!”
赵四小姐浅笑着说:“驸马爷有些病急乱投医了”,一双吊梢眼平静地将一诺望着,“从小我父亲就教导我,听人说话,要捡着听。不能全信,不能不信,要从谎话中推测真实情况,更要提防真话。因为有人会用真话来诈你的真话,更有些不择手段的人会用假话冒充真话来诈你。”
听完赵四小姐这番话,一诺立刻忍不住扪心自问,对数日前诓骗她的事愧疚不已。
赵四小姐回过身来,对驸马说道:“驸马爷您说得头头是道,那您为什么不替自己鸣冤?”
驸马双手撑着椅子慢慢站起,努力地压制住自己的情绪,眼中冒火地望着赵四小姐,“怪不得我今日一进门,你就给我来个下马威,敢情赵四小姐是下了决心要让我蒙受不白之冤,锒铛入狱了。”
赵四小姐不气不恼,语气和缓地说:“驸马爷既做得出那些有悖纲常伦理的事,作何怕身败名裂呢。”
驸马被赵四小姐这么一刺激,只觉得全身的血液一瞬间都冲上了头顶,他不再避讳众人,直白地说道:“赵四小姐既然早就谋划着要置我于万劫不复之地,那么当日,琴师死后,又为何费尽周折地托人与我传递书信。不止在书信中表示,若安在禄被害,定会力证本爵爷的清白。更嘱托来送书信的人,据实表露你的衷心。想不到,你……你……翻脸比翻书快!”
赵四小姐听完先是一愣,继而撂下茶盏,说道:“驸马说得言之凿凿,字字掷地有声,故事跌宕起伏,竟比说书先生技长。”
“你!”驸马被她气得直捶胸口。
“信呢?”赵四小姐不依不挠地说:“嘴巴长在您脸上,黑白不都是由您来说!驸马爷不如拿出真凭实据,免得为了一时口舌之争,气坏了身子。”
“哪还有什么书信!”驸马气得嘴皮颤抖,“我读完书信后,就被来送书信的人当场给焚烧干净了。”
赵四小姐冷笑一声,悠悠地站了起来,拍拍衣衫上的褶皱,说道:“既无书信,那就是驸马爷信口开河了。”
说着就抬起步子往外走,走到包厢中间时,转身说道:“驸马爷说的作证的事,我并不知情。这酒馆不过占了数亩大的地方,又是薄墙残瓦,既吞不下街头巷尾的风言风语,也咽不下驸马爷的似海冤屈……”
一诺打断道:“这样就下结论还太早!”
就在赵四小姐和驸马争论不休时,一诺已经把这些事在脑子里理出了个大概——驸马方才说的那番话已经很明白了,赵四小姐曾先前向他透露过愿意挺身力证他的清白,也正是因此,驸马才大着胆子将自己引到了沙茶酒馆来。可赵四小姐却一口咬定没有答应作证的事,他二人个个说得都是凿之有据,那么问题可能出在那封书信上。而传递书信的人,大费周章地做这些,或许是因为他有挺身而出为驸马作证的打算。
一诺提议道:“既然在你二人之间有传送书信的第三者,不如寻来,说不定他才是真正想要为驸马作证的人。”
驸马“啪”一声拍案而起,“是个男人”,驸马伸出食指冲在一旁听得认真的店小二指了指。
店小二立刻像踩着老虎尾巴了似得弹跳开来,众人更是惊愕不已。
驸马翻了个白眼,继续说道:“不是他!那个男人,脸方方的、眼睛大大的、高挺鼻子、薄嘴皮。年纪约莫着有……一大把了吧,或许没有那么大,反正头发全白了。骨骼精奇,走路虎虎生风,功夫极深。他的言谈举止间,有种不经意地从骨子里散发出的江湖游侠的侠义气质。”
驸马说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赵四小姐,心想:“臭丫头,那****信里写得好一副赤胆忠心。没想到,到了节骨眼上,你居然反悔。幸好是来了个杀手,若是在庭审大堂上,岂不被你坑死。你最好把人给我藏好喽,若让我找出来,我定要把你的不仁不义大肆宣扬一番,让你酒馆名声扫地,最好关门大吉!”
而这时,赵四小姐听完驸马的这样一番叙述后,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论是从那送信人的相貌、他的一身侠气、胆量,还是从他做的这一桩事来猜测,都太像一个人——赵四小姐的爹爹,以仗义救急名扬五湖四海的赵升。
赵升多年不曾在江湖上露面了,驸马这样的后生都是只听过他的名声,并未见过真身。
可是店小二见过!
赵四小姐心里正纳闷他爹爹遁世那么久了,怎么会突然现身呢。正想着呢,余光看到店小二两脚划拉着地面,正小心地一步一步向自己靠了过来,心里顿时一惊:“这个没有眼力劲的蠢货,不赶快堵上他的嘴,怕是就要把爹爹给抖搂出来了。”
店小二动了动嘴皮,还未出声。
赵四小姐抢先一步说道:“驸马说的人,我未曾见过。”
店小二两眼瞪得跟铜铃似得,直到赵四小姐瞪了他一眼,他才晃了晃脑袋,心有不甘地垂下了头。
赵四小姐和店小二之间的异常举动很快被一诺察觉到,“赵四小姐,请留步!”
一直在一旁冷眼观望的苏辰快步走上前去,拦住了一诺,他紧攥住她的手腕,说:“酒馆还要营生,赵四小姐已经陪了二位多时。若言姑娘有什么话想要问的,问我是一样的。”
赵四小姐抬脚出门,驸马立刻将门关上,质问苏辰:“尧,你怎么能放她走呢!你没看到她朝店里那个伙计使眼色吗?她肯定知道那个人是谁!就是不肯说,摆明了要跟本爵爷做对!”
一诺望着苏辰缠着手的纱布上渗出的血渍,说:“你是怕我对她做什么吗?”
苏辰说道:“隐云说过,被施了幻术的人会出现间歇性的失忆。”
“松手吧!她已经走了!”一诺一把将他甩开,转过脸去,她实在无法那么近距离地望着他为了别的女人泛红双眼。
驸马没好气地说:“都这个节骨眼儿了,你们还在这儿打情骂俏!若言姑娘,不如本爵爷再送你一处与尧一样大的五进五出大宅,你直接把安氏给我剁了!免得她等不到我招她过门,奔了府衙去告状,坏我名声!”
“你的名声比别人的性命还重要吗!人命关天,在你们眼里就值一处宅院吗!”苏辰气愤地说。
一诺知道苏辰这是指桑骂槐,心里气愤他刚才的举动,也不理会他,对驸马说道:“除了送信人,不是还有一个证人吗。走吧,不要在这里浪费光阴了!”
驸马紧跟着一诺出了沙茶酒馆,不停地追问:“还有一个证人?”
“安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