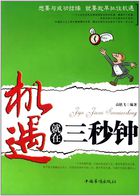因为刚刚成亲,府里总是宾客不断,闭门思过的事也就一推再推,这倒是给了他二人朝夕相处的机会。
何家自少卿父亲那代起开始经商,但是古人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老夫人从小就聘了先生终日教导,以图他能够有朝一日光耀门楣。
少卿天资聪颖,又勤力,倒也没有辜负老夫人的期望,小小年纪就考中了秀才,还是头榜头名的秀才。
一诺虽然读了十几年书,也算是学富五车了,但是见过他的字画和文章后,心中直呼自愧不如。
一诺一边吃着点心,一边偷偷地瞥了少卿几眼。
这个将她带入这个新奇世界的男人不仅会“发光”,还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最要命的是只单单对她呵护有加、体贴入微。
想到此处,她小声嘟囔了一句:“真是要命啊!”然后伏在桌上嘿嘿地笑。
少卿放下书,望着她说:“你吃这么多,当然要命了。”
“我这是在储粮,过了今晚,明天、后天、大后天,都要挨饿,所以赶快让厨子再做点点心,我肚子还能再装点!”
“你放心,我会偷偷给你送饭的,饿不着你。”
“别,您老可放过我吧,我可不想被乱棍打死。”说完,又往嘴里塞了一块芙蓉糕,两个腮帮子都撑得鼓鼓的。
一诺就这么断断续续地吃到了日落,吃完之后在院子里晃荡了会儿,最后忍不住蹑手蹑脚地走到少卿身旁,小声嘟囔:“好像……有点撑着了……”
少卿看看天色还早,便说带她出去走走。
一诺听了,头点得像捣蒜似得,脸上露出一个极其阳光、温暖的笑容。
他们穿过一条笔直的石板路,路两旁的商贩高声叫卖着,那古老的腔调让一诺有些沉迷,每家小铺的门前都挂着泛着点点烛光的灯笼,一排排灯笼串成一道暖暖、柔柔的光带。
一诺在心里暗暗想着:“和一个温文尔雅的古人,在这古老的年代,谱一首唯美的恋歌,实在是太棒了!”
她忍不住回头偷偷看少卿,他正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帅气的侧脸被烛光照得分外硬朗。
“我们去泛舟吧?”他突然蹦出的这么一句话,让一诺有些心惊。
她可是从小怕水的,但是看着他期待的眼神,她只得默默地点头。
那是一只很小的船,只够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
少卿坐在船尾,握着两个桨,偶尔划一两下,神情有些焦虑。
一诺比他更焦虑,她一直小心地看着船的四周,船身很低,总觉得河水要没进来了似得。
她努力克制了一会,终于忍不住对少卿说:“我们上岸吧,这里没什么可看的!”
“不会啊,待会到了前边入湖的地方,划过漩涡后,有一处世外桃源呢。”
一诺听到入湖、漩涡后,咽了咽口水,两只手死死地抓着船沿,静默了一会后,再也坐不住了,“这么晚了,还是回去吧,奶奶会着急的。”
“晚了!坐稳了!”
一诺听见这话,猛地回头。
一个比船还大的漩涡赫然出现在眼前,她两只手一下就捂住了双眼,漩涡带着小舟旋转起来。
一诺直接被甩了出去,“扑通”一声溅起了一片的水花。
她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岸上了。
少卿紧紧地抱着她,眼神慌张。
她感觉到肺、鼻腔里都是水,挣脱开他,伏在地上干呕,她痛恨这种窒息的感觉。
那一夜,她蜷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
梦里她仿佛又回到了两岁那年——她跟着哥哥玩,哥哥嫌她浑身脏兮兮的,想给她洗洗,就把她扔进了门前的河里。
后来的很多年,她都回忆不起当时是如何上岸的,但是那条河、那条河上架起的桥、那条河周围的树,甚至那几棵树是怎么交错着种的,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这是她最早的记忆、这恐怖的记忆,这记忆使得她在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仍然不敢用浴盆洗澡。
少卿躺在她身旁,紧紧地搂住她颤抖的身体,不时地为她拭去额头渗出的密密汗珠。
这天下午的时候,有旁观者偷偷地警示他:“行为举止可以模仿,更何况若她是莫黎,想要模仿一下朝夕相处的妹妹绝不是难事。她们样貌又极其相似,稍加修饰,便难辨真假。”
虽然他的内心是偏向她的,但是他还是有诸多的犹豫。
“那么,唯一能够辨别真假的就剩下了这最后一个法子了!”这就是他陪一诺逛街时为什么看起来若有所思了,当时他正在筹谋落水事故。
本来计划是小船撞在礁石上,一诺落水。但是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帮了他一把,一诺自己没扶好,不小心坠入水中。
这样落水事故就和他撇清了,但是他心里并不轻松,尤其是在他掀开衣衫看到那道刺眼的旧伤疤的时候。
在何府,人人都知道少爷对莫淇痴心一片。
少卿待莫淇如何,从她和莫黎的性格就可看出一二——同样的凄苦经历,莫黎成长得冷若冰霜、心狠手辣,而莫淇却恰恰相反,一副菩萨肠,一张暖心脸,这性格很大程度上都要得益于少卿的呵护有加。
就在莫家姐妹进入何府的第三个年头,扶城突然流传出莫黎与殷家戏班的小生有染的流言蜚语。
这等败坏门风的事,老夫人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将莫黎找来,质问她传言真假,她自然抵死不认。
她在何家住了那么多年,老夫人知道她胆大、聪慧,看唬是唬不住她了,只能上家法。
当家丁把莫黎从椅子上拖下来时,莫淇看着已经痛晕过去的姐姐,受不住了,她给认了。
老夫人也不是老糊涂的人,找来那小生,当场质问,到底是哪个姑娘与他私定的终身。
戏子无情,那小生见莫黎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了,心里琢磨这何氏宗亲在扶城,可是只手遮天的,不好惹。若坦白了,别说莫黎了,只怕自己的性命都难保。好在兰心事先与自己通了气了,便一口咬定是莫淇主动勾引的自己。
站在一旁的少卿,静静地听完这一通话,脸黑着,拽着小生的衣衫拖到莫淇面前,怒气冲冲地问:“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这种登徒浪子,背信弃义的小人,你说,你喜欢他什么?”
莫淇不做声。
少卿对小生说:“你既然有胆动我的女人,也该已经备好了万全的对策吧!哼,今天落到我手里,我就不能让你囫囵个儿地回去!把他给我绑上!”
几个家丁抓着小生的手脚,将他摁在长条凳上,再用麻绳拴紧。
小生一看这情形,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少卿喜欢的是莫淇,自己这是被兰心给摆了一道,稀里糊涂地被人当了棋子。只是少卿一往情深,护莫淇心切,不仅不能把她拖下水,自己反倒可能会命丧当场啊,忙喊道:“我还有话要说!”
“你别再说了!”莫淇一嗓子给他的话吼了回去,她怕这懦夫为求自保把莫黎供出来。
她一边用身体护着他,一边哀求少卿:“求您放了他吧!”
少卿看着她眼泪汪汪的样子,更气了,从家丁手中夺过鞭子,一把将莫淇拉开,“今天我就替你收拾这个污损了你名节的畜生!”
小生一边求饶,一边嚷嚷着还有话要说,少卿以为他又要不知廉耻地把责任都推到莫淇身上,怒吼着:“还不把他的嘴堵上!”
家丁走过去将他的嘴掰开,塞了布条。
小生挨了十几鞭子后,已经没有力气挣扎了,满脸的汗水和眼泪,心里冤得狠,嘴里呜呜咽咽的想说话。
少卿气得浑身发抖,小生一出声,就换来重重的一鞭子,慢慢的他也就没力气哼哼唧唧了。
眼见着小生的后背被打得血肉模糊,脑袋耷拉着,嘴里的布条都有了血色,眼瞅着就要被少卿活活打死了。
莫淇突然扑过去护住他的后背,少卿一时没反应过来,一鞭子抽在莫淇肩上,瞬时白色衣衫就渗出了鲜红的血迹。
自从那件事发生后,莫淇就开始有意疏远少卿,少卿常常悔恨自己当时太过多疑。
一诺的身体抽动了一下,少卿这才回过神来,看着她在熟睡中仍然皱着眉头,身体不停颤抖的样子,他的心更痛了,将她搂得更紧了。
一诺身上的那道旧伤疤不仅取得了少卿的信任,还快速地堵住了何府里的丫鬟、家丁的嘴,她在何府的日子这才稍稍有了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