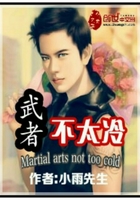接着是另外一个男声:“广仁兄你喝多了,坐下来醒醒酒吧!”
只听那声道:“我没醉!我、没、醉!子美兄,你说你,那么厉害,状元郎,为何不把公主许配给你了?为什么要给我?难道他不知道,我最喜欢、最爱的,只有绿蚁吗?”
接着是那个男声吩咐小厮的声音,太低听不清楚,估计是在点菜吧。我只是好奇,那个绿蚁,绿蚁的,到底是什么酒呢?这么好喝吗?只待莲心她们吃完饭我就要问问的。
正待开口问的时候,银花已经吃的肚儿圆圆擦过嘴了。她指着桌边墙上的一段字说:“小姐,这是写的啥啊?”
我本不欲理会,奈何总是要看看到底是啥的,走到近处,只见上面写着:“求写酒诗一首,写的好的免去席钱。”
看得我不禁笑出声儿来,对着莲心说道:“哎呀,怕是这顿饭钱,不用付了。”
她听了笑笑便下楼去了。不一会儿拿回来一张纸并一支笔,我想了想,提笔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然后戴上面纱,携了银花的手,一边走下楼出去。
到了酒肆不远的小摊跟前,看看商贩卖的花花草草,不多时莲心却已追上来,笑道:“掌柜的不住口的夸奖了,说是很是风趣,有雅意!还问我,女博士可还在?不才诚心还想请教一二了!我赶紧推脱了才走。”她眼底都是笑意,看来,对我是越来越认可了的。
接着逛完这豫州城大大小小的成衣坊,我也陆陆续续买个几匹布,银花和莲心都有些拿不过来了,快天黑的时候才慢慢往回赶。
快赶到小角门儿时,看到吴广站在门口的气死风灯那里,见我们回来,赶紧接过银花与莲心手中的布匹,进来院子落上锁。收拾一番又是吃晚饭,无甚新意。
吃过晚饭吩咐莲心,我要泡澡。不一会儿,便有几只木桶,抬了热水到一楼的卧房间壁,更衣的地方,我舒舒服服的泡了澡,莲心还为我洗了头发。
洗完澡,披散着头发,在二楼,与银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继续拿着特制的画笔,画着画儿。
画着画着,画风突变,连现代的短袖都出来了,不是银花提醒我接下来不知道还会画出些什么。我只好睁眼说瞎话,告诉她,不是没了袖子,而是外面还有一件镂空的纱衣,披在外面,看不出来罢了。她听了依旧一脸的崇拜之意。骗小孩儿,果真简单。
次日清晨,发现没了画画的纸,便让莲心吩咐吴广去买些回来。
哪知到了中午,吴广竟然带回来一个令我哭笑不得的消息:说是昨日午间,有一个花容月貌似是天女下凡的女子,在醉仙酒楼写下一首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现在整个豫州城都传遍了,已经是豫州纸贵了,甚至很多店家都断货了。
吴广买回来的都是最后剩下的几叠纸了。说是很多造酒的作坊都说,想花高价钱,请这位姑娘为自家的酒写一首诗了!就是不知道给绿蚁酒做了诗的姑娘,要价几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