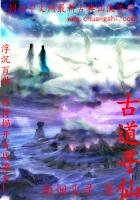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
无殊深吐一口气,将怅然思绪抛开,加快速度将碗碟洗好,塞进消毒柜,然后走到一边,正准备把窗帘拉上,眼角余光却瞥到了楼下。
栖息在夜色中的布嘉迪威龙,因它招摇的车型叫人无法视而不见。如此明目张胆地昭示,也只有那个人做得出来。
她刷地拉上百叶帘。
心口又隐隐地痛了起来。
无人的客厅里,电视仍在播放着少儿节目。无殊紧张地叫了声:“北堂皓。”
有个声音从小阳台上传来,“我在这。”
北堂皓倚在雕花扶栏上,伸出手将走近的她拉进怀里,不满地说:“你总是连名带姓叫我。”
“叫什么呢?大耗子好不好?”
他笑了笑:“那以后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叫小耗子?”
无殊红了红脸:“我还没嫁给呢,你就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他抓起她的手指说:“戒指都已经套上了,可不准耍赖。要是嫌我想得远,我们明天就去见老爷子。”
她将头靠在他的脖颈旁许久。
“阿皓。”
“嗯?”
“忽然觉得很困。”她闭上眼,不去思考心悸的原因。
北堂皓揉揉她的头发,说:“累了?去泡个热水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