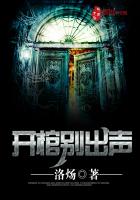一个月之后,九月八日,饶有兴要去省城读书了。七日,饶有兴家里象过节一样的热闹。亲朋好友前来贺喜,隔壁邻居也提一些鸡蛋、蔬菜的前来祝贺。饶家摆了几桌升学酒,宴请大家。隔壁邻舍的孩子们也不知他家干什么事,纷纷来到他家的门口跑来奔去凑起热闹。
村支部、村委会为鼓励山沟村民的子弟努力学习,多出人才,前年就出台了凡本村的村民子弟考上大学的给予奖励的政策。今天村里出了个大“秀才”,这也是全村人的光荣。村书记、村主任代表组织和全村人民也来了,还送来了大“红包”。
饶富贵的家,村主要领导平常都没有来过。这老实巴交的饶富贵,多年来,看到村里的领导都不敢说话,今天两位领导登门拜访,他也仗着儿子上大学,成了国家的人,壮起胆、张开缺门牙的嘴巴,瘸着腿上前拉起村党支部书记就往堂上的上席座位上走。近一点的本家看到书记、村委主任来了,也都从座位上站起来。饶有兴也在堂前堂后不停地接客帮忙。看到两位主宰全村人民命运的“贵客”来到。虽然为田水灌溉之事与他们心中有很大的不快,与村主任还饶了口舌。但毕竟是村里的‘皇上’,得罪不起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也不去计较这样的事情,自己虽然要离开家乡去读书,与他们接触相对要少了。但父母还在、根还在,他就迅速迎上前去。
对饶富贵来说是估计不足。厅堂上席座位已有坐主,两位长辈来客自然坐定。村里“皇上”突然到来,主人热情非同一般,来客自然明白,上席位子理应让他来座。两位长辈有自知之名,迅速站起来,让村领导入座。村书记被饶富贵拉去上席坐了。村主任看到饶有兴走来,就走上前一只手搭到饶有兴的肩膀上,拉着他往门外走。在大门外边上没人的地方:“有兴啊!你那天走了以后,我就和乡干部小马到了你家田的现场,看到之后,我们一致认为饶世有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无理的。并找到他,要求他把灌水渠重新恢复起来,这是乡村干部的处理意见。现在已经恢复好了吗!饶世有这人是有点不讲道理,你知识分子也不要和这种人一斑见识。”
饶有兴把村主任看了又看,好像他是另一个人似的。一月前不是叫我用抽水机到下游抽水来灌溉吗?不是在批评我小毛头不懂道理吗?这么快也改变观点了呢?!但口中仍说:“麻烦您们了,谢谢!谢谢!去喝酒。”他说着,拉起村主任往厅堂走去。
饶喜子当了多年村书记,见过一些场合,能左右一些‘局势’。在自己的村民面前,要应付这种场合,也算是小菜一碟。饶富贵拉他坐在上席时,他一定拉住饶富贵和自己一起坐上席。饶富贵从没有这么近距离接触过村领导,坐在座席上也不知说什么,脸上露出了拘束的、很不自然的笑。大家相互客套一番之后满上酒,饶喜子喧宾夺主,站起来说:“你辛苦,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儿子,我借花献物,代表村两委先敬你一杯。”书记站起来敬酒,饶富贵更是手足无措,慌乱中筷子也被碰到掉在地上。
酒席中,大家相互敬酒、又高谈阔论,另桌几个年轻人不忘农村酒桌特有的娱乐形式,五呀六啊、全来到啦,竞猜起拳来。大家热闹了好一阵子,才渐渐回家。饶有兴送书记、主任到门口,书记说道:“明天叫两个小青年帮你拿下东西,你老爸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也就不要让他去了。”村书记的关切到了极点上,使饶有兴感动了好一阵子。
“不麻烦、不麻烦,谢谢书记!”饶有兴一边说,一边在想:我只是去读书,也不是当什么大官,何需这么大动干戈。
“那渠道已经恢复原样了吗?!”书记好像带问又是告诉饶有兴的语气说道。
“谢谢!谢谢!麻烦大家了。”饶有兴一个劲地谢谢领导。
饶有兴送走客人后,想起上午饶仙花托一小朋友给他的字条说,晚上在村口的大樟树边等他,有事要找他商量。
去还是不去呢?犹豫了好一会。去吧!他在自问自答。于是就往村口走去。
夜深人静。弯弯的月牙儿特精神,亮亮晶晶;对面门头山的雄姿在朦胧中影影绰绰;她站在村口风水树——千年大樟树旁,亭亭玉立,不停地眺望着村中的路口。
“我估摸你不会来的?”
“这不又计算错了。不能用传统的方式解现时的东西。”过去,两人在一起学习时,他常用‘这不又计算错了’来问她,今天又说了这句话,在饶仙花的心中感到有点亲切。
两人沉默一会。
“如果我真的不来呢?”
“我一直等到你来的时候。”
“等多时了?”
“嗯!”停了一会又说“一会儿。”
“单项选择,就不要多项选择。这样不就又做错了?”
“我犹豫,拿不准该选哪。”
“有事?”
“没事。你明天走了?”
“嗯!”
“坐啥车?”
“到县城坐火车。”
看她用手擦了擦眼睛。
“你哭了?”
“没有。”
“我心中难受。”
“那你打算咋办?”
“听天由命。”
“不!要与命运抗争。”
“我爸是粗人,你不要与他计较。为灌溉事,我骂他损人利己,贪图小便宜,没有眼光。我代表全家向你道歉。”
“农村人就是这种小农经济,要理解。过去的就不要再提起。”
“给你造成了损失,补偿你一点。”
“不需要!不要说这些了。”
“也许是他这种眼光,影响了我的学习,给我造成今天被动结局。”
“外部原因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内因。你要在内因上多找找。”
饶仙花今年未考上大学,她把一肚子的“火”全倒在她老爸身上。她认为,为灌溉之事与饶有兴家产生矛盾,饶有兴从此不理会她,两人在学习上没有很好的交流,她又老是想着这件事,致使她在学习上分散了心、退了步,而没有考上大学。这也许有几分的理由,但不是主要的理由。饶有兴已经说到位了。
饶有兴考上大学,来了通知书。在饶世有的心中:饶富贵这个屁都打不出一个、一生没有一点光耀,村里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今天却养出了一个儿子考上大学、出人头地,成为国家的人。没用的父亲却养出了了不起的儿子,这是为什么?可能是他饶富贵一家心地善良,上帝‘恩赐’于他、保佑于他的结果。又看那村书记、村主任,村里的村民都前去贺喜,饶富贵在全村人面前真的挣足了面子。饶世有回想到自己的女儿在都里乡读初中时,在学校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到了高中毕业,却最差的大学都没有考上。她骂我损人利已,难道真的是“天”对自己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惩罚吗?是对自己的一种报应吗?果有这么灵?也来的这么快?他想到这些,在女儿对他发火时,他也不作声,更不敢骂她。自己主动提出让女儿继续复读,争取明年考上。一边又偷偷地把原被他挖掉的小渠道重新恢复起原样。
“我明天送你到车站可以吗?”
“算了吧!免得他人多舌。”
“那我一定来送你呢?”
“浪费资源!除此没有什么收获。”
“你原来的一些复习资料送我行吗?”
“你认为呢?”
“我不知写议论文还是写记叙文?”
“只要写得好,何谓议论和记叙。”
“没别的事我们就回去吧!”
“这个送给你。”饶仙花拿出一个信封给有兴。
“什么?”
“回去再看吧!”
“当面讲不是更好吗?!有什么问题我可直面回答你。”
“只能回家看。”
当饶有兴回到家时,同学吾洪才问他这么长时间到哪里去了?至于饶有兴到哪里去,吴洪才心里多少是知道一点的,但还是有意地问了这个问题。吾洪才可谓是饶有兴最亲密的同学加朋友,他家住都里乡都里村,家境与饶有兴一样属于“扶贫”对象。两人从初中到高中足足在一起六年,可谓是阴影不离。他们能够结下如此兄弟般的友谊,很大程度上是“贫穷”里面的共同语言促成的。由于富家子弟一般与贫家后代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也很难相处在一起。遗憾的是吾洪才今年高考,仅差九分,而名落深山。
夜已深深,两人躺在床上,还没有睡意,先谈的是饶仙花的事。饶有兴说不要谈论这件事,商量的还是吾洪才今后的去向问题。饶有兴要吾洪才去复读,争取明年考上大学。看他今年的成绩,明年完全能够考上。吾洪才说自己的家境与饶有兴的家好不了多少,不要说家里不可能同意他去复读,他自己也不想去挤这条独木桥,弄不好掉下河,还要淹得半死不活,决定要去赚钱减轻家庭负担。这又是一个既懂事,而眼光不远的农村孩子,有了这种想法,所以他复读的可能性没有。吾洪才自嘲说,人家不是说我“我无才”(吾洪才和‘我无才’有点谐音)吗!恐怕命中注定我不是这块料。我想去做点生意,现在做生意的比较多,就是家里缺少资金。两人谈着谈着,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饶有兴去上学所需生活用品昨天基本收拾好,今天起了大早,从书堆里找出过去的一捆复习资料,拿出三百元钱给母亲说,这是从饶仙花处借来的钱,要母亲在他走后还给她,一并把这些书给她。吃过早饭之后,吾洪才帮他挑上行李,前面开路,他手提着一个装有生活用品的包,走出了这个家。母亲跟着儿子,送到村口,还是舍不得回去。饶有兴叫母亲回家,在转过身时,看到母亲揩了揩分明是闪出泪花的眼睛,又看到母亲那饱经沧桑、刻满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心中不免一阵难过,叫了一声“妈”说,“我去读书,您应该高兴啊!我放假就回来。”
“我高兴,我高兴。”母亲说着,泪泉就像决堤的坝,却怎么也止不住。饶有兴用手把母亲擦着眼泪说,“我赶车去了啊,你回家吧!我到学校就写信回来。”此时的饶有兴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咬了咬舌头转身而走。
到了都里乡汽车停靠站,饶有兴叫吾洪才回家,自己一个人去火车站,便从包中拿出出乎他意料的“预算外”资金,村委会奖励的五百元钱(相当于当年国家二十三级干部一年的全部工资),给吾洪才说,“不管你是复读还是做生意,这点小钱帮不上什么大忙,你还是先收下。”两人推来推去,汽车已经来了。
改革开放后,农民从烂泥田中爬上来,办起了企业,跑起了码头。小小县城火车站,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肩扛背驼塑料袋、编织袋的农民,带着农村人自制的商品准备外出销售。
饶有兴旧貌换新颜,一手提只小皮箱、一手生活用品。穿戴不算华丽,也是一派学者的风度。与这些肩扛背驼、挤得满头大汗的人群,看得出不是一个群体的。
他差不多是在最后面走过检票口,便舒了一口长气,习惯性地回过头。看看这个原挤满乘客的车站候车大厅,现在已经空空荡荡,也好像是要多看看这个城市,心中在想:家乡,我去省城读书,要离开你一段时间。在他回头的瞬间,透过候车室那硕大的玻璃窗,一个熟悉的身影,亭亭玉立,昂头在张望。她咋会来呢?你真是个傻姑娘,他的心里又是一阵难过,继而迅速地转过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