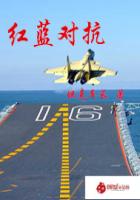话说秃尾巴狼何虾在砖窑被深山虎石岩的飞刀割掉了鼻子,仓皇逃回炮楼。炮楼里的鬼子把他臭骂了一顿 ,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鬼子的脚上穿的是高级皮鞋,外边看不出,皮鞋的头儿上还内包了铁皮,踢到老槐树身上能踢下碗口大的一块树皮。这一脚踢到秃尾巴狼何虾身上,他那里受得了,直踢得秃尾巴狼何虾呲牙咧嘴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县城里的伪军警备司令官阴山狈刁士贵听到报告,当即撤消了秃尾巴狼何虾的皇协军小队长职务。
曾几何时,在花虎庄炮楼里一跺脚,炮楼都要晃三晃的皇协军小队长秃尾巴狼何虾,一下子掉进懊恼、沮丧近乎绝望的污水坑里。他不甘心就这样沉没,绞尽脑汁思索生存的出路,瞪大眼睛寻找救命的稻草。
有门儿!秃尾巴狼何虾想到了他的干爹笑面虎白有财。这个消瘦的像匹饿狼一样的干巴老头,却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大女儿野菊花白凤委身于在县城当皇协军大队长(有的人也称呼他县城警备司令)的刁士贵,外号人称阴山狈。
二女儿白娥在保定学堂念书,听说和二十九军的一个排长打得火热。不过,到底花落谁家尚无定论。
如果让干爹笑面虎白有财出来说句话,阴山狈刁士贵不能不听。或者求干姐姐野菊花白凤在阴山狈刁士贵的枕头边吹吹风,也必然有效。
秃尾巴狼何虾不敢直接去找他的干姐姐野菊花白凤。因为阴山狈刁士贵知道他的底子,知道他秃尾巴狼何虾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况且在野菊花白凤嫁给小王庄的痞子丧家犬何郎之前,就是秃尾巴狼何虾的老相好。
后来,野菊花白凤见风使舵又跟了伪军大队长阴山狈刁士贵。丧家犬何郎装聋作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了个伪军中队长当。秃尾巴狼何虾就更不敢再和野菊花白凤来往了了。
如果现在让阴山狈刁士贵知道了自己和干姐姐野菊花白凤那段旧情缘,哪样或许会把事情弄砸,雪上加霜。最佳方案就是求干爹笑面虎白有财出头,肯定能行。
秃尾巴狼何虾把两支长白寿参和两瓶地道的山西汾酒往笑面虎白有财面前一放,小老头的眼睛就眯成了两条线儿。
秃尾巴狼何虾说:“炮楼里忙,好长时间没得顾上过来。心里结记干爹的身体,来看看您。”
笑面虎白有财伸伸胳膊表示身体还算结实。说:“没事,干爹结实着哪。”他一指秃尾巴狼何虾横缠在脸上的绷带。不解地问:“那是咋么啦?”
秃尾巴狼何虾下意识地一摸那曾经长鼻子的地方。叹了口气说:“唉――,前两天,在花虎庄砖窑遇到一个排的八路,我估摸着就是韩飞虎他们的人。他们人多,仗打得挺邪乎。两军相逢勇者胜。我领着弟兄们一阵风地冲进八路人群里,贴着身子死拼。趁我正和一个当官的厮杀时,一个大块头八路从侧面向我扑来,抡刀就砍。我一心难得两顾,躲闪稍慢了一点儿,哪刀贴着我前脸劈下,把鼻子丢掉了。”
“好险啊!”笑面虎白有财听何虾绘声绘色地讲述,吓得头皮发紧,浑身抖搂。哆哆嗦嗦地说:“鼻子丢就丢吧,没有丢了命就好。真是万幸,万幸。我的儿呀!真该给你记头功。”
“记个屁!”秃尾巴狼何虾气不打一处来,“记不记功不要紧,咱干的是这个。两军阵前,理应一马当先。千不该万不该,刁司令不该听信小人谗言。胡说我被八路俘虏,割掉鼻子放了回来。这不,把我这个小队长也给撸了。我说干爹,您干儿子冤枉啊!”说着,秃尾巴狼何虾的眼一挤鼓泪水就哗哗地流下来。
笑面虎白有财一点儿也不怀疑秃尾巴狼何虾的述说。他相信干儿子的才能,本来当一个小队长就够屈才的了。
笑面虎白有财用手敲击着桌子。皱着眉头说:“有这等事!?士贵啊,士贵,你咋能这么办事。真是的,没有一点儿头脑.。”笑面虎白有财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嘴里一个劲地,“嗯,嗯,嗯。―――”
门被推开,野菊花白凤飘然而至。一进屋就亮出一副娇滴滴的嗓门,带着暖心润肺的滑音:“爹,你咋啦?谁惹爹生气呐?”又看见往日的情人秃尾巴狼何虾也在,接着说:“这不是何虾兄弟吗,那阵风把你也吹来啦?哎哟!挂彩了,要紧吗?”
“没事,没事。姐,你也来啦。”秃尾巴狼何虾的眼睛很贪婪地在野菊花白凤的脸上扫来扫去不愿离开。嘴里说,“我没事,就是过来看看干爹。”
笑面虎白有财一肚子的不快,正没处发泄。见野菊花白凤来了,把秃尾巴狼何虾的遭遇给她一说,越说就越有气,“这个刁士贵,你不知道咱们的关系吗?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总的给我留点儿面子吧。再说,不能谁的话也听。在外头混事,免不了招惹住谁,到时候就有人背地里给你使绊子。当司令的,膛里要清楚。”
野菊花白凤听得出来,显然这是爹在抱怨阴山狈刁士贵办事浑浑呛呛分不出远近内外。便赶紧圆场。说:“行喽,行喽。我当谁惹爹生气呢,跟他呀,不值得。士贵办事有一忽没一忽的,您老甭在意。我回去跟他说说就行喽。”
野菊花白凤又安慰了一番何虾。末了,伸出纤手在何虾胳臂上轻轻一捏,只捏得秃尾巴狼何虾筋酥肉麻浑身燥热。颤着舌头说:“还是姐姐结记小弟。”
野菊花白凤走的时候,笑面虎白有财把秃尾巴狼何虾放在桌子上的两瓶山西汾酒递过去,让她带回去给士贵过过酒瘾。
阴山狈刁士贵酷爱喝酒,一闻到酒香,腿软得就挪不动地方。野菊花白凤就不愿让他喝,怕他喝多了瞎胡闹。
阴山狈刁士贵这个死鬼,本来就是北瓜蔓拧绳———没一点儿正劲。若再多喝了酒,常常把个野菊花白凤折腾得筋疲力尽如一滩烂泥。今个儿不同往日。她就盼着刁士贵喝,盼着他多喝。他喝多了,小弟何虾的事就好办了。
野菊花白凤扭着屁股一进屋,阴山狈刁士贵的眼睛还是看见了,野菊花白凤故意藏在身后的两瓶山西汾酒。“什么好酒?”阴山狈刁士贵一下子跳起来。
野菊花白凤躲闪着故意不让他看。却把酒瓶放在桌子上打开瓶子盖,让浓烈的酒香弥漫整个房间。
闻到酒香的阴山狈刁士贵,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欲望。鼻子一耸一耸地吸吮着被酒香浸透了的空气。伪军司令的臭架子早已荡然无存,低三下四地乞求野菊花白凤给酒喝。
只一杯酒下肚,阴山狈刁士贵就觉得浑身燥热,气血涌动。两杯酒喝过,就觉得浑身的血管鼓胀得难受,不放血,不发泄,说不定就会撑崩爆裂。等第三杯酒喝进去,阴山狈刁士贵的脸红得像刚从血盆子里钻出来,眼睛也直了,像两只手电筒的光,不动地方地照着野菊花白凤,只照得野菊花白凤都觉得有些难为情。
这个野菊花白凤别看年轻,在情场上可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她朝阴山狈刁士贵 嫣然一笑,妩媚百生。顺势在阴山狈刁士贵身上挠了一把。
此时此刻的阴山狈刁士贵被酒精烧得头昏脑涨,自己早已控制不了自己。借着三分酒劲七分野性,阴山狈刁士贵像一头挠槽的叫驴,又踢又咬,嗷嗷怪叫,野菊花白凤哪里还招架得住。
紧要关头,野菊花白凤脸蛋子一耷拉,一本正经地说:“你这个人,怎么也不看个眉眼高低。你是刘备招亲,人家可是刀子剜心呢!”
阴山狈刁士贵不禁一愣:“咋么啦,有啥事发愁遭难,像刀子剜心哪?”
“我有件事,你得给办。你不办,我心里比刀子剜还难受。”野菊花白凤瞅着即将乖乖投降的阴山狈刁士贵,故意卖关子。
“办,办。别说一件,就是十件百件,只要你说出来,我就办。”此时的阴山狈刁士贵连骨头都酥软了。只要野菊花白凤能提出来,什么条件都能答应,“就是你想吃活人脑子,我立马给你取来。”
“好。这可是你说的。”野菊花白凤的面色立刻由阴转晴眉开眼笑,给阴山狈刁士贵传送过去阵阵秋波。刻意撒着娇说:“我干弟弟何虾可是受人诬陷的。他的小队长职务,你不能撤。啊————!”
“你不早说,已经撤了。”阴山狈刁士贵无奈地说。
“那还不全凭你一句话。撤了,再官复原职嘛。”野菊花白凤一扭身子站起来,既撒娇又使犟地说,“你办不办?不办,我心里有气,憋闷得慌,不痛快!”
“办,办,办!”阴山狈刁士贵低三下四地对佯装生气的野菊花白凤说,“花虎庄炮楼的何虾立即官复原职。这还不行吗?我的姨太太。”
“这还差不多。”野菊花白凤如愿以偿,转眼之间犹如往身上注射了八支兴奋剂,高兴地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了。像是沙滩上晒太阳的一只河蚌。阴也行,晴也好;风也可,雨也罢,任由着你想咋着就咋着吧。
阴山狈刁士贵和野菊花白凤两个人,各自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各自做着各自的好梦。一场貌似身心愉悦实则内心空虚无聊的游戏玩过之后,两个人都觉得心满意足。那真是合作共赢,各自收获颇丰。
兴奋之余,两个人又卿卿我我于密室之中,犹如大奸臣秦桧夫妇密谋风波亭惨案一般,滋生出一条毒计来。给原本阴沉的花虎县上空又增添了一层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