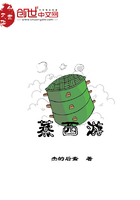房选之父房攸先,前朝进士出身,新朝建立之后以诏入官,靖宁初至从二品参知政事,丁母忧,方罢。后屡诏不起,至房选尚公主,封伯宁侯,加少师,复入朝。我登基之后,房攸先为光禄大夫、太师、英国公,作为满朝文臣武将中封爵最高的人之一。
但是,我却绝少见到这位国丈。在我的印象中,房攸先从未单独入宫觐见过。除却大朝、赐宴等正式场合,我并无见到他的机会。而房选之母赵氏,则更为神秘。她出身故宋皇族,是一位王的孙女。
因此,房攸先觐见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我于养心殿前殿正堂接见英国公房攸先。他由内臣引入,至御座下行礼如仪,礼毕赐座。他头戴加笼巾貂蝉梁冠,冠上八梁,是国公制式。身穿朝服的房攸先举止庄重雅正,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簪缨世家雅道相传的气质。
我对之微笑如仪,笑容浅浅,客气道:“国公入宫,可惜始政卧病,不能全礼。还望国公莫要怪罪。”
闻言,他略一欠身,道:“回万岁,臣不敢受殿下之礼久矣。况且臣年老,本不欲叨扰万岁夫妻,此番入宫实是世情所迫。”
“国公何以如此言?”我面容微讶。
“敢问万岁,臣前度几番上表乞骸骨,屡不得允,是万岁之意,还是殿下之意?”房攸先正色问我。
我的笑容使面部线条更趋于柔和,缓缓道:“国公的奏疏,朕并未让始政见到。朕也并非不允许国公致仕,只是罢官、削爵之类的事,朕是不允许的。”
“万岁因殿下之故,优待房氏甚厚。臣一家本受之有愧,况且今次金陵之祸,房家本来有过。臣请削爵、罢官,实是正当。只望万岁不要因臣家之故,迁怒于殿下。”
我微微舒了一口气,原来房攸先请罢官削爵,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儿子。于是我缓言对他道:“世家之于国家为肌理,如遇动荡大事,宜作壁上观。”
“不敢。”他起身欲拜,我急令左右相扶。
我继而道:“此语是实。不过史家正言不敢如此道罢了。国公与赵夫人为朕舅姑,然房氏却并非始政做主。朕不会怪罪。至于恩推房氏,是为始政立身,与房氏身为世家本无关。而房氏不插手金陵之乱,正是世家本分。朕不会因房氏之故迁怒国公、赵夫人与朕叔房迮一脉。更不会因此不信于天王,否则朕便不会令天王代驾江南。”
闻言,房攸先即一沉吟。方道:“如此,诸大臣不会因此谏言于万岁吗?”
我还保持着微微的笑容,“朕会一力承担。”
房攸先拱手作揖,道:“万岁如此宽待臣家,臣无以为报。而此前殿下久滞于金陵之事,臣有有言于万岁。”
我摆摆手,只道:“此中是非曲直,朕心如明镜。国公不必多言。始政去金陵,除却路途之外根本不能说是久滞,不过言官有意谏言,便顾不得这么多,朕心里却都是明白的。而赵夫人之病,朕亦甚为关心,前度已遣太医往金陵随侍照料,想赵夫人只略有些春秋,并不碍事的。”
言毕,我略一顿,复又道:“国公既已致仕,恐怕有南归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