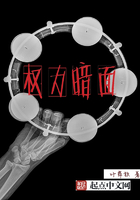方之衡封王那年,先帝对他十分厚爱,这才赐予他,方之衡素来也是珍爱此物,贴身把玩,甚少示人,以至于这一屋子的嫔妃皇子都未必有人识得此物。
可就是这么一个珍爱之物,方之衡却舍得送给三皇子。
皇上,是不是太宠这个孩子了?
一众皇子心中也是疑惑不已,虽然他们并不识得此物,但是却听到那是父皇之物,他们素日瞧见父皇莫不是战战兢兢的,连口大气儿都不敢喘,更别说是开口像父皇索要物件了,倒是这个病歪歪的老三在父皇面前也实在太得脸了,若他不是个三天两天卧病的德行,或许他才是这宫中第一劲敌呢。
不过是短短一顿,徐令月已然恢复一脸笑意,对方渐琛道:“虽是借花献佛哀家也开心,哀家的孙儿有孝心,哀家的儿子有舐犊之情,哀家自是喜不自禁。”
方渐琛退下,轮到四皇子始休上前,众人都颇为戏谑地瞧着始休手中提着个篮子,缓缓走上前来。
方渐琪不由得阴阴勾了勾唇角,冷哼出来,其实自打始休刚一进殿,所有人都或是惊诧或是讥诮又或是同情地不时看向他手中的篮子,除了一篮子紫色的桑叶并一些榆树叶子之外,再无别物。
也真是个可怜孩子。
不过这就是皇宫,出身、皇宠、心机、坚韧,这些子关键,从来就缺一不可,所以眼下他能拥有的,就只有这篮子桑葚罢了,至于日后还能拥有什么,没人知道,也似乎没有人稀罕知道。
他这位所谓帝后嫡出的四皇子,出现的如此突兀,或是又在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消失。
皇宫的战场中,从来不会允许有这样的竞争者出现。
不仅不够格,而且还差得相当远。
“孙儿给太后请安,孙儿常听母后说太后最喜欢桑葚的甘甜之味,故此备下这一篮子的桑葚供太后品尝,恭祝太后天增岁月人增寿。”始休恭恭敬敬跪地行礼,双手将一篮子桑葚高高举过头顶。
徐德仪心下一怔,她倒是真说过一嘴子太后喜食桑葚的话,不过当时是和春桃说的,且还是因从内务府挑了一批子绣了桑榆花样的缎子,她随口就吩咐让人送去给太后做了被面,不过就是么顺口一说,当时始休在殿里请安,不想他却也听到了,还给记住了。
徐德仪一边浅浅抿了口茶,一边则瞄了始休一眼。
这一次,她是有意不让春桃知会始休重阳之事,自然是有意想让始休在众人面前出一出丑的,但是却不想这小子倒还有这一后手,且这小子倒还般伶俐,非但没几句抱怨,反倒还顺嘴奉承了她。
也罢,都道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她心中纵使再不喜这冷宫孽障,此时也不会当着这许多人的面刻薄,徐德仪一边将茶杯放到小几上,一边伸手从始休的篮子捡了一颗桑葚,奉到太后面前,含笑道:“太后快尝尝这孩子的孝心吧,眼瞧着这桑葚就甘甜。”
“果然甘甜,”徐令月就着徐德仪的手吃了一颗桑葚,忙不得赞不绝口,一边又对始休道,“难得你这般有心,如今都重阳了竟还能寻得这一篮子的桑葚,想来也是花了一番力气的,快起来吧,你身子骨弱,仔细一会子膝盖跪疼了。”
“孙儿多谢太后,孙儿能为太后尽孝,已是天大的福气,并不觉得辛苦,”始休一边说着,一边又对徐德仪恭敬道,“还要多谢母后提点。”
徐德仪抿了口茶,稍稍点点头,意味深长道:“你有心才是最好。”
“皇后孝顺,皇后抚育的孩子自然也孝顺,”徐令月道,一边又对碧乔道,“扶四皇子起身。”
碧乔忙得过来扶了始休起身,始休躬身退到方渐琪身后,方渐琪白了他一眼,并不多言。
再后面就是六皇子方渐瑾了,方渐瑾今日所献是一尊糯底阳绿白玉金佛,乃是众皇子所献礼中最贵重的一件,贤妃乃是安氏一门嫡女,素来出手阔绰,也并不稀罕,且贤妃如今还在卧床静养,不便前来,自然给六皇子备下的礼更加贵重。
这尊金佛很得太后心思,方渐瑾也是个嘴巧惹人疼的,且又是宫中最小的皇子,太后更是欢喜,搂着小孙子在自己身边坐下,直到用膳的时候也是如此,其他嫔妃公主与皇子则各坐一侧。
膳后,徐令月分别赐六位皇子一只麒麟纹玉如意枕,甚是精巧稀罕,一众人又在慈宁宫陪着徐令月说了一会子话,因徐令月乏了,这才纷纷退下。
始休来的时候是坐轿,这时候却并不想早早回去,天还早呢,在三清殿待着,也不过是和崔嬷嬷大眼瞪小眼儿地干等着天黑罢了,索性随意走走。
打发了轿夫先行,始休慢条斯理地到处走着,九月的天,已经颇有些寒意了,加之外头又起风,难得这雕梁画栋也显出几分秋日萧瑟。
出了慈宁宫,始休沿着朱红的高墙朝后走,慈宁宫后面有个偏殿,里面住着慈宁宫里头有些身份的宫人,如张德海和碧乔等,宫中其他宫殿也是如此,如今太后开恩,轻许也住在里头,且还有个单独的院落。
前些时日,轻许还未醒来的时候,始休也是日日过来的,倒也是轻车熟路,只是今日,始休的步子难免有些沉重。
得知轻许醒来之后,始休便就暗中打算着日后不再去了的,至少这个时候他还去不得。
这个时候,他还不能给轻许一个交代。
从前在乾西宫的那些时日,多少个深夜,他不声不响趴在大槐树上,听着轻许在坟茔前哭泣,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轻许的眼泪,实际和他是有关系的,只听着她小猫一样的呜咽,便就觉得钻心的疼,他从前也是见多了冷宫里头疯女人的眼泪,所以他是极其厌恶女人啼哭的,但是他就是见不得阿许落泪。
只是如今想来,阿许的眼泪,竟然都与他有关,原来他自打出生,便就对阿许有愧的。
时至今日,轻许毁容断指,他更是罪孽深重,所以,他要如何面对这样的阿许?
他心知肚明,知道不该去见阿许,但是一双脚却似乎并不听话似的,等到脑袋清明的时候,他已经走进了轻许的小院,一抬头,始休的鼻子瞬时就酸涩了起来。
这简陋偏僻的小院,里头是有棵梨树,轻许昏睡的时候,那梨树还是一树浓绿硕果累累,这个时候再瞧见的时候,已然是一地落叶,除了枝头上稀稀疏疏挂着的几只斑黄的梨子,整棵树都是光秃秃的,而轻许就坐在那满地落叶中。
背对着他,低着头,身着一袭浅紫色的、宫人棉麻长袍,似是在修改衣服,只是看得出双手并不利索,尤其是那断指的右手使不上力气,只好改用左手来解上面的扣子,光是这样远远看着便就觉得费劲得很。
“南生,是你回来了?”似是听到了脚步声,轻许淡淡出口询问,“桑葚可交到他手里了么?他……他可派上用场了么?”
轻许的声音飘进始休耳中,那是久违的、熟悉的、日思夜想的,始休不语,也根本迈不了步,浑身上下似都在轻许的那一句淡淡询问中散了架,始休忙得伸手扶住了门框,眼泪一滴一滴打落在名贵的皇子朝服上。
“南生,你别生气,我一早就该猜到,他如今是皇后嫡子,如何还需要我再给他操心?那一篮子的桑葚既是失了用途,你便就都留着吧,权当是我给你赔罪了,”许久没有得到回应,轻许讥诮地勾了勾唇,自嘲道,“南生,你也别笑话我,我只是习惯了,就像你从前习惯了照顾你的娘亲一样,我是习惯了照顾他,关心他,习惯了时时事事为他打算,只是他又不是那个从前需要人照顾的撒娇小孩儿,我早就应当知道的,只是真的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