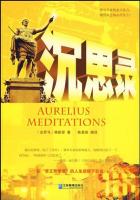这种见解,非常平易,却是宋以后无人敢道的议论。程颐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那种武断的论调,在这八百年中,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男女。
费氏把生命,妻子,产业等等,和义理看作同样重要的东西;教人要把这各种分子合起来看,不可单拿“义理”一种来评判人。这真是平允忠厚的态度。
他们又说:
尚论者,生不同时,事不共历,固宜考详始终,推量隐曲,安可悉铢两于圣贤而立论哉?古人有言,“难得而易失者,时也。”不特此也。
难一而易二者,心也。难合而易乖者,情也。难决而易动者,疑也。难无而易有者,争也。难平而易忿者,气也。难免而易来者,忌也。难伏而易起者,谤也。难完而易瑕者,名也。难久而易变者,事也。难善而易坏者,政也。难除而易生者,弊也。……难通而易执者,意见也。难悔而易遂者,过误也。难成而易欺者,勋业也。
世若此其纷纷难处;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议者在其后矣。有不自恐自惧,而深究责,大生愧悔,求以寡过,尚何敢任意苛搜,轻刺往哲哉?(上,十七~十八)
这一大段中,如“难一而易二者,心也;难平而易忿者,气也;难通而易执者,意见也”,皆是阅历有得的名言。宋以来的儒者往往意气用事,勇于责人,而不自觉其太过。
如朱熹之劾奏唐仲友,如元祐后人之诬蔑王安石,都是道学史上的绝大污点。费氏最恨那“斤斤焉同乎我者纳之,其未同乎我者遂摈而弃之”(上,四四)的不容忍的态度。费氏形容他们:
不危坐,不徐言,则曰非儒行也;著书不言理欲,则曰非儒学也。二三师儒各立一旨,自以为是;外此。非。绝天下之人,以为不闻道;自命曰真儒。其说始固蔽不通,学者不能尽可其说,辩论亦从此纷起矣。
……于是以儒之说为昧难测也,儒之意为执难平也,儒之事为烦难从也,儒之情为隔难合也,儒之气象为厉难近也。彼方夷然自远,此复绝之;不肯钳然以处人后,二者各欲为名高,交相恶矣。
……立于朝廷,两相危陷,……以忧社稷。下处草野,是非烦辨。损害学案,激使他趋。天下之人婚官丧祭,终身儒行之中,所尊反与儒异,所言反与儒敌,其何尤哉?(上,四四~四五)
宋以来的理学有几个大毛病:第一,不近人情;第二,与人生没大交涉;第三,气象严厉,意气凌人。费氏父子痛斥这种理学,说他“矜高自大,鄙下实事”。(上,四七)他们要提倡一种平易近人的“中,实”之道:
盖圣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为教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五)这真不愧为实用主义者的态度。
费氏父子皆有历史的嗜好,故他们对于古今学派的异同沿革,也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他们,他们提出一种“心理区别论”来解释历史上学派的异同。他们说:
天地囗缊,万物化醇。……人生其中,性安得皆同而不少异耶?男女媾精,自化而形,目于色,耳于声,鼻于臭,口于味,其官甚异;同出一身,不见其异,不闻其同也。学者论道,安得执其同,遂谓无异;执其异,遂谓无同耶?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圣人以狂狷兼三德也。《洪范》传曰:“又用三德:平康正直,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沉潜多者狷。高明多者狂。刚柔者,裁之也。……高明而教使柔,沉潜而教使刚,然后才因学以当于用。(上,四九)
中行,狂,狷,同传圣人之道;高明,沉潜,不可偏废。圣人谓颜氏之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子贡告诸往而知来:高明者欤?子羔执亲之丧,泣血三年未尝见齿;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沉潜者欤?子张之学多高明,门人所传近于狂;子夏之学多沉潜,门人所传近于狷。师也过,商也不及,圣人进退之;未尝谓二子遂以过不及终其身也。……高明而学焉,则以高明入于道;沉潜而学焉。则以沉潜入于道。道同而所入异,入异而道亦同(疑当作因)之不同。韩愈所谓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上,五○)
我们分中行,高明,沉潜三种性质,颇似近世詹姆士说的哲学家有“心硬”“心软”两大区别。
高明一派,费氏谓近于刚,其实乃是詹姆士所谓“心软”的一派。沉潜一派,费氏谓近于柔,其实乃是“心硬”的一派。
心软,故富于理想,而易为想像力所诱惑;自趋于高明,而易陷于空虚。心硬,故重视事实,重视效果;虽不废想像,而步步脚踏实地;然其魄力小者,易堕入拘迂,易陷于支离琐碎。费氏拿这个区别来说明学术思想史上的派别:
后世学者,性本沉潜,子夏氏之儒也;而说变焉。自以为尽于圣人之道;执其说[以]非天下之高明。学者之沉潜者皆从而和[之],谓其非合于圣人,不知其为沉潜之非高明也。
性本高明,子张氏之儒也;而说变焉,自以为尽子圣人之道;执其说[以]非天下之沉潜,学者之高明者皆从而和[之],谓其非合于圣人,不知其为高明之非沉潜也。
圣人之道于是乎异矣。群言肴乱,不得圣人折衷之,必折衷古经乃可定也。古经之旨皆教实以致用,无不同也;而其传亦皆学实以致用。即有异,无损于圣人之道,亦不害其为传也。(上,五一)
以上说的,皆为有人间“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言学异同之辨”而发的。小程子与朱熹属于沉潜一路,陆王属于高明一路。费氏此论最为平允,发前人所未发。
费氏父子的家学也属于沉潜一路,故费密虽受学于孙奇逢,为王学后人,而他攻击“良知”之说甚猛烈;他只取王守仁恢复古本《大学》一件事而已。费密作《孙徵君传》(《耆献类征》三百九十七,页三六~三七),只说:
其学以澄彻为宗,和易为用;是王守仁,亦不非朱熹。密曰:“先子有言,汉儒注疏邃奥,学者安可不造?”徵君则叹以为果然。
费密所取于孙奇逢,如是而已。费密又自说是子夏七十二传。是他也自居于沉潜一路。但他屡次自命为中行,自称为“中传”,自以为得古经之旨,故对于程朱陆王的玄学方面一律攻击。
然而他的推崇古注疏,他的崇尚事实,都只是他的沉潜的天性的表现。他所攻击的程朱,只是程朱受了高明的传染的方面,并不是他们的沉潜的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他“自以为尽于圣人之道,执其说以非天下之高明,……谓其非合于圣人,不知其为沉潜之非高明也。”
但费氏父子的沉潜,虽然是个人天性的表现,却也是“时代精神”的先驱。八百年前,程颐给他的哥哥程颢作《行状》,曾述程颢的话道:
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
这是二程当近世哲学开幕时期对于中国当日思想界下的诊断。他们深知当日最大的病根是那“高明”病,是那“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的玄学。
然而自他们以后,以至明末,五百年中,程朱之学盛行,结果还只是一种“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的玄学。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两宋时代高明之病太深,病根入骨,不易拔去。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这个鬼就是玄学鬼。二程不睬邵雍、周敦颐的玄学的宇宙论,却舍不得那主静主敬的玄学。朱熹提倡格物穷理,却又去把二程唾弃的先天太极之学重新掘出来,奉为玄学的奇宝。
陆王唾弃先天太极的玄学,却又添出了“良知”“心即理”的玄学。陆王末流的玄学狂热,更不消说了。高明的病菌弥漫在空气里,凡要呼吸的人,多少总得吸一点进去;沉潜的抵抗力强的人,也不能完全避免。
所以费密活在程颢之后五百年,他诊察五百年的思想界的毛病,仍不能不下“囊风橐雾,可有可无”的诊断。五百年的玄学病,到此已成“强弩之末”;李闯、张献忠继客氏、魏忠贤之后,屠杀了几百万生民,倾覆了明朝的天下,同时也冰冷了五百年的玄学热。
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面尊崇汉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朝二百余年“汉学”的风气:他们真不愧为时代精神的先驱者!
十三,九,十七,脱稿。
第四章 李塨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蠡县人。父明性,有学行,隐居不仕,是一个遗民,学者尊为孝悫先生。颜元为他作传。
1677年,十九岁,中秀才,学院为吴国对。
1679年,廿一岁,始见颜元,深以颜学为然,“遂却八比,专正学”。
1681年,廿二岁,作日谱。是年《年谱》云:“夜卧思天地间无处无鬼神,人无处可离敬。如此卧也,焉知无神视,无鬼凭?敬耶,神钦鬼敛;肆也,神惧鬼凌。敬肆,祸福之机也,奈之何不懍?”
二十四岁时,或问天有上帝乎?曰,“有。门有神,山有神,岂天而无主宰之神乎?《诗》曰,在帝左右。《书》曰,予畏上帝。非有而何?”,这些地方,可见其陋。他终身不脱宗教思想。晚年惟以“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律。岁后,“每曰存心使如帝天之临。”
岁时,“每日下书‘小心翼翼,惧以终始’以自勉。”颜李皆是《太上感应篇》一类的宗教家。(二十四岁,“自勘家人多病,皆由己懈惰,天降之灾。”)
1683年,父死。1686年,廿八岁,入京。在京时,与许三礼(酉三,河南安阳人。为当时的名御史)交。许三礼著有《圣学直指》诸书,恕谷引其言曰:
宋儒以理注天,且云心中自有天,似讳言苍苍者,则贯天人之学绝。又率不信鬼神。似以心外无鬼神者,则格幽明之学绝。
又记他的谈话曰:
道原于天,终于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功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归结也。天行健以生生也。君子自强不息以行仁也。今儒者遗置天地民物,但言明心见性,只为戴儒巾之禅和子而已。
恕谷似颇受他的影响,因为他们师弟本都是这一路的人。他有与许酉山书,首论尊德性,德即智仁勇,及《周礼》六德等;性即形色。
圣人践形即是践其肃义哲谋圣以全形色之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强不息。次论道问学。引《大戴记·保傅篇》说小学履小节,学小艺;大学履大节,学大艺,皆修己治人之事,不以读书著述为教。恕谷期望酉山“以忠信笃教为德,以诗书礼乐为学”。
1688年,三十岁,寄书与费密论学,有复书。是《年谱》云:“思仁道大,求之惟恕。……乃自号恕谷。”
1695年,卅七岁,他的学生郭子坚请他到桐乡。是为第一次南游。在扬州拜费密,见其弟子蔡瞻治岷。在杭州见王复礼草堂。王氏著有《三子定论》(朱、陆、王)。
恕谷记其言论,有“太极图本道家说,今本《大学》《孝经》系朱子改窜,晦圣经本旨,程、朱、陆、王皆染于禅”等语。秋间北回。
1696年,卅八岁,毛奇龄寄赠《驳太极图》《驳(河图)(洛书)》。
1697年,三十九岁,再到桐乡。在浙时有《上颜先生书》(二,三四),可见他已受南方学者的影响了。《书》云:
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汉唐儒者原任传经,其视圣道固散寄于天下也。朱儒于训诂之外加以体认性天,遂直居传道。于是变旧章有八:
(1)《太极图》。
(2)伪传《河图》、《洛书》。
(3)静坐。
(4)教人以性为先。
(5)朱子凭虚臆造:“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之说。遍考三代教法皆无之。
(6)致良知。
(7)立道学名,但取注经讲性天者为道学。
(8)立书院,专以读书为事。
是年毛奇龄在杭州,恕谷与王复礼往拜之。在毛氏席上见着姚际恒。恕谷从毛氏问乐。
他在南方三年,至1699(四十一岁)始北回。
一、学制
习斋立肥乡漳南书院规模云:
正厅三间曰习讲堂。
东第一斋“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西第一斋“武备”,课诸子兵法,攻守,营阵,陆守诸战法,并射御技击等科。
东第二斋,“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
西第二斋,“艺能”,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门内直东曰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直西曰帖括,课八比举业。
门外……东为更衣亭,西为步马射圃。……
(《年谱》下,三一)
恕谷学制,见《辨业》一。
二、理
王复礼曰,“颜先生言理气为一,理气亦似微分。”曰,五分也。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其流行,谓之道,以其有条理谓之理。非气外别有道理也。(《谱》二,三九)
钱丙不讲学问,不讲持行,专以明理为言。年来加以狂怪。
三、格物
恕谷自言丁丑(1697)重如浙,戊寅(1698)至杭州,旅次晨兴,忽解“物即大学中之物,格即可如程、朱训为至,即学也。格物致知为学文,诚意以至平天下为约礼。”(《辨业》序,一)
致,推致也。与《中庸》“致曲”之致同。格,《尔雅》曰至也。《虞书》“格于上下,是也。”……《周书·君奭篇》“格于皇天”,“天寿平格”。蔡注训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