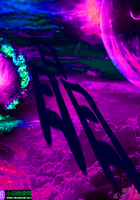比起那个叫万仞的地方,暹罗人或许对冀求是熟悉的。但这两个地域的割裂依然太漫长,尽管那些典籍里的描述详尽而透彻。但那毕竟只是个百年的缩影,也毕竟过去了一万年。
而在那样的年代里,冀求人的机械文明就已经震惊了暹罗。
这里能称之为战舰的产物,在人家那里只能算是大的舢板。就算用精金包裹,它们依然很脆弱。说白了,木船就是木船,在冀求真正的玄铁巨舰面前,它不过是一只渺小的螳螂。
一万年前如此,现在好像也没多大改观,这真的很让人唏嘘。
需求永远是前进的动力,而没有需求就意味着停滞不前。现在,东西两道天堑造就了太平,却也封锁了需求,让海航与海防也只能畸形下去。
而在冀求,在风暴海的北端,依然有辽阔而平静的海洋。对这个喜欢征服的国度来说,先进的机械文明也意味着压倒一切的力量。所以,他们一定在大展拳脚,一定在持续的向前。落寞拓也已经不敢想象,现在冀求人的文明会怎样了。
而在这里,那个永远不确定的期限,恰恰是束缚暹罗的羁绊。在辽阔的北部边疆,就算再多的边城耸立,一旦天堑变成沧海,战线的纵身将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敌人可以任意在任何地方登陆,而暹罗却永远无险可守。
这种战略的先天不足,是暹罗大陆永远的痛。它拥有天赐的坚固外壳,也意味着打开这把锁的钥匙也在上天的手里。没人知道何时,何地的门就会敞开,即使无数代有识之士,穷极一生的专研,这个时间和地点也无法确定。一旦大战开始,暹罗只能走在被动防御的老路上。
敌人明摆着从海上来,而暹罗只能在陆地上与之决战。好在暹罗还有独到的东西,那些让冀求无法理解的符文大阵,还有金丹大能的神奇修为。这些都曾经让冀求铩羽而归,或许,这也是一种平衡。但、落寞拓也并不这样认为。
只能希望初期的损失不具有毁灭性,只能寄希望诱敌深入,层层防御。在他的眼里,这就是单纯的磨消耗,这不符合一个年轻人的心。
对于那一战,曾经是他年少时的最爱,甚至还有点沉迷。直到如今,他始终认为暹罗的胜利是幸运的,他真的有很多的话想说。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北部边塞就崩溃了,全线的大溃退令整个暹罗蒙羞。而整个大陆中部,最终只能在青罡一线才组织决战,那足足向南推了一千八百里。而在西线,只能靠风之原的狂风拖慢人家的脚步,在鸭石山谷的地利之下,才苟延残喘。
甚至,翻遍古籍的每一处段落,他没看见任何一次值得庆祝的胜利,只有无休止的一退再退…
如果不是那个叫云梦的仙君惊天一击,最终斩首了敌方主帅,或许整个暹罗就不会那么幸运。如果不是万仞大军突破了北方的山口,或许,历史将沿着另外一条轨迹走下去吧。
在那些典籍里,详尽的记述了冀求战舰的很多细节。虽然他还没见过实物,但对这些东西的了解,绝不会比某位孟浪兄差。甚至,宗门顶尖的匠师们早给出了详尽的数据,那更加的直观和专业,而不仅仅只是印象。
在敌对的那片大陆,机关被称作机械,为此暹罗人还曾自诩为鼻祖。但除此之外,共通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在暹罗崇尚万法自然时,那里更习惯逆天而行。同为灵石的运用,在暹罗还在靠矿脉贫富来区分时,那里已经有了提纯与凝缩。这是非常巨大的成就,也是个巨大的威胁。
当我们还迷醉于灵兽驱驰的快意时,人家已经获取了强大无匹的动能。
在那次旷世之战以后,暹罗迎来了深刻的反思期,也对那场惨胜专研过很久。当然也曾试图取长补短,或者做些改进与融合。但这里的大能们发现,这并不只是难度的问题,而是对整个文明传承的颠覆。
因为,两地的区别实在太多,不止是流传功法的大相径庭,还在于对整个修者世界的理解。
暹罗太注重,或者只注重修为本身,而不是应用在整个修者社会。修为对应的是个人,或者最大限度到一个家族。而量产与普及高阶修士这样大规模的事情,在暹罗根本无法完成。
观念或许才是最难改变的东西,它被赋予极尽的崇高和伟大,但它并非真的无私。
于是,成就只存在于账本里,只彰显在招牌货的流水里。而秘方被锁紧箱底,或者深藏某个继承者的心里。而最高超的工序,往往只掌握在工坊的大匠人手里,而他们这辈子都不会跳槽,甚至传男不传女…
这些东西外流的几率微乎其微,只存在于某个宗门。它是一个家族存在的根,是这户人家的命,即使没有了传人,也要带进坟墓里……
这就是暹罗大陆宗门盛行的由来。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垄断,但同为垄断,这里却做得更彻底。除了血腥的抢夺和吞并,获得未知的功法与工艺,就别无它途。
但抢夺会流血,而且还包括抢夺者自己的血。当力量趋于平衡时,代价就越大,有时候甚至是得不偿失的地步。这也是暹罗社会的写照,它孕育了宗门这种怪物,就只能赋予大小宗门各自的权利。无奈的期待在未来,他们可以恪守自己的职责。
但期待这东西,又如何靠得住,那几乎等同于放任。
虽然在栾城那样的大工坊里,暹罗人研制出了另一类的东西,但那仍然只是机关学的延续,它是符阵流派的延伸。而符这种东西是玄学,更依赖顿悟这种玄妙的东西。它同样繁杂又过于神秘,普及这件事根本行不通。
于是,落寞拓也又想起了那个女子,如果抛却个人的情感,她才是新路的出口吧。
在他手中,此刻就握着一贴膏药,那是近些年他觉得最有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