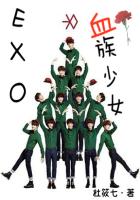在他身上最发达的乃是阳刚之气。论体力和满足,他可以跟松树和岩石称兄道弟。有一回,我问他溜溜干了一天活,到了夜里有时觉不觉得很累;他露出一本正经的神情,回答说:“天知道,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来就没觉得累过。”反正在他身上,智力亦即所谓的“灵性”还是在沉睡中,就像婴儿时一样。他接受过只是采用天真的、无效的方式下进行的教育,天主教神父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开导土著;而采用这种方式,小学生永远达不到有自我意识的境界,仅仅达到了信任和崇敬的程度,这个孩子并没有经过培养而长大成人,他依然还是个小伢儿罢了。大自然创造他时赋予他健壮的体魄,使他乐天知命,并在方方面面尊敬他,信任他,做他的后盾,这样他就可以像孩子一样,一直活到七十岁。他生性是如此率真,不谙世故,因此,就用不着正经八百地来介绍他,犹如你大可不必向邻居介绍土拨鼠一模一样。他得慢慢地认识自己,就像你得慢慢地认识自己一样。他可不会装腔作势。他干了活,人家给他钱,这就帮助他不愁温饱;但他从来不跟人们交换看法。他是那么单纯,而且天生卑微——如果说胸无大志的人可以叫作卑微的话——这种卑微在他身上既不是明显的品质,也不是他自个儿能意想得到的。聪明一点的人,在他心目中,几乎成了天上诸神。如果你告诉他,如此这般的一个大人物正要驾到,那么,他仿佛觉得如此至关紧要的事肯定跟他不搭界,用不着自己去瞎操心,还不如干脆把他忘掉就得了。他从来没有听到人家赞扬过他。他特别尊重作家和传教士。他们的言传身教,使他惊叹不已。我告诉他,我写过不少作品,他想了好半天,以为我是在说写字,因为他自个儿也能写一手好字。有时候,我看见他把老家教区的名字写在公路旁雪地上,字体挺漂亮,还标上正确的法语重音符号,由此我才知道他曾经打从这里走过。我问他是不是想过把自己心里的感想写下来。他说他倒是给不识字的人念过和写过一些来往信件,但从来没有试过写写自己的感想——不,他写不了,他可不知道开头应该先写点什么,真的要他的命,写的时候还得留意切莫把单词给拼错了!
我听说,一个知名的聪明人兼改革家问过他,他乐意不乐意这个世界发生变革;不料,他却惊讶得咯咯大笑,因为这个问题他过去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不,这个世界我可喜欢来着。”哪个哲学家跟他闲扯一下,准会受到许多启发。在陌生人看来,他仿佛对人情世态一窍不通;然而,有时候,我在他身上却看到了一个我前所未见的人,我真不知道,他是像莎士比亚那样聪明,还是像小伢儿一样单纯天真;我也不知道他是富有诗人的才气呢,还是愚笨透顶。一个镇上的乡友告诉我,说他看见他头戴一顶紧绷绷的小帽,笃悠悠地穿过了村子,还独自吹着口哨,让人不由得想起了活脱脱一个假扮的王子呢。
他只有一本历书和一本算术书,他特别擅长算术。前一本书在他看来乃是一部大百科全书,他认为那里头包含了人类知识的精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喜欢问问他对当前种种改革问题有何看法,对此他从来都能给出最简单、最实际的回答。反正这样的问题,他过去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没有工厂,他行不行?我问他。过去他一直穿的就是家庭手工织的佛蒙特灰布,他说,这不是挺好嘛。那么没有茶和咖啡,他行吗?除了水,这儿还供应什么饮料来着?他说,他常常把铁杉叶子泡在水里,他觉得热天喝上它,可比水还要好哩。我问他没有钱,行不行呢,他举例说明,钱给人带来的便利,他的表述富于哲学意味,竟然跟货币起源和“Pecunia”词源不谋而合。如果说他的家产是一头牛,现在他想到商店里去买些针线,可是每次买这么一点儿针线,都要拿牛的一部分去做抵押,他就觉得既不方便,又很难办到。他可以替许多制度做辩护,这可比哲学家还高明,因为他的说法都跟他本人直接有关,他指出了它们为何盛行的真正理由,他并没有胡思乱想出什么其他的理由。有一回,听了柏拉图关于人的定义——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还听说,有人拿来一只公鸡,把毛全给拔掉了,管它叫作“柏拉图的人”,他当即说明,公鸡的膝盖的弯曲方向不一样,这可是人与公鸡的一个重大区别。有时,他会大声嚷道:“我可多喜欢侃大山啊!天哪,我可以侃上溜溜儿一天呢!”有一回,我已有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问他对今年夏天有没有新的想法。“老天哪,”他说,“一个像我这样干活的人,要是他有过一些想法,而且又能念念不忘的话,那他就一定会干得不赖的。也许跟你一起锄地的人想要和你比试一下;天哪,那你就得一门心思扑在锄地上,心里想的只是杂草。”在这种场合,有时候他会抢先问我有没有什么改进来着。入冬后有一天,我问他是不是常常感到自我满足,希望在他的内心能有一种东西,来取代外部的牧师,达到更高的生活目的。“满足啦!”他说,“有人满足于这件事,有人满足于另一件事。有人已经要啥就有啥,也许会满足于背烤着火,肚子顶着餐桌,打坐一整天,我的天哪!”可是,哪怕我使尽花招,我怎么也没找到他看待事物时所持的教会观点;仿佛在他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就是简单方便,有如你指望野蛮人会觉察到的那样;这一点,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如果我建议他不妨改进一下生活方式,那他只是回答说,太晚了,来不及啦,毫无遗憾的表情。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彻底信奉忠诚,以及诸如此类的美德。
从他身上可以觉察到,有某种确实存在的独创性,不管它多么微乎其微,而且,我偶尔还发现过他的独自思考,表达自己的意见,真是难得见到,我可乐意在哪天跑上十英里路去观察这种现象,这无异于重温一下许多社会制度的起源。虽然他有时迟疑不决,也许还不能有棱有角地表达他自己,但是,他在话语之间常常隐含一种不俗的见解。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的思想非常原始,而又沉浸于他那粗犷不羁的生活之中,虽然要比仅仅有学问的人的思想更有出息,但还是没有成熟到值得报道的程度。他说过,在生活的底层,尽管他们出身低微,而又目不识丁,说不定也不乏天才人物,他们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装作自己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人们都说瓦尔登湖深不见底,他们就像瓦尔登湖一样,也许他们显得有些浑浊不清。
许多观光客偏离游览路线,特意过来看看我和我的室内摆设,而且还为登门造访找个借口,说是要讨一杯水喝。我告诉他们,我喝的是湖里的水,用手指着湖,还借一把舀水勺给他们。我虽然离群索居,但每年仍免不了有人来看我,我想,大抵是在每年4月1日,人人都想出门踏青吧;我好歹交了好运,尽管我的来客里头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来自济贫院或者别处的弱智族,也跑来看我;不过,我总是竭力使他们的全部智力都施展出来,向我说说心里话;在这种场合,智力往往成了我们谈话的主题;我也从中获益匪浅。说实话,我发现,他们里头有些人倒是怪聪明的,一点儿不比所谓教会执事济贫助理或者市镇管理委员会成员逊色;我觉得,现在该是他们相互易位的时候了。说到智力,我认为弱智与大智并没有多大区别。有一天,一个头脑简单但人很随和的贫民特地过来看看我,过去我倒是常常见到他和别的一拨人仿佛当作栅篱一样,要么站在地头上,要么坐在栲栳上,照看着牛和他自个儿不至于走失,这一回,他却表示自己要像我一样生活。他流露出非常单纯、真实,以及远远超出了,或者还不如说低于一般的所谓的“自卑”的神情,告诉我说他自己“缺乏才智”,“缺乏才智”就是他说的原话。上帝把他打造成了这副德行,可是他认为,上帝关心他,就像关心别人一模一样。“我一向就是如此,”他说,“打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脑瓜从小就不管用,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的脑子可不灵啦。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想。”而他就在我跟前,证实了他说的话没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玄乎的谜。我难得碰上一个这样大有希望的人——他说的话都是那么单纯、那么诚恳、那么真实。说真的,他显得越是谦卑,反而越是高贵。起初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聪明策略取得的结果。这么看来,在这个弱智贫民所建立的真实而又坦率的基础上,我们的交谈倒是可以达到了比跟智者交谈还要好的效果。
我还有一些来客,通常他们也算不上什么城市贫民,其实,他们应该都算是贫民,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理应称作世界贫民;这些来客吁求的不是你的殷勤好客,而是你的乐善好施;他们急巴巴地期盼着你的帮助,他们一开头就说明来意,他们已经发了狠,就是说,他们断断乎不帮助自己了。我要求来客可别饿着肚子来看我,虽然说不定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胃口,也不管他们又是如何得来的。慈善事业的对象,可不是来客。尽管我又开始张罗自己的事儿,回答他们的问话不免越发冷淡、越发怠慢,殊不知有些客人还是不明白他们的访问早已结束了。候鸟迁移的季节,来我这儿访问的,智力程度殊异的人几乎都有。有些人智力较高,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加以运用;一些逃亡的奴隶,一举手、一投足,活脱脱像仍在种植园里似的;他们有如寓言中的狐狸时时听到猎犬在追踪它们,苦苦哀求地直瞅着我,仿佛在说:
哦,基督徒,你会把我送回去吗?
这些人里头,有一个真正逃亡的奴隶,我帮着引导他朝北极星的方向逃去。有的人只有一个心眼儿,就像带着一只小鸡的母鸡,或者像带着一只鸭子的母鸭;有的人私心杂念特别多,脑子里乱糟糟,就像那些要照料上百只小鸡的老母鸡,个个都在追逐一只小虫子,每天在晨露中管保丢失一二十只——到头来都变得羽毛蓬乱,遍体疥癣;有的人光有想法而没有长腿,像一条智力不俗的蜈蚣,使你浑身起鸡皮疙瘩。有人建议不妨置备一本签名簿,供来访者留下自己的名字,就像怀特山那儿一样;可是,天哪!我的记性非常好,用不着那个玩意儿。
我不能不注意到我的来客的一些特点。少男少女和少妇通常好像挺喜欢到树林子里去。他们看湖水,看野花,消磨时光。一些商人,乃至于农场主,他们想到的只是孤独和生意经,认为我住得不是离那儿太远,就是离这儿太远,实在诸多不便;尽管他们说过,他们偶尔也喜欢到树林子里溜达溜达,其实,一望可知,他们并不喜欢。那些焦灼不安的人,他们的时间通通拿去谋生或者维持生活;那些上帝不离口的牧师,仿佛他们拿这个话题当成他们的专利品,因此对所有别的意见也就难以容忍了;医生、律师,以及那个不安分的女管家,在我外出时,她会窥探我的碗橱和床铺——要不然某某太太怎么会知道,我的床单就没有她家的床单干净呢?——还有那些年轻人,再也不算年轻了,他们却认为跟着各行各业的老路走,这才最保险,他们都说我当前的生活境况不会有多大好处。得了!问题正好就在这里。年弱多病的,以及胆子小的人,不管年龄、性别如何,想得最多的是疾病、意外和死亡;在他们看来,生活似乎充满了危险——其实,只要你不去想这想那,又哪来危险不危险呢?——他们认为,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应该精心选择最最安全的地区,因为在那里,有一位B大夫就可以随叫随到。在他们看来,“村子”按字面来讲,就是一个Com-munity,意为共同抵御的联盟,你不妨想一想,他们连去采摘乌饭树浆果时都要捎带着医药箱。这就是说,一个人活着,总会有死亡的危险;只是由于此人活着跟死去无甚差别,这种死亡的危险因而也就相对地减少了。一个人在家中闭门打坐,其实,跟外出跑步一样,都有危险。最后,还有一种人,他们自命为改革家,所有来客里头就数他们最最讨厌,他们还以为我是一直在歌唱——
这就是我亲手修造的屋子;
这就是住在我造的屋子里的人;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第三行诗是——
正是这些家伙烦死了
住在我造的屋子里的人。
我不怕捉小鸡的凶鹞,因为我没有饲养小鸡;但是我怕捉人的凶鹞。
撇开最后这种人,我还有一些更加令人愉快的来客。孩子们来这儿采摘浆果,铁路工人穿着干净的衬衫,星期天早上来遛弯儿,渔夫和猎户、诗人和哲学家,总而言之,一切老实巴交的朝圣者,为了自由的缘故,全都来到树林子里,他们真的把村子甩在了身后,我已准备好欢迎词:“欢迎,英国人!欢迎,英国人!”因为过去我跟这一个民族打过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