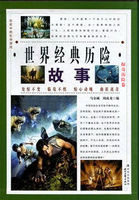她叫郎山妮,绰号“小狼”。
她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身着大红嫁衣时的情景。她亦不会想到,大喜那天通往新郎刘杰明家的路,会是一个充满了阴晦的巨大死亡陷阱。
那一天,没有离别时的眼泪,只有即做新妇的小小忐忑不安,她甚至原谅了没有前来接亲的新郎刘杰明。郎山妮纵身跃上本该属于新郎的坐骑——枣红马,她咧开嘴笑了,她家没有马,但是她从小就骑村里郎九爷家的马长大,一直把九爷家的马骑成老马,也把自己骑成了一个大姑娘。她回头看了倚在门边的老父亲郎孝坤一眼,郎孝坤有气无力的样子,很像一件晾在竹竿上的衣裳。他冲郎山妮笑了一下,眼泪却无声地流了下来。郎孝坤突然觉得女儿的出嫁,让他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不着边际。
迎亲的队伍一路吹吹打打,路过那个叫作“忘情川”的山谷,伴着唢呐阵阵的欢鸣,路边那些不知名的野花儿也随着微风摇来摆去,甜蜜的花香在空气中回荡。嫁衣下摆上,那匹仰天呼啸的小狼也和着唢呐声声长啸。那些奔流于血液里狼的特性,似乎也融进了郎山妮的骨髓里。
阳光纷纷扬扬从树丛间洒落,像从天空被人扔下的松针。那些草木在风中摇摆,植物和花草的气息让郎山妮打了一个细碎的喷嚏。她发现父亲郎孝坤的影像,在她面前慢慢地变得模糊起来,越来越远,她有些慌乱。当她从马背上坐起来的时候,一张小小的照片从内衣口袋里掉落在地。
照片里是一个有着白皙面孔的男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隐在他的嘴角。他的头发是柔软的,眉毛是淡淡的棕色,只有那双眼睛是明亮着的。照片里的男人即是郎山妮的夫婿刘杰明,他的面孔早已在她心里被温习了数次。她不知道刘杰明没来迎亲的原因,但她在心里一直把刘杰明当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俯下身子的时候,那张照片已经被她捏在手里。她看了一眼照片上的刘杰明说:“总有一天你得给我一个说法。”话毕,郎山妮仔细地把照片重新放回内衣口袋。
谁都不会想到本该乘轿的新娘,会骑在新郎迎亲的马上。新娘长相不俗、眉清目秀、明眸皓齿,特别是胸脯圆润胀鼓,恰似草滩上涨潮的春江水。与众不同的还有那双脚,也非乡下女人的三寸金莲,而是秀气的天足。一双绣花的布鞋蹬在马鞍子上,她将马匹缰绳牵在手里,威风里透着英气。
新娘身后,跟着一个梳着大辫子,头上插小花的丫头,虽不是丰乳肥臀,但看起来也颇为丰腴健美,大眼睛、长睫毛、薄薄的红唇,总是笑吟吟的,充满朝气。她叫春芽,是新娘郎山妮的丫鬟,边走边大声招呼随行的人,嗓音清脆,她的声音似乎不像说话,而像一串挂在山野女孩子脖子上的风铃,随着队伍上坡下坎,不停地发出悦耳的笑声。
而迎亲的花轿里,应是新娘端坐的地方却盛放了一杆被擦得光洁、锃亮的猎枪。这柄猎枪是郎山妮最心爱的宝贝,她像爱惜自己的头发一样爱惜着它。
出嫁前的晚上,郎山妮久久地坐在自家院子里的长凳上,一遍一遍地擦拭着这柄猎枪。她的手慢慢划过枪管,最后落在枪把上。那片深沉的土黄色和它散发的冰冷气息,让她极为着迷。更远的天际后面,太阳无限温柔地消退幕后,郎山妮映在地面的剪影和树影沉在一处,房里隐隐透出的光亮照在她脸颊侧面和棱角分明的唇边。
春芽噘着嘴巴端着一碗茶走过来,“小姐,你该睡觉去了。”
郎山妮笑了,说:“你自己为什么不睡?”郎山妮的目光转了过去,看到父亲郎孝坤住的那间屋子顶上,铺满了银白色软缎般的月色。
郎山妮没有看站在她身边的春芽,她的视线越过院子落在那片没有光线的门口,那是他父亲郎孝坤的居所。她霍地站起来,端起碗咕咚咕咚地把茶喝完,抹了抹嘴,小声问:“我爹他睡了没有?”
“老爷他应该是睡了。小姐你是不是明天要嫁人了,高兴得睡不着?”春芽脸上浮起不怀好意的笑,她晃荡着身子,在郎山妮面前绕了一个圈,得意地说:“我知道你睡不着,你总算嫁人了,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你抱着娃回娘家的时候。小姐,我替你高兴,比我自己嫁人还高兴呢。”
郎山妮将碗往长凳上一放,突然出手将春芽扛在了肩上,春芽在郎山妮的肩上哈哈大笑起来。
郎山妮不知道,郎孝坤正站在窗前,望着院子里咯咯笑成一团的郎山妮,用沉静的目光抚摸着前院的郎山妮,他的视线落在她乌亮的发间,略带淘气的脸颊和嘴角上面。二十多年与郎山妮相处的日子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窗外的月光倾泻进来,他扶住窗棱的手居然也慢慢地抖动起来,那小小的颤动连着他的右腿也动起来。他终于无力地伏在窗前,眼睛看向居室中最深处的某个角落说:“我的小狼长大了,我的小狼要飞了。”
阿财不时地回过头来,朝郎山妮看一眼,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郎山妮的夫婿刘杰明在新婚前逃走,代替刘杰明接亲的阿财,是刘家最贴心的仆人,此刻他就走在春芽的前面。
春芽瞄了一眼阿财的背影,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神色,她低声地重复着一句话:“就没见过哪家接亲新郎官不来的道理,这是什么规矩啊!”
“你说这些还有用吗?”
“小姐,他们刘家太欺负人了,就没见过这样的事儿。”春芽提高了嗓门,有些愤愤不平地替郎山妮委屈着。
“是你嫁人还是我嫁人?”
“小姐!嫁人就该受委屈?我就是替您委屈!”春芽的声音略微地高了起来。
“行了春芽,就算姓刘的在天边,我也会把他揪回来。”
“唉!”春芽长长地叹口气,不再说话。
欢快的唢呐声穿透了云层。八路军独立团严团长听到唢呐声的时候,急忙从怀里掏出那枚怀表。上面显示的时间是十二点四十五分,距离发起进攻的时间还有一刻钟。他再次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那队闯入山谷的队伍是一群快乐得忘乎所以的人,人群中最为艳丽的新娘脸颊若木棉般艳丽,他宛若看到新娘嘴角溢起的微笑。这群人不知道一场生死搏杀就要降临,严团长想,新娘嫁人选错了时辰。他急忙命令正准备拉响引爆地雷的顾小辉停止手中的动作。顾小辉皱着眉头,慢吞吞地站起来,隐在一棵大树的后面。
山谷里似乎安静了下来,唢呐手的调子戛然而止,一切物象都像着了魔般地陷入沉静,西面天空被氤氲笼罩在一片死寂中。
猎人的直觉让郎山妮以矫捷的身姿跃入花轿去抓猎枪,就在她滚出花轿还没来得及站稳的时候,伴随着一声枪响,她身边的轿夫就被西面射来的子弹在身上开了一个小洞,鲜血飞溅,染红了他的粗布衣裳。轿夫瞪着眼睛,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前胸。他踉跄了几步,四面的天空在他眼前旋转起来,尖锐刺耳的尖叫冲进他的耳朵,他看到不断有人慢慢先于他倒下,陪嫁丫鬟春芽惨白的脸成了他人生最后记忆的定格。
枪声间夹杂着人们的哭号冲进郎山妮的耳朵,也漫过严团长的耳朵。山谷西面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独立第五旅团的安西联队,中间是这些误入忘情谷的迎亲队伍。为不伤及老百姓,严团长无奈,只好提前行动,率领队伍抵抗日本人突如其来的攻击。
“保护群众!”顾小辉兄弟听到严团长这样命令。
安西联队联队长安西大佐举起望远镜,眼前的景象让他诧异。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不断地纵跃着,宛若林中矫捷的猎狼,在她纵跃之后,不断有身穿土黄色军衣的日本士兵跌倒在地。而更近的地方,一个狂奔的汉子抱着一个女子健步如飞,这身影清晰地出现在望远镜中,他一时没弄清楚对方的身份。
“那个女人有些手段啊!”安西问身边的神枪手上原枫,“这是一些什么地人?”
“不像土八路,倒像支那人的迎亲老百姓。”上原枫回答。
“有意思地!”安西大佐摇摇头,继续观看。
春芽被这场突来的“意外”着实吓着了。她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景,从前只是听老爷郎孝坤在心情极佳的时候,讲述过一些战斗的场面。她有些担忧小姐郎山妮的安危,可她没有在人群里找到郎山妮,她扑进阿财怀里,紧紧吊着他脖子,说了一句“小姐”,稍后又喘着粗气说:“好吓人啊!”
阿财也知道瞒下少爷离家出走的消息很不对,可他的使命由不得他说出实话,他只能暂代少爷把新娘接回刘家,所以也只能对春芽的自语询问假装没有听到。没有人知道那时候他的窘迫,他不敢抬头,不敢直视新娘和春芽的眼。
现在春芽的手实实地挂在他的脖子上,阿财再不多想,抱起春芽就向远处的林间跑去。那边长着许多茂盛的野草和一些杂七杂八的树丛,是躲避的极佳场所,阿财的速度越来越快。
是郎山妮最先发现阿财和春芽的,同时她还发现了那拿着手枪瞄准他们的阴险目光,那是侵略者即将猎杀前的逼视。春芽是从小陪在她身边的丫鬟,也是她最好的伙伴,她把春芽当作自己的姐妹,绝对不许春芽的生命受到半点威胁。
郎山妮就地向阿财奔跑的方向滚去,在安西部下的枪声响起之前,用尽力气推倒了春芽和阿财。在春芽眼前的尘土和烟雾中,猎枪也向着子弹来的方向挥去。子弹射穿了举枪射击者的身体,日军倒下,仍有速度的子弹头碰巧击中安西大佐的望远镜,哗啦一声,镜片粉碎,安西大佐吓得不轻。望远镜被这种跳弹击中的概率很小,即使久经沙场的安西也觉得幸运。
他望着肩膀上的那个小洞,皱了一下眉头,小洞里不断有红色的血向外流淌。安西大佐用手抹了一下伤口,右边几根手指上蘸了些鲜红的颜色,和国民党军队主力交战两年多,他都不曾在身体上留下伤口,如今却被一个不知身份的女人血染军衣,让他感到耻辱。
他记住了身着红衣的郎山妮,更记住了她衣服下摆上的那匹仰天长啸的小狼。那是一匹凶悍的狼,在他眼里,更是一匹桀骜不驯的母狼,虽然那只是刺绣的图腾。
安西将手指伸到嘴边,对身边炮兵中队的指挥官小野平静地说:“咸。”
炮兵中尉小野立刻抽出指挥刀,低着头:“消灭她?”
安西没回答,拿起小野的望远镜。五门迫击炮准备好,士兵们动也不动,只等长官下令。安西欣赏地看着那女人像流火一样左冲右突,他不担心女人逃跑,而是想尽可能多看一眼她衣服上绣着的小狼。
一分钟后,安西大佐那双冷酷的眼睛从前方收回,望着女人的背影,嘴角挂上了一丝阴鸷和怜惜的冷笑。
“对准女人开火。”
“是炮击吗?”
“对,我要她粉身碎骨。”安西再次命令,说得咬牙切齿,但这几句却是从喉咙口里呼出的。下令的那一刻,他的脑子里闪过日本老家的妻子,或许就是那点红色,让他受了刺激。残酷的战争只能激发出他更残酷的兽性,他不想再看到一个穿红的女人,就像联队编成离开妻子时,他撕碎了她的照片一样。
小野举起指挥刀代替命令。迫击炮弹压入,一门门小钢炮冒出蓝烟,锃锃作响的金属撞击声呼啸弹出,在郎山妮附近爆炸,掀起一阵黑色的呛人烟雾。郎山妮在一片片被掀起的黑色泥地中穿梭着。
她的宝贝猎枪不比三八大盖威力小,咔嚓咔嚓上着子弹。郎山妮动作稳健飞快,频频地挥动与击发。随着她手臂的起落,数名日本兵被子弹射中,他们的身形被子弹的贯穿力抛起后跌落,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上面广阔的天空。他们甚至没有看清郎山妮的性别就丢掉了性命。
春芽和阿财藏进树丛的时候,亲眼看见随着夜色逐渐降临,那些经由炮弹、子弹制造而成的烟尘吞噬了很多人的性命,也同样吞噬了很多美丽的花儿和青草的生命。春芽忧伤起来,所以她的脸上就一直挂着两条浅浅的泪痕。
阿财小心翼翼地看着山谷里的悲惨景象,对春芽说:“你瞧,天都黑了。没啥动静,鬼子八成撤退了。”
春芽说:“该结束了。你们家真浑蛋。”
“你才浑蛋。”
“要是小姐不见新郎就不嫁,就没这事了。”
“那你家小姐要是没生下来,更没这事了。”
狠狠一脚踢过去,春芽发了小姐才有的脾气。阿财说:“好吧,算你狠。”
八路军独立团与安西联队战斗到了傍晚时分,因双方彼此敌情不明,便都收缩兵力,短暂的交火宣告结束。因突然误入山谷的迎亲队伍,独立团原作战计划被打乱,只好与鬼子硬碰硬,所以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不小。
日军对遭遇战也估计不足,因而交火时安西联队长心里没底,担心被八路军主力包围,就主动退却。战火硝烟中,严团长和政委率部队追击一阵敌人,便转回打扫战场。望着牺牲战士的遗体,大家都肃立无言。
顾小辉是尖刀连的一员虎将,在严团长心中举足轻重。虽然他黝黑的脸蛋上还透露着一种不服输的孩子气,可又粗又黑的眉毛下闪动着的勇敢和顽强,已经透露了他的军龄。他在一名日本兵尸体旁边找到了哥哥顾小波,当时,哥哥就横躺在日本兵旁边,身上布满了搏斗后留下的创伤,可见双方战斗时何等惨烈。
顾小辉在为哥哥整理军服的时候,一直想哭。顾小波脸上都是血,左侧眼角的疤痕是他和弟弟小时候爬树时留下的印记,如今也被鬼子用牙齿咬开。在他右胳膊上还有枚桑叶形的红色胎记,此刻凝结着鬼子的脑浆。顾小辉动作很慢,他努力用一块还算干净的湿布,把好哥哥的脸擦干净。
他总是想起与哥哥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事。他们一起参加八路军,一起并肩打鬼子。当兵时顾小波已经很高了,而小辉的个头还像个娃娃,两兄弟在战火中成长,都成了部队骨干。如今,哥哥走了,顾小辉眼里的泪终于止不住,一滴滴洒到哥哥脸上,发出揪心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