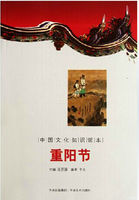昆仑山相距太阳太远太远,它们之间的空间距离简直无法计算。它们是一对情人,但只能在白天相会。
昆仑山相距太阳太近太近,太阳的光芒直射昆仑,承受了阳光抚摸的坚硬冰雪,也会变得温柔湿润起来。
在热烈而眩目的阳光照射下,巨大冰川的舌尖上便有一滴一滴的水珠掉下来;雄伟的雪山也软绵绵地流泄出一股一股的涓涓溪水。慢慢地,这一滴滴水珠、一股股溪流交合汇聚,积满山壑谷湾,就会冲溢出来,从高达数千米的山崖上奔涌而下,从沟谷斜坡上呼啸而过,撼天动地,势如利刃,在峡谷沟壑中割蚀深切,形成河流。当到达平原、沙漠,急流便缓慢散乱起来,逐渐变得平静温和。
昆仑山的冰川雪峰受孕于太阳的光芒,首先产生了一条现名为玉龙喀什的河流,接着又产生出一条更大的现名为喀拉喀什的河流,两河合流,便形成了现在的和田河。两河的名字,都由昆仑山产玉而来。昆仑山的大小玉石,就是随着河道而滚落人间的。流下白色玉石的河叫玉龙喀什河(白玉河),流下深色玉石的叫喀拉喀什河(墨玉河),还有一条小小的分支,流下的玉石颜色与前者不同,是绿色,因而也就有了一条与墨玉河汇流的绿玉河(布朗其河)。
唐代文献对上述三条河流有明确的记载:“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日白玉河,西日绿玉河,又西日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各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
三河汇流形成的“和田河”是今称,汉称“于阗河”,唐称“玉河”,明清称“和阗河”。
这是一条吉祥的美玉之河。而其源头昆仑山,则是一座云诡波谲、玄机四伏的神话之山、众神之山。
古老的神话被文献记载下来,文献记载的神话说昆仑山是“百神之所在”,是“天帝之居”、“帝之下都”,“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还说昆仑山是大地之首,“有增城九重”,有五城十二楼,有九井,九门,瑶池,帝宫,不死树。琼阁林立,坛圃处处,玉英缤纷,翠竹葱茏。护卫这些处所的,是一色白玉雕花的栏杆。
传说皇帝曾命伶伦制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至昆山之阴,取翠竹为笛而奏乐音。
《穆天子传》说,周穆王驾八骏之乘,漫游西域,在昆仑山会见西王母,他一方面与西王母对歌作舞,情意缠绵;一方面还“命其随从攻玉,戴玉万只而归”。那时已知昆仑山是“西域良山,玉山所在”。据说西王母为周穆王设宴欢娱的地方,正是在昆仑山上的瑶池之畔。
古代昆仑山神话中,出现过两个西王母。
《山海经》说,“玉山,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历及五残。”这里的西王母半人半兽,人面虎身豹尾,显然是一个神的形象。
《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则是能赋诗交欢、载歌载舞的人中之王。
周穆王设宴款待西王母时,她“乘翠凤之辇而来……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共玉帐高会。荐清澄琬琰之膏以酒,又进……
昆渝素莲,万岁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桔。素莲青,一房百子,凌冬而茂。”这就说明,西王母已是高居宫阁、享受文明生活的女王。
上述文献记载的西王母不是一回事,人面虎身豹尾的西王母可能是野蛮时代某个氏族或部落的尊神;善于诗歌、端庄大方的西王母,则应是西域昆仑山一带游牧部落的一位女酋长。在母系社会,部落首领为女性是很自然的。
史料记载尧、舜、禹、周穆王都曾见过西王母,他们所见西王母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代西域游牧部落的女酋长。
流传在西域塔里木河流域的一则神话说:在远古之时,昆仑山下是一个大湖,周围都是陆地。当时人们为了征战,砍伐昆仑山的竹子作箭互相残杀。翠竹砍伐殆尽,惹怒了天帝,天帝用倾盆大雨惩罚人类,湖水猛涨,大地变成一片汪洋。人类无处可去,就纷纷逃到昆仑山上楱身。后来洪水退了,原来人们居住的地方变成了沙漠,原来大湖所在的地方却成了肥沃的田野,人们便都下了山,聚集在大湖一带,开始了繁衍生息的新生活。
事实上,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在古生代是一片浩淼的海域,古生代末期发生强烈的造山运动,海底陆台上升,构成昆仑山主轴和中脊的框架。中生代山体边缘继续上升,到第三纪上升至5000米以上,大致形成昆仑山的基本形态。至今上升为7000米以上的几座高峰,茫茫昆仑更加使人们感到高深莫测。变幻缥缈于山峰之间的云雾,给人们留下了未知神秘世界的更多悬念。
昆仑山形成的过程是真实的历史。
昆仑山怪异的神话传说是虚构的艺术。
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艺术,铸成了人类文明的整体。
塔里木河流域还有这么一则民间传说:太阳和月亮不愿见面,就各自躲在昆仑山的两边,白天日出,晚上月升,从来不同时出现于天空。这样往复久远,宇宙就出现了白天和夜晚,光明和黑暗。
塔里木河各源流的流量大小,也听任日出日落的摆布。白天阳光灿烂,昆仑山冰雪消融,河流水势旺盛;夜晚昆仑山万籁俱静,冰川雪峰安然入睡,月光下的溪流也会水凝气禁,变得悄无声息。
昆仑山是河流的真正主宰。夏天气温增高,冰雪大量融化,洪流激荡,排山倒海,和田河有充沛的水量流入塔里木河,洪水还常常泛滥成灾。除夏季以外的九个月时间,严峻的冰山坚守贞操,寒冷的雪峰惜身如玉,即使艳阳高照,也很难使它们消化成水。和田河每到秋、冬、春三季就没水了,处于长时间的枯水于涸阶段。
尽管如此,夏季洪水的漫溢,还是在和田河流经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上,造成了一条抹不掉的绿色走廊。
这条绿色走廊古代就已形成,是沟通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北交通的一条捷径。也是于阗文化、龟兹文化、楼兰文化乃至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一条运输线。
这是一条不规则的运输线。夏日洪水汹涌而至时,夹带大量泥沙,河道淤高,河水漫滩;有时河边积沙被洪流冲刷,整体席卷而去,就形成一段直上直下的陡峭河岸。胡杨、红柳、沙枣、芦苇和沙棘等乔灌木的种子、幼苗,就随着洪水一路飘荡、四处安家。久而久之,和田河两岸的绿色植被生机勃勃、郁郁葱葱,抵御着沙漠的侵袭,成为贯穿南北的生命通道和文明运输线的绿色屏障。
河岸两旁,除了以胡杨为主体的森林带、以乔灌木为基调的草甸带和固定沙丘植被群落之外,就是塔克拉玛干那峰连波涌、沙浪滚滚的流动沙漠。河岸漫滩上的新月型沙丘,河岸高地上的山脊沙丘链,沙漠深处的鱼鳞状沙丘以及沙漠腹地山麓的格状沙丘和复合型金字塔沙堆,形成了举世无双的沙漠景观。
最神奇的沙漠景观是兀立于沙漠腹地的玛札塔格山。此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仅有的山脊,由第四纪沉积红砂岩和白云岩组成红、白二山。它位于和田河中游绿色走廊的西岸,它令每天早晨醒来的和田河感到惊愕和欣喜。这巨大的山体出现在沙漠深处,确实显得奇绝而富于神话色彩。
在落日的余辉中,玛札塔格红白两座山峰如同两位披挂盔甲、长须飞翘的武士,头对着头,静静地仰卧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庄重安祥。
当旭日升起,映人人们眼帘的玛札塔格山又是别样一番风景,红山、白山像一条双头巨龙,横卧于和田河畔,头临河床如二龙戏水,尾部向西延伸长约loo公里,翘起的尾巴就成了一座1000多米的高峰。
登上玛札塔格山头,可以鸟瞰和田河,瞭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山体本身奇形怪状,蔚为壮观。红山头上还坐落着著名的汉代城堡、烽燧,唐代寺院佛塔,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圣墓”,这些遗存又给绮丽的自然景观抹上了不同时期厚重的文化色彩。
玛札塔格山谷的风蚀地貌,尤其神秘怪异,令人触目惊心。
那巨大而逼真的风蚀佛塔群无尽地林立于峡谷之中,如排山倒海的波尖浪峰,气势雄伟。风蚀壁龛、风蚀塔柱、风蚀屋檐、风蚀佛寺、风蚀巨型蘑菇、风蚀琼楼高阁……鳞次栉比,如梦如幻,是海市蜃楼,是佛界仙境,还是月球景观移位于人间?
就在和田河绿色走廊的密林草丛中,就在玛札塔格的深山峡谷中,就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瀚海中,活跃着数以千种计的飞禽走兽、自由生灵。兽中之王老虎像哲人似地,蹲在山岩上望着和田河沉思;野骆驼行走时的威武雄壮、马鹿穿山越林的灵巧身姿,都映照在和田河的水波中;成群结队的野驴、羚羊、黄羊从沙丘上一拥而下,扑进和田河浅滩戏水畅饮;野猪、沙狐、跳鼠,怪模怪样地四处张望,又一溜烟地逃得无影无踪;而那勤奋的云雀、百灵、水鸟和猎隼,忽而掠过河面撩起点点水花,忽而又飞腾四散,有的还站在树梢上扯开嗓子唱个不停。
还有水坑里跳跃的鱼,天空中盘旋的鹰,沙洞中出出进进的兔以及古木参天的胡杨林问奔跑的鹅喉羚……在和田河的绿色走廊中,胡杨林虽然被砍伐大半,但中幼树却悄然而起,还有一些生长在有水份的沙洲、洼地的红柳、芦苇、灌木丛,仍然郁郁葱葱,是动物王国最后的家园。这些随水草而居的生灵们,不顾生存环境的恶化,依然故我,把沉寂荒凉的沙漠喧闹得一片欢腾,给悠悠流淌的古老和田河带来无限生机。
自古以来,和田河与塔里木河一样也是一条无定河,具有游荡性、间歇性和忽凉忽热的性格。洪水期河水漫滩,一片汪洋;枯水期则滴水全无,河床干}固。这里的动物和植物,也似乎成了游动的部族,随着水的盈亏走向而不断迁移。
据古代文献记载,那时的和田河一度是东北流向,洪水期狂奔乱淌的河水或汇水塔里木河,或与东邻的克里雅河汇合,浩浩荡荡地进入罗布泊,东流的一支就是古代塔里木盆地著名的“南河”。常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田河继续西移,到了清代和田河又折而向东,与塔里木河水系汇流,基本形成和田河与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在肖夹克汇流成塔里木河的水系形势。
河道发生变迁,是受河道强烈的沉积作用影响的结果。古代老和田河改道西移形成新和田河,则是因为老和田河左岸被洪水冲开一个大口子所致。
和田河的河道无论怎样变迁,一条延续人类生命、沟通人类文明的绿色长廊一直没有消失。只是植被的分布重点、动物王国的活动中心,随着河流的变迁进行一些局部的移动而已。
昆仑之水孕育了和田河,和田河汇入塔里木河孕育了绿色生命,孕育了人类文明。
登昆仑兮食玉英
屈原在他著名的诗篇《九章·涉江》中,高吟狂歌:“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
长江之滨的楚国大夫屈原虽然没有到过西域,却发出“登昆仑兮食玉英”这大气磅礴的豪放畅想。这足以证实,昆仑山玉石之重名,早已享誉天下。
汉景帝之子、被封为中山靖王的刘胜,死后葬于河北保定附近陵山的峻岭之中。当考古工作者怀着探奇揭秘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打开这座两千年前的古墓时,被眼前出现的景象惊呆了:在工作灯的照射下,这位中山靖王全身上下银光闪闪、浑然一色,那穿在刘胜身上的铠甲,原来是一件金缕玉衣,上面用金线缀着2498块玉片。在另一座墓中,他的妻子窦绾也是一身金缕玉衣。玉是避邪驱祸的吉祥物,但当地并不产玉,这玉衣所用大宗玉料来自何处?经过化学分析和科学鉴定,才确定这是来自昆仑山下古国于阗的软玉。
昆仑山距此六千公里。
如果以古代沙漠阻隔、山回路转、畏途遍布的交通情况来看,路程比现在的公里计数还要远得多。没有丝绸之路,一切都不可能。
距今3800年前,罗布泊一带的居民就用玉石作装饰物。在孔雀河北岸的古墓中就出土了于阗软玉质的玉珠,两汉时期的精绝、楼兰两地遗址中也都采集到于阗软玉质的玉珠等装饰品。
罗布泊地区邻近古代于阗,是塔里木河的下游,上溯和田河可达昆仑山。这里出现于阗玉不难理解。令人惊奇的是,大量于阗玉何以出现于远在中原的汉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
不仅如此,于阗美玉输送内地的时间和地区,远比汉代中山国的时代更早、地域范围更广。这是塔里木河的光荣。
早在殷商时代,商王武丁之妻妇好,饮茶的青玉碗、用膳的白玉盆以及玉质装饰品,都是用来自于阗的玉石加工的。她死后,还把生前用过的七百多件玉器带进墓葬中。至今,这些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玉器,就成为于阗玉盛行商朝王室的实证。
战国初期,楚地使用玉器已很普遍,不仅用于装饰和生活器皿,而且还用于古乐演奏。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就有用于阗玉石制作的。古代湖北一带的王公贵族对玉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难怪楚国三闾大夫、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要“登昆仑兮食玉英”
了。
从战国到两汉,于阗玉在中原的使用达到一个高潮期。于阗玉以其优异的质量被人们视为玉之上品,儒学家甚至把玉石润泽而又坚锐的物理属性比拟成仁义智勇的君子之德。帝王将相以拥有于阗玉器作为权力的象征,还把玉置于贵族礼仪文化和丧葬文化之中,给玉赋于无限美好的含义,办一件好事,也被说成是“玉成其事”。每一件于阗玉,都闪烁着塔里木河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