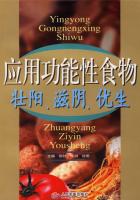电话另一端的说话人没有报出名字,布罗德卡立马意识到是提图斯。“三小时后,十点整,斯特凡大教堂,最后一排长椅。”
还没等布罗德卡说上什么,电话就断了。
即便凯尔特纳大街和斯特凡广场上微风拂煦,但大教堂里面仍旧寒气逼人,呼出的呵气凝结成白团团的水雾。朱丽埃特紧紧裹住大衣领子。
还没有像中午时分那样人满为患,到时候会有无数的旅游团和求知的人们排着队穿梭在大教堂里。此时只有一名导游以维也纳口音的英语向一队日本老人旅游团解说这座十五世纪的宏伟建筑物的艺术魅力。
提图斯已经等候在最后一排的长椅上,他仰头望着拱顶,好像陷入沉思。布罗德卡从他身边过时,差点没认出他来,提图斯的头上套了顶褐色长假发。
布罗德卡和朱丽埃特一右一左分别坐在提图斯旁边,他身上窜着股酒味。
先需要提图斯的帮助。
“明天早上我在饭店等提图斯的电话,”他说,“然后这几天我们再找个机会见面,时间和地点由他定。”
史雷格尔米勒希点点头,“好,尽我所能吧。”
回酒店的路上朱丽埃特出奇的沉默。她在心里对布罗德卡刚才的表现赞叹不已,尤其他竞有心在律师那里留有他的一封密信。后来布罗德卡才对她坦白,这件事是他临时编出来的,以防史雷格尔米勒希狗急跳墙起歹念。
第二天一大早——布罗德卡和朱丽埃特还在睡梦中,也就是七点刚过的样子,电话铃声大作,睡眼惺忪的布罗德卡拿起听筒含糊地说了声“喂?”
电话另一端的说话人没有报出名字,布罗德卡立马意识到是提图斯。“三小时后,十点整,斯特凡大教堂,最后一排长椅。”
还没等布罗德卡说上什么,电话就断了。
即便凯尔特纳大街和斯特凡广场上微风拂煦,但大教堂里面仍旧寒气逼人,呼出的呵气凝结成白团团的水雾。朱丽埃特紧紧裹住大衣领子。
还没有像中午时分那样人满为患,到时候会有无数的旅游团和求知的人们排着队穿梭在大教堂里。此时只有一名导游以维也纳口音的英语向一队日本老人旅游团解说这座十五世纪的宏伟建筑物的艺术魅力。
提图斯已经等候在最后一排的长椅上,他仰头望着拱顶,好像陷入沉思。布罗德卡从他身边过时,差点没认出他来,提图斯的头上套了顶褐色长假发。
布罗德卡和朱丽埃特一右一左分别坐在提图斯旁边,他身上窜着股酒味。
提图斯微微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他转向布罗德卡说:“请不要在意我的装扮,要是没有这假发的话我都不敢出房间,这样至少没人认出我来。”然后他直接问道:“你想怎么样?”
布罗德卡清清嗓子,他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他小心谨慎地瞧了瞧四周围,确认没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才把声音放得很低地说:“提图斯,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而且你根本不必担心我会把你泄露出去。”
“那史雷格尔米勒希是怎么回事,他说你讹诈他。”
“那是唯一能把你引出来的办法,我绝不会出卖史雷格尔米勒希,我保证。”
“她是谁?”提图斯用脑袋示意朱丽埃特。
“她是我的爱人。我答应你的事,对她一样有效。”
朱丽埃特向提图斯伸出手,说:“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他打看她好一会儿,就像她是一个被人拒绝接收的邮包似的,“我不这样认为。”他并没有也把手伸出来——像提图斯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举止也算不上不礼貌——他扭过身子面向布罗德卡问:“还是那个老故事?”
“如果你喜欢这样形容,”布罗德卡点点头,“这期间我发现了新的线索,它们都指向同一个……”
“我能想象得到,”提图斯嘟囔着,“所有的线索都终止在梵蒂冈的高墙前。”
“正是如此,可实在不合情理,我和我母亲都和教堂毫无瓜葛,到底怎么回事,提图斯?如果我上次没听错的话,你曾在梵蒂冈任过教职,你一定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事。你亲身经历过,是不是?”
“嗯,不错,是这样,那远不是令人欣喜的事情,光把那些记忆说出来就让我嘴里有种恶心的味道。”提图斯从他的外套兜掏出一瓶酒,往嘴里倒进一口。
“你在暗示,那些圣贤并非因敬仰上帝从而聚集在神于人世间的代言人——耶稣的周围?”
提图斯苦笑地说:“敬仰上帝?梵蒂冈里的人什么都谈,只是不淡上帝。相信我吧,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听到此话,朱丽埃特瞠目结舌地看着提图斯。如果有人说出这种言词,而且他又是个前神职人员,那么他的内心是何等的愤懑。
提图斯手上转动着锡纸包装的小酒瓶。他神色紧张地凑近布罗德卡,同时怯生生地朝四周瞧了瞧,说道:“几乎没人知道,梵蒂冈里面真正发生了哪些事情。那时候,波兰教皇去世之后,枢机主教们被召聚在一起举行秘密会议,从他们当中选出新一任教皇。
可是他们没能达成一致,在紧锁的大门背后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哪一位枢机主教能获得大多数选票。形势严峻,票选出一位新教皇的前景似乎非常渺茫,于是那些老人们决定抓阄。大家商定,靠抓阉产生的新教皇不能独自下达任何指令,梵蒂冈所有的决策应由枢机主教们共同讨论之后再执行。最后,这个阄落到了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幸运儿头上。”
“历史上既有强势的教皇,也有软弱的教皇。”布罗德卡说。
“话是没错,”提图斯点点头,接着说,“但是这种状况就是另外一码事。在新教皇还没有选出来之前,教廷中一小撮位高权重的枢机主教已经将大权揽在手上。此后,他们把教皇或多或少地软禁在梵蒂冈的高墙之内,他不得擅自离开梵蒂冈城,必须在所有呈于他眼前的文件上签字。”
“人们不是常常从报纸上看到吗,这位教皇一向深居简出。”布罗德卡说。
“正是,”提图斯轻声笑起来,“倒是可以这样说。”
布罗德卡皱起眉头,“那么在这当中,那个史莫雷斯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问,“难道他是……头?”
“他是其中的一个头,这个组织像是一只无比硕大的章鱼,根本就瞧不出头在哪里,它的触角可以伸至最最细小的角落。”
“难道就没有人起来反对他们吗?”
“谁要是敢于公开与这些圣徒黑帮为敌的话,谁就死定了。你还记得两年前辞世的那个枢机主教吗?那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接连有六位来自南美和东亚的枢机主教去世。报上说是因为他们太老了,是寿终正寝。其实他们之中年纪最轻的是五十六岁,最大的六十六岁,皆算不上高龄。而且无一例外都没有被送交尸检。众口一词,枢机主教们绝非意外死亡,他们是被召到天上去的。问题是,是被谁召上去的。”
提图斯的嘴此时如开闸的水,滔滔不绝。“罗马教廷有一大批帮凶。对于教廷来说所有的神职人员不过是手中的棋子,他们遍布全世界,不论何等职位。这一百二十位枢机主教、四千位主教以及超过四十万个教士被那一小撮人牢牢控制,他们掌握着实权。”
“你认识这些人吗?”布罗德卡小心翼翼地问。
“我认识他们中的几个,”提图斯傲慢地回答,“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和哪些人见过面。我对他们在瑞士和巴拿马的银行帐户及其密码再清楚不过……一句话,我对他们的底细实在太了解。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为什么要东躲西藏地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