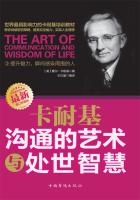野茨一摆手把棒子停了,走上来告诉他,这是各种刑罚里头最轻的,顺手把靠墙的东西指了指,意思是说:“你吃得住吗?”周铁汉从地上站起来,点点头,好像说:“我知道这是最轻的,我已经准备都尝一尝了!”再问,仍然是几个“不知道”。随着野茨的手一挥,军警们又涌上来四五个,扒住肩头只一磕,周铁汉跪在地下了,一根杠子压在两腿弯上,每头踏上去一个人。周铁汉的汗泼水一样淋下来。野茨喝道:“说不说?”周铁汉说:“不能说!”一头又上去一个人。周铁汉觉得腿就要折了,疼痛从腿上传到肚子里,传到心口,传到头顶上,他觉得额角上的筋咚咚地跳着,就要把肉皮崩开了。这时,周铁汉忽然看见瘫在地上的两个老乡,就像拉进屠场的羊一样,浑身哆嗦成一团,他们的眼鬼火儿似的望着他,好像在说:“你扛得住吗?”周铁汉一转眼躲开了他俩,突然把目光落在野茨身上,野茨劈开腿站在他的面前,脸上乐悠悠地眯着眼儿看着自己,那眼色,那神气,是周铁汉不知从哪里看见过的,是自己的父亲对长工们吗?还是什么大商店的老板对贫穷的顾客?还是煤矿的工头对工人呢?他想着,肚子里就装满了气,心里说:“怎么能在这种人眼皮下低声下气?怎么能向这种人哀叫求饶?那真是太下贱,太无心肝了!”他坚决地闭紧嘴摇了摇头。在杠子上增加到六个人的时候,一阵昏迷,就死过去了。
就这样,周铁汉又被过了三堂,也就又死过去三次。有一次,他的两个大拇指被细麻绳拴紧,把整个人吊上了房梁。当他醒来之后,觉得右膀子沉重闷胀,火燎似的发烧,他的伤口又发了。
野茨在周铁汉身上掏不出一点东西,就在一个夜晚,把三生提了去。
三生,只是这样幼稚的一个十八岁的孩子:长这么大,还不曾出过门,从小就跟着母亲一块下地,一块受苦,没有惹过人,没有骂过人,从母亲那里他承受了善良的性格,也承受了火热的心肠。以至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平事,为什么日本鬼子竟要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抢东西;为什么把周铁汉治得这样苦。他是这样的纯洁,以至还不懂得仇恨。可是,现在他开始懂得了。每一次周铁汉被提走,他就把心提到嗓子上,等他,盼他,希望他快点回来,每一次都等得把心放在烙铁上一样的焦急。可是,被架回来的周铁汉,每一次都是皮开肉绽,半生半死的。三生虽是每一次都竭力忍耐着,到底仍禁不住痛哭失声,热泪滚滚而下。有一次,他一面给周铁汉撕着粘在肉上的衣服,擦着身上的鲜血,一面问道:“干哥,他们也是个人,为什么心就这么狠啊?”
周铁汉答道:“因为咱们是好人!”
也正因为这样,周铁汉对这孩子不大放心。他觉得三生太善良了,因此,他曾在一定程度上不大喜欢他,尤其是不喜欢他的软。譬如,听占维讲起紧张的战斗故事,他就龇牙咧嘴;见医生给自己从伤口里取骨头,他也觉得疼;见自己被敌人治得太苦,就痛哭;都是太软的表现。而软人是没有出息的。所以,自从他俩一块被捕以来,周铁汉一直在担心三生是不是挺得住,会不会说出泄漏机密的话。为此,他和三生谈得很多,教给他要怎样回答敌人,要怎样咬住牙根,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怎样去死。他说:“有些人,本来还没有死,大伙就当他早已死了;有些人,本来死了,可是大伙还当他活着。我们,就是要学那些永远活着的人!”周铁汉把在大“扫荡”中与鬼子同归于尽的张子勤,一次再次的讲给三生听,要他永远记住这个永远活着的人。
三生是个真正听话的孩子。
三生在半夜里被抬回了黑屋,浑身血迹,昏迷不醒地躺着。周铁汉轻轻地抱着他。
慢慢地给他舒胸、撅腿,过了好久,才见他哼哼几声,清醒过来。三生醒来以后,就睁大眼,凝住神朝周铁汉望着。周铁汉也望着他,许久才问道:“你说了没有?”三生说:“说了。”“怎么说的?…‘按照你教的说的。…‘别的呢。…‘别的什么也没有说。”周铁汉松口气,把他抱得更紧些,轻轻晃着,好半晌才说:“好,好!……”三生的眼里忽又涌出热泪来,一面呜咽着说:“干哥,这样的罪,你倒受了四次了啊!……”
案子就这样拖着。
案子拖得太长了,城里的桥本大队长给野茨来了信,让他把周铁汉两个送进城去。
野茨看完信,心里好一阵嘀咕,他想:就这么糊里糊涂把人送去,不能甘心。他素来有一个雄心:凡是经过他手的“罪犯”,都应该弄得“水落石出”。不然,就是在长官面前丢了脸。而周铁汉尤其不能轻轻放过,不能放过这功名,这晋升的机会。这天黑夜,他决心最后把周铁汉折磨一次。
半夜里,周铁汉又被押进了那座大厅。蜡烛的闪闪跳光,透过桌上的玻璃,把野茨的脸映上一层绿色。大厅两厢,干巴巴站着一色鬼子,都是全副武装,上着刺刀,瞪着眼看他,显得分外森严。野茨嗒嗒嗒敲着桌子,好像全不耐烦了似的说:“给你三分钟!
好好地想一想!”于是又说了一套在周铁汉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实话招承,大皇军胸怀宽大,不咎既往,分派给上等差事干;一是就在今夜——死!
野茨以为这样一说,至少要把周铁汉吓掉魂的。可是,他奇怪得很,周铁汉脸上连颜色也没有变,却泰然地笑了笑,清楚地说道:“你自己怕死,别把共产党也想成怕死!
呸!你说得晚了!我从叫你们抓住的那一会就想好了,我还好好地想什么?要枪崩,要刀砍,早就由了你,走!”野茨没有料到今天的戏法会失败得这样惨。但是,什么东西还给他留着一线希望,他无力地挥一下手,鬼子们把周铁汉押出了荒郊。
天上没有月,一片漆黑,只能模糊地看见有人在往前走。转过一座破庙,在一个泥坑沿前停下了。野茨故意用电筒在周铁汉脚下照了照。周铁汉看见在自己跟前是一个污烂的泥坑,阴湿湿黑糊糊的,没有清明的水,也没有翠绿的草,却满撒着炉灰和煤渣;在半截蒜辫子旁边,还躺着一只死猫,皮毛儿脱得秃子似的,嘴扎进泥里去了。一个穿黑制服的“中国人”,装着同情怜悯的声音说:“你看看这块地方好吗?”周铁汉说:“很好。”“不觉得冤枉委屈吗?”周铁汉回过头去,横着眼骂道:“放你妈的屁!我活着也好,死了也好,不和你们这伙汉奸崽子在一块,就干净痛快!”那小子无皮赖脸地说:“哎,朋友!共产党不是你亲娘,你死了,共产党也不哭你,倒是你娘才哭哩!何苦为他们卖命?你今天死在这里,连个人知道也没有,连个人心疼也没有。你只要活动一下心眼,我一只手就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以后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周铁汉肺也要气炸了,恶狠狠地朝那声音抢上去一步,可是立时被鬼子拉回去了,他跺着脚骂道:“死皮不要脸的狗汉奸!人们有一天要嚼你的骨头!”那声音却笑着说:“好了好了,你擎着吧!”哗啦一声,身后几棵枪同时拉开栓,推上了子弹,一齐瞄准了后脑。天又黑又静,没有一丝儿声音,沉重得就要塌下来。周铁汉挺挺地站着,昂着头,闭着嘴,两眼炯炯,望着前面。沉了约半分钟,一个声音突然说:“你说,知道不知道?”周铁汉脸也不同,高声说道:“死了心吧!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啪!几支枪一块响了,周铁汉眼前金花一迸,不由得栽下坑去。
可是,他又被架起来了,鬼子的枪并没有真对准他的脑袋放。他又被关进了黑屋。
一辆汽车停在黑屋的门口,周铁汉和三生被装了进去,又坐上几个鬼子,呜——一声,开着走了。
汽车卷着烟尘,沿着平坦的汽车路飞跑着。一个一个的岗楼闪过去了,一个一个的村庄闪过去了。秋末冬初的天气,风有些凉,人们起先都纠成一堆,汽车走到大陆村附近时,三生和周铁汉却都探出头去,向西北方向望着。透过遍地的水车,透过碉堡似的看园子小楼,在块块相连的麦地那头,在绿色栽绒毯似的大地边沿上,一片黄绿的树丛中,隐约现出一片土平的房顶来,那就是马庄了。
三生望着自己的家乡,第一个想起了自己的老娘,眼里泪花儿滴溜溜转着。这时候他是多么想见一见她的面啊?他想老娘不定怎样地惦记我们呢?不定怎样想得发疯呢?要是她看见了我们,该有多么喜欢呀!他觉得:太需要安慰,也太想安慰一下老娘了。周铁汉望着自己的家乡,第一个想起了那些亲热的同志们:沉默严谨的大队长,开朗尖锐的副政委,高大勇猛的丁虎子,细弱年轻的张小三……他们就在这一个连一个的村庄里头,就在这一块无边无沿的平原上,鱼儿一样的游来游去,他们多么自由自在,多么幸福啊!他们整天都高兴,整天都愉快!……当然,有时也伤心,有时也发愁,那就是想起我周铁汉来的时候。可是,他们伤着心,发着愁,就会想法给我报仇的。
哼!鬼子用枪毙来吓唬我,叫我说给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怎样活动,……简直想掏了我的心!
汽车闪进了宁晋城的东门,嗤一声停在宪兵队的门口。周铁汉两个被架下来,搡进了一座监狱。
这座监狱是鬼子宪兵队特设的,由原来一座民房改成,和宪兵队一宅二院,三间西屋打通,门窗都是一掐粗的木桩子,南头隔壁是茅房,北头一排上房,驻着一个警备中队,是专管“看差”的。周铁汉从木桩门里挤进去,在黑影里,见地下还睡着许多人,一个个长头发,塌眼睛,三根筋挑着脖子,瘦得像一把干柴。三生也被搡进来以后,门外一阵铁链子响,木桩门上了锁。
周铁汉呆呆地站在地下东撒西看,像要认识一下这新的环境。靠墙角的一个犯人坐起来递给他一块被角,拍拍身旁的地下说:“坐下歇歇吧。”周铁汉点点头坐在地下,便也拍拍地下,让三生坐在那块被角上。于是周铁汉悄悄地和那人拉起话,了解着这狱里的大体情形:狱里一共连自己十八个人,大多是抗日的区村干部,也有四五个部队上的。其中靠东墙根门口躺着的,是警备旅的两个伤号:一个伤在大腿上叫黑仓,一个伤在小肚子上叫铁锤儿。他俩不时翻转着身子,哎哟着。
第二天上午,周铁汉被四五个宪兵拥着,穿过一层院,到了一间大客厅。客厅,周铁汉看着非常熟悉,因为很像自己父亲的上房,只是八仙桌子不是靠在条几前头,而是摆在正中间,周围是四把太师椅,不是两把,别的差不多都相同。周铁汉一踏进门,便有个约四十年纪,黑胖油光,身体魁梧的人笑脸迎住,很客气地推过一把太师椅。在桌后,还有个矮胖的小老头儿,鼻下留一撮小黑胡,戴一副黑边眼镜,穿一身黄绿色呢子制服,脚下是洋袜青布鞋。周铁汉知道这是个日本鬼子,可是乍一看,倒很有几分中国气派。周铁汉在就近一把椅子上咕咚坐了,一语不发。那个黑胖子先挥挥手让宪兵们退下去,就欠起身来做介绍道:“这位,是大日本太君桥本大队长,鄙人就是本县的警备联队副郭云峰。嘻嘻!周队长,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请先不要多心,听说你在牙口寨受些委屈,吃些惊吓,我两人备了桌酒席,给周队长压压惊。”说完,看看桥本。桥本温和却又威严地点点头。周铁汉心里一动,不由得掂量了一下对手:一个是全县闻名的铁杆汉奸,一个是狠毒狡诈的鬼子大队长,他们在网什么圈套儿了。周铁汉暗暗捏一把劲,更加了三分小心。
酒宴摆上来了。碟碟盏盏,铺满一桌,有鸡有鱼,有肉有酒,浮漂着一层黄油,冒着打鼻子的香味。周铁汉也叫不上净是什么名堂,只从排场看,便知道是上好的酒席。
郭胖子拿起杯盏满了酒,双手放在周铁汉面前,随后递过一双筷子,开口道:“一切都请放心,今天别的事一字不提,只为周队长压惊。周队长放宽心,请!”说完把酒杯一侧,脖子一直,咕嗒一声下了喉。周铁汉心说:怕什么?吃就吃!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抓起筷子大吃大嚼起来。他吃得非常坦然,眼也不看,嘴也不停,满桌子上乱夹乱挑,拣可口的一箸接一箸直往嘴里填,好像身旁根本就没有别人一样。郭胖子又满上了第二杯,放在他面前。周铁汉瞥他一眼,没有动。一会,满桌的菜,空空落落,下去~大半。周铁汉觉得胃饱肚圆,把筷子拍在桌上,又叉起腰坐在椅子上。临收席了,桥本才开了口,他只翻来覆去说了一件事,就是叫周铁汉现在先养伤,此外,把心放得宽宽的,什么也不要想。最后说:“我的,虽是大日本长官,却喜欢交中国的朋友。你的,~切都请放开,脑子的不要想。”
就这样,周铁汉享受了一番优厚的招待,又被带回了监狱。从这以后,每天有一个医生来给周铁汉治膀子,给他上药,扎绷带,治得很细心。天气冷了,还给他拿来一床被子,一件长袍,一身小棉衣。看狱的警备队“皇协”,也另眼看他,别人上茅房每天只能两次,他却不受限制,还开口闭口的称他为“周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