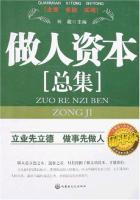海德格尔主张回溯到古希腊早期思想家那里去,这表明了回到思想自身的一种努力,“如果说马克思从生产,尼采从意志来讨论存在问题,那么海德格尔则从思想来追问存在”。由此找到了久被遮蔽、被遗忘的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现在可以看到:存在与思想归属于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本性源于那种让共属”。(ID,S.27)让共属是这种同一性的根基,也是一种相互敞开,“思想与存在的关系,是这样一种相互的自我放弃。在意义上,一方向另一方敞开,一方自身的本性源出于另一方”。回到古希腊思想中去之于追问存在意义重大,“海德格尔要求回到早期思想家去并跟形而上学的开创者们进行论辩,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在早期思想家那儿海德格尔找到了那种很早就被思索而且是作为我们思的事业的思想”。美学一词源于希腊语aisthetikcs,西方美学思想渊源由此可追溯到古希腊。海德格尔向古希腊思想,尤其是向前苏格拉底思想的回溯,体现了他把美和艺术问题建基于存在之境域的努力,这无疑是海德格尔追问与解决现代存在问题的必由路径。
二、存在何以被遗忘?
存在与思想的发端密切相关,存在作为问题之所以被提起,以及对存在的追问,基于存在的被遗忘。存在之被遗忘虽然到现代才充分意识到,却由来已久,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开始了。那么,“存在何以被遗忘”却是一个非常重要,必须给予认真回答的问题。传统形而上学导致了存在的遗忘,“柏拉图以其思想开始了形而上学,把存在者理解为存在者的存在这样的东西,把存在者理解为理念”。(Nll,S.245)形而上学把存在作为范畴看待时,已经开始把存在当做存在者来对待了,存在的意义由此迷失。存在不同于存在者,其本性是虚无,这也是存在容易被遗忘在存在者之中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存在往往不能凭借认知与理性去把握,更导致了遗忘的加剧。
正因为存在被遗忘已久,因此要去重新追问那被遗忘的存在及其意义。“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如众所周知乃追问存在的意义。此存在自身区分于存在者。如此理解的存在却显现为虚无。与此相应不是‘存在和虚无’,而是‘存在作为虚无’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形成主题。存在‘存在着’,凭借于它作为虚无虚无化。”形而上学把存在作为存在者,然而,存在却是虚无。此启示表明,虚无让存在去存在。存在被理解为在场,即存在者的存在,而不是存在自身,这是存在被遗忘的根本原因。同时,存在自身具有的遮蔽性,也导致了这种遗忘。在此,形而上学只能把握存在者,而不能关切到存在自身,存在由此被遗忘。
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的被漠视,与存在的被遗忘是密切相关的,“海德格尔认为忽视这种本体论的区别不仅使得西方哲学而且甚至使得西方文明出现日益增多的失败。因为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越来越远离对于存在的静观,转而研究存在者,最后进而只关心对存在者的技术使用和控制”。在此,海德格尔揭示存在与存在者这种存在论区别被忽视所导致的不良后果。西方形而上学力图在存在者上找到最终根据,这相关于本体论———神学的样式,“正如海德格尔所理解的那样,本体论———神学的哲学探求事物(存在者)———被作为根据的和建立根据的事物———的原因和原则”。这就决定了存在之被遗忘的必然命运。
存在不仅仅处于被遗忘的命运,而且任何对于存在意义的提起,都会被视为多余。“根据希腊人对存在的最初阐释,逐渐形成了一个教条,它不仅宣称追问存在的意义是不必要的,而且还认可了对这个问题的耽搁。”(SUZ,S.3)在人们心目中,“存在”是一个既最普遍又最空洞的概念,这似乎在于:存在既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寻。
这里的关键是:“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虚无却不存在?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GA40,S.3)此存在悖论令人吃惊,使人困惑不已。任何企图通过下定义的方式,来解“存在”之谜的作法都是不能成功的。
由于人们经常用到“存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好像已明白其所指。“于是,那个始终使古代哲学思想不得安宁的隐蔽者竟变成了不言自明的东西,以至于谁要是仍然追问存在的意义就会被指责为方法上的失误。”(SuZ,S.3-4)看来,对存在的追问,不仅需要智慧,而且还要有勇气。为了能让人明白与了解重提存在之意义问题的必要性,也是为了更好地阐明存在究竟是如何被遗忘的,海德格尔着重从与“存在”概念相关联的一些重要方面入手展开分析。首先是“存在”概念的普遍性。无疑,“存在”是最具普遍性的概念。他的独到之处在于,认识到“存在”概念的普遍性,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个别事物之上有种属,种属之上有族类。然而,“存在”的这种最高普遍性,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最高族类。“存在”的最高普遍性,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而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因此,逻辑上关于概念种属类及其包含关系不能用于揭示“存在”的普遍性。海德格尔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进一步探究“存在”之概念。早期希腊文中的physis、aletheia、logos的含义分别是涌现、去蔽和聚集,都是存在的显现。后来,这些词语的意义发生了许多变化,其本义被遮蔽。海德格尔以不同于胡塞尔的视角来看柏拉图,“柏拉图在胡塞尔眼中是某种哲学理性和任务的建构者,只是其终极目的仍在幽暗中沉睡未醒,而对海德格尔来说,柏拉图相反却标志着关于存在思想在哲学中被忘却并规定自身的那个时刻,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只有因为其共同的希腊根源才变得具有决定性”。柏拉图把存在作为理念来把握,是存在意义遗忘的开始,也是其关键。在柏拉图那里,存在被当成存在者,而在概念里把握。海德格尔由于对存在问题的极其关注,从柏拉图那里看到了许多思想家未能发现的东西。
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更为关注存在的本质,力图回归希腊思想的源始经验,但他也未能揭示存在的本质。“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属于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因而亦难逃存在的遗忘的历史。”亚里士多德把与“存在”概念的普遍性相关联的统一性列为类比的统一性,亚里士多德的类比,与关联事实的最高族类概念的多样性相对照。类比关系不同于种属关系,如果说种属关系是一种纵向关系的话,那么,类比关系基于两个事物在一系列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从而确定在其他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类比的统一性关联于不同事物之间的某种属性上的一致性,不再相关于种属关系。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类比仍然未能深入揭示“存在”这个概念。因为,存在的普遍性绝不能凭借一切纵的和横的逻辑普遍性来把握。
在中世纪,“存在”是“超越者”,“超越者”意指跨过边界。托马斯.阿奎那提出“超越者”这个概念,用以指存在、单一、真理和善。在阿奎那那里,存在是超越了种和属之上的超越者,对存在的认识须跨过个别事物的边界,不能以认识一般事物的方法去认识。正是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认为,中世纪把存在作为超越者有道理,但他同时认为,由于究竟如何去把握“存在”这个超越者并未得到阐明,因而,仍然不能从根本上廓清问题。
中世纪的存在论基于托马斯主义与司各脱主义,托马斯主义认为,哲学研究事物的本质与存在,本质是非物质的最根本的实在,本质决定存在。司各脱主义则主张只有个别事物客观存在着,一般只是概念,是同类个别物之间的共同点。总之,中世纪存在论也并不能厘清“存在”这个概念。有的著述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范畴带有神话和信仰主义的性质。这种评价有一定的普遍性,却不能关切存在的本性,也偏离了海德格尔思想自身。
近代的康德强调了思维与存在的分离,“物自体”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具有不可认识性。黑格尔则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但存在只是思维的产物。在黑格尔那里,“存在”被规定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逻辑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逻辑学是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基础与灵魂,逻辑学是研究纯粹概念的科学。逻辑学包括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而存在论是其整个逻辑的出发点。“存在”在黑格尔那里是直接性的概念,存在是作为自在的存在,这里的“自在”指概念处于潜在的、尚未展开的状态。
“存在”概念中所包含的对立要素尚未显露或分化,仍然保持着直接的、源始的同一性,因而,无规定性具有自在的普遍性。黑格尔的存在论处于逻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自在仅关联于概念的多样性。在海德格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被黑格尔忽视了,“在这一点上,他与古代存在论保持着相同的视界,只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与关联事情的‘范畴’的多样性相对的存在统一性问题,反被他丢失了”。(SuZ,S.5)这就是说,黑格尔并未能很好地把握存在问题。有的著述不明白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在“存在”概念上的差异,把二者混为一谈。海德格尔由此表明,“存在”虽是最普遍的概念,但仍然晦暗不明。
近代以来的美学和哲学思想虽来源于古希腊,却发生了诸多变异,使得这些思想正在远离古老的思想传统。笛卡儿的理性主义规定了近代思想,“作为‘我思’,我是此后一切确定性和真理据以立足的根据”。(BW,P.280)对此,“海德格尔重新论述哲学史的方式使我们理解了笛卡儿的这个形象肇始于希腊时代,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出现了这一形象的各种变形。这样一来他就使我们与传统有了‘间距’”。确切地说,正是海德格尔使这一“间距”显现了出来。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儿的“我思”、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尼采的“强力意志”等都并非存在自身。
“存在”概念的另一个特质在于其不可定义性。对此,海德格尔首先提到了帕斯卡尔论及确定存在所带来的荒谬。人无法在试图确定存在(是)的同时不陷入这样一种荒谬之中:无论通过直接的解释还是暗示,人都不得不以“这是”为开始来确定一个词。因此,要确定存在(是),必须说“这是”,并且使用这个在其定义中被确定的词。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源于把定义规定为“属加种差”的逻辑思想。把“存在”理解为存在,而“把存在者归属于存在并不能使‘存在’得到规定”。(SuZ,S.5)其实,这种下定义的方法由来已久。
这里的困难在于,存在既不能用定义的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也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表现。因为,存在是区别于存在者的。“所以,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可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它本身就基于古希腊存在论,但它并不适用于存在。”(SuZ,S.5-6)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往往导致人们不能正视存在及其意义问题。
自明性是“存在”概念的另一重要问题。海德格尔发现,在一切认识和命题中,在对存在者的一切态度中,以及在对自身的态度中,都用到了“存在(是)”。然而,他还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通常的可理解性,不言而喻的可理解性,即这里的概念的自明性却是不可理解,也就是说不是自明的。存在者在这种态度中是明了的,然而存在者背后的存在自身却仍是不明了的,“这表明,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任何态度和存在中,都先天地有一个谜”。(SuZ,S.6)康德把“自明的东西”规定为通常理性的隐秘判断,作为分析工作的重要方面。
这种与理性相关的方法不适合于“存在”这个概念。
这种自明性之于“存在”概念实在是可疑的。如何讨论存在问题呢?“谈论存在问题正是谈论先于和超出任何本体论话语或传统存在论的敞开。”由此看来,康德哲学的错误在于,其认识的形式是主观的,而把认识看成是主观的这种假设,是“纯粹教条的假设”。(FS,S.9)一方面,自明性不可能使存在明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自明性的方法本身就不适切于存在。
海德格尔在此旨在表明,存在问题不仅尚无答案,而且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晦暗而茫无头绪的。存在之被遗忘以及存在问题的这种状况,更加说明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一般存在论把存在作为最高、最普遍的范畴,存在基于逻辑推理,存在成为了存在者。在此,“海德格尔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教导我们严肃地询问什么是‘存在’?
从而把我们从对存在的完全遗忘中唤醒过来”。这是关切存在的思想前提。
那么,海德格尔又是准备如何去重提这个存在问题的呢?他说:“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或只有它才是基本问题,那么就需要对这一发问本身作一恰当的透视。”
(SuZ,S.6)发问即寻找,海德格尔力图在古希腊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联。进而,他说:“只要问之所问是存在,而存在又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那么,在存在问题中,被问及的东西正是存在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