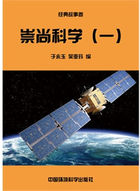果真,这句话一出,云倾城便笑了,“再杀一只鸡,姐姐非杀了我不可。”
她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泪都出来了。心中的苦一瞬间决了堤,收也收不住。
芮妍端来元宵的时候,云倾城一个人坐在那里嚎啕大哭着,哭声在院中回荡,那么响,那么悲怆。
浔玉珩拉了芮妍到身边,“让她哭吧……”
芮妍凝了自己夫君一眼,点点头。她不是看不出这女子的愁楚,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境遇。没有人能代替另一个人走完人生。却总好过没有人陪伴。如今,她能在自己家哭,也算是交了心的。
人生又有多少人能真的与自己交心呢?
云倾城也不知自己哭了多久。只是,哭得累了,便捧起元宵吃起来。吃着吃着便又哭了。
末了,芮妍在她身旁坐下来,牵起嘴角,“明日一起上街。”
云倾城泪眼朦胧地望着芮妍。这个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女子,守着这间不大的院子。一日三餐,与夫君相濡以沫。她突然懂了,陪伴是最真挚的情话。无论风雨飘摇,能陪伴到老是多么的不容易。
她并不是困在往日的囹圄,而是有些事发生了,终是在那里。无力回天。
拭尽眼底的泪痕,云倾城有些不好意思地脸一红,可是让人看了笑话。胡乱抓起手边的棋子随意地就要放在棋盘上。
浔玉珩笑着将她的手一挡,“该吃药了,晚些再落子。”将她手中的棋子收在掌心。
云倾城抬头便能瞧见那人的眉眼,不那么出挑,却有神韵自在其中。瞥了那人一眼,道,“换药方了。等会空闲了,都搓成丸药,你也好好练练牙口。”
说完,便有些后悔,怎么变得如此睚眦必报,小人行径。
对面那两人只是笑着看她,让她一度羞臊,忙端着空碗往门外走去。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说的就是这俩人,一样的妖孽。把她挤兑的无法,又舍不得离开他们,没办法。她渴望这种简单幸福的生活。
肿着两个核桃一样的眼,却笑盈盈地走进厨房的一瞬间,云倾城呆了。
一个多月的心心念念。那人如今就在眼前。云倾城却不知道要说什么,要怎么问。只是定定望着,望着他身上她亲手缝制的长袍;望着那时常出现在脑中丹凤长眼,出现在梦里的墨绿色眸子;望着他的薄唇;望着他如瀑的青丝;望着他缎面靴子上的尘。
“妘儿……”
男子轻唤了一句,张开双臂。
云倾城有那么一瞬间恍惚,妘儿……
牵起嘴角,笑得有些惨烈。心顿顿的疼。垂下眼睛不再看他。将碗筷收好,舀出些热水来。
待云倾城洗好碗筷抬头之际,院中不知何时又飘起了雪。
茫茫的雪纷纷扬扬,每一片都如鹅毛般大。
再回首时,已不见风灵的踪迹。一向来无影去无踪,她该习惯了。既然爱上了风,便要接受他的飘忽不定。
第一次,云倾城有些发疯地追了出去。茫茫大雪中找寻着那一袭白衣的男子。他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她不相信风灵会这样无缘无故地离开,她心里前所未有的忐忑。那不安带着她在冰天雪地的路州城里狂奔。奔跑在每一个她不熟悉的街道。找寻,找寻。
一瞬间,仿佛这世界只剩下她一个,茫茫的雪中她不知道这样的她有多伤悲。只是不停地找,不停……
催动内力,腾空直上。路州城的全貌慢慢出现在眼前。一条街,一条街……
最后,她看见了泰常……
惊身掠过。跟在泰常身后进了一间破落的客栈。
这客栈真的很破,很久,里面约莫也只有几间房的样子。看店的是一对老夫妇,相伴坐在柜台后面。
见客人来了,忙上前招呼,“客满了,客官明日请早吧。”
“我来找人。”云倾城行至柜台前,“请问刚才的公子是住在这里吗?”
夫妇二人相视一眼,“姑娘,恕老汉无可奉告。”
“请老人家明示,他是我朋友,名泰常。”云倾城言简意赅,心却跳的有些急促。心中甚是不安。
“哦。”这时,老人家才将翻开账簿查看登记。
“谢老人家。”
云倾城瞟一眼账簿,便向二楼奔去。
在云倾城推开门的一瞬间。泰常惊呆了。他凝着自己昔日的主子,就在他面前,他无言以对。
“风灵呢?”云倾城瞥了一眼床榻上的女子,她关心的另有他人。
“这……”泰常迟疑了半晌,方道,“公子出城了。”
泰常是说不了谎的。云倾城轻哼一声,奔之旁边的房间。没有人告诉她,她也知道,那人一定在。
这是心有灵犀,虽然不知缘何而起。
云倾城毫不迟疑地推开房门,映入眼帘的一切让她瞬间失去了力气。下身一软,摊在门口。
风雪自敞开的窗中呼啸而过。雪落了一地,地上湿湿的一片。落住的雪白茫茫地遮住木质地板。
风灵靠在榻上,胸前一片血迹,潺潺的血流顺着它早已流经的道路流到地下,汇成一滩,血,艳丽如虹。
云倾城第一次觉得云洲的天那么冷,路州的雪那么冰。她从上至下,从头到脚都被这冰凉的天冻住了。
她却第一时间撑起软的打颤的腿,将房门关好,又去将窗户关牢。
房间里也是冰凉的,地炉早已灭了,血流在地上已经泛起了冰凌。
云倾城将还有些温度的手附上那人冰凉的胸膛。她的心跟着颤动着。她找不到那人的心跳。
慌忙间撕破衣衫,露出他健硕的胸膛。却找不到那人的伤口。只是血似乎从他的肌理透出,滴落,滴落……
心顿时跟着抽搐了。竟是想不出是什么人能让他伤得如此绝望。
“醒醒,醒醒啊!”女子摇晃着男子,奋力摇晃着此时一丝气力都没有的人。
“别晃了。”
泰常不知何时已进入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