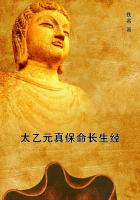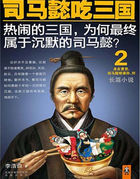阿诺手心一颤,指间花朵坠地,无声无息,令人暗伤。
苦薏上前挽住她的臂,扶她坐下,柔声道:“姑姑,苦薏听名闻影,怕是召氏创的法儿,素闻召氏男子育瓜第一,女子莳花妙手,想来这些糕点也不外乎各种花事相杂调来,或许阿房翁主也会也未可知。”
“阿房翁主若会,早就端来孝敬太后了。怕是她母亲没有留传予她。”阿诺幽幽一叹,为阿房惋惜不已。
苦薏欲开口,门外传来宫女的声音:“诺姑姑,太后醒了,传您伺候呢。”
“好,来了,去吧。”阿诺急忙起身,扶了苦薏的手迅速往正殿而来。
苦薏暗暗咋舌,王太后对阿诺姑姑果然依恋太深了,因这依恋,也束缚住了诺姑姑的手脚,怪不得以她宫中尊贵位分却助不了阿房一力,只能干着急了。
进得殿中,王太后舒适坐在榻上,几名小宫女替她捶着肩头膝盖,见了阿诺二人,太后眉眼含了兴致道:“阿诺,哀家已有数十年未曾好睡眠了,最难得的是也未见恶梦,哀家今天精神儿好,一定要去园中逛逛去。”
“太后这一好眠,果然气色都好了许多,是该出去散散闷气了。也亏得这丫头一首好曲子,随意拨一拨,太后就入眠了。”阿诺含笑上前,伸手扶了太后的臂膀,温醇语语。
王太后展颜大笑:“是了,哀家一喜倒忘了这茬,卓苦薏,哀家要重重赏你。”
“民女一首拙曲结得太后心缘,是民女之福,哪里敢要赏呢。”苦薏恭敬一礼。
“你不敢要赏,哀家却是赏之更欢。来人,把哀家的珠宝匣子拿来,随意卓苦薏挑选,你要多少都是可以的,哀家一眠值千金。”王太后神色亲厚,浓浓的欢喜裹得她全身上下充满仁慈光辉,仿佛祖母一般的情愫,一壁上下打量着卓苦薏,笑道:“你也是富贵之家的小姐,又是替陵儿谋经济的人,要多少子珠宝不得的,但哀家给你的可是一份尊宠。”
“苦薏万般求也求不来的尊宠,苦薏谢过太后。苦薏不敢把这尊宠带到民间糟蹋了去,只求太后恩准苦薏一件事,便是苦薏的福愿了。”苦薏低头,款款请求。
王太后眉头微皱:“哦?何事?比珠宝还金贵么?”
“于苦薏,情义最金贵。苦薏以卑微之躯与人义结金兰,又痴长她几岁,一心只求义妹至福为上,然而天不遂人愿,义妹自小多灾多难,好不容易身体好了,又因犯了花祟被束缚闺中不得游赏之乐,实为人生恨事。苦薏有法子为义妹去除花祟之苦,却力小位卑,说了也无人肯信。”苦薏声调格外幽婉凄酸,听人耳中,着实有戚戚之感。
太后闻言,眉头微拧,不豫道:“你说的可是阿房?哀家知道你们义结金兰,在我皇族金楣,本是欺贵之罪,哀家念阿房少小失母,有失教诲之处,不与她锱铢必较,你今儿提起,言下之意是王宫禁她自由,害她苦楚了?”
太后面上怒色一蓬,隐隐有凌厉绝杀之势,阿诺急得攥紧手心,眼风飞快从苦薏身上滑过,端正姿容,低眸看了台阶,心中狼奔豕突。
“苦薏绝无此意!”苦薏不卑不亢道:“素闻太后最是宠爱阿房翁主,自从翁主贵体违和,太后因爱怜她体弱,减免了她晨昏问省好生休养。翁主感激太后疼恤,一心想早些恢复了身体伺候太后膝下,好替她母妃尽孝,所以趁病着时,捧了她母妃的秘方儿,学会了数十道点心,说是要亲手做了让太后尝尝,实则想尽孝的心儿比什么都大,倒不是图了媚机,就算阿房翁主素日不是伶俐可人的,到底是太后的亲孙女,太后哪有不挂心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