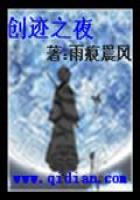织监令身后俏然立了一女子,长发如云铺展开来,仿佛瀑布雅丽芊绵,绿裙松松垮垮,随意挽了腰绦,露出一痕雪脯,艳得人耳根火燎,她绕了一缕黑发于指间玩弄,一壁袅袅上前,放荡地倚在织监令膀子上,吃吃笑道:“织监令,您瞧这几个婢女,虽说肌肤黄了点,倒个个有些姿色,比起先前那几个磨镜强上十倍了,特别是这个,你瞧,倔着呢。”
语毕,一手抬了苦薏的下巴,戏弄地抚了抚她的面,指尖敷红,鲜如血汁,像似一用力,并要划破她柔嫩的脸颊。
一股子腥风隔帘飘来,合殿氲在混浊的污息里,碾在青石板缝隙间,如一枝缠人的藤弯弯绕绕卷上脖颈,呛得人作呕。
苦薏厌恶扭脸,被她一把牢牢控住,妖冶道:“怎么,宁愿做苦哈哈的织娘,也不肯随了我们取乐么?”
苦薏冷眸看她一眼,淡淡一笑:“我不做织娘,更不做取乐的草料儿。”
“看中你是福气,有些人想做料儿还不够资格呢。”织监令手中银月棒猛地扬在她下巴,拧了柳月眉妩媚一笑,笑里一股子邪恶风骚:“黄皮婢女,你们几个去梳洗梳洗,换了这粗布衣,披了我们的风流华衣,才真真有磨镜趣儿呢。请吧,本监可不想久等哦。”
浣嫣水苏懵懵懂懂,睁着玲珑大眼望向苦薏,带着探询的味道。
那凤眼女子眸华收缩,眉心坠落一尾秋色,有一缕惋惜。
苦薏缓缓推开织监令的银月棒,倨傲扬了扬眉,冰泠泠道:“织监令真会取乐,磨镜虽好,终不及男女真情!织监令风华正妙,何不配了绝色儿郎,方是如鱼得水鹣鲽之欢呢,躲在这里学那颠鸾倒凤,妙不过一分罢了。”
浣嫣水苏本是聪明如莲的女子,闻言羞得低首垂眸,不敢再看这对风流的女子姿态,卓府之中女子一到十三四岁必然要配了府中小厮,否则按大汉法律,是要分五等交算税的,到三十岁还未嫁加到五算,即一年要交六百钱,王侯将相府中的婢女免税,旁人却无这样的厚恩。所以二人从小呆在卓府内,从未闻过什么叫磨镜。
甫时闻得,才知世间还有一种女子间的污垢,令人愤懑羞耻。
狭长窗外一帘日落,漫天的红晕灿丽扰魂。
苦薏焦灼屏心,一壁应付两枚轻浮媚眼的女子,烦燥一波接一波披拂在身。
却又黯然神伤,女子与女子的冤孽从来就不是轻易而过。
织监令懒惫盯她一目,眸心剜了如雪的光芒,如兽森森笑开:“婢女,既来了这里,就由不得你百伶百俐,本监看上的从来就逃不出银月棒,睁大眼瞧我的棒儿。”
银月棒闪着如雪的白寒,除了执柄外,通身扎了银针,难怪那样诡谲的光芒,刺人眼疼。
苦薏拉紧浣嫣水苏往后速退几步,心头怦怦,这一棒下来,凭谁也熬受不过。
想不到堂堂王宫,竟有如此惨烈的刑具。
苦薏美眸含怒,细细审着她,一壁想着稳当应策,心越急越是半筹不纳。
织监令举着银月棒娓娓逼来,红媚媚的樱唇噙了志在必得的笑意,那般龌龊,那般酸人心腑,仿佛一阵阵冬雨挑衣刺肤。
绿衣女子搔首弄姿,嘴里咬了青丝,吃吃娇笑,时不时抛来一个媚眼。
“慢着,三翁主等会子必来提审我们,若是不见了我三人,只怕三翁主拿你是问。”银月棒挨着耳边,苦薏急中生智,不顾一切叫道。
银月棒稍稍止住,带着狐疑的神色:“提审?进了这里,还有活路么?本监掌管数年,未曾见过主子们有新鲜的劲儿。”
“我们本不是王宫中人,被太子误带进来的。翁主见过太子证实我们无辜,自然会在天黑前送我们出城。你若拿我们取乐,惹恼了翁主贵颜可不是玩的。”苦薏臂上汗珠如水滑落手内纹理,湿透浣嫣水苏的掌心,弄不清谁是谁的了。
“哦?民女?竟敢与太子有了龃龉,也算是大胆狂逆了,怪不得翁主要关了你们!真真不知天高地厚,还当翁主会来救你们,做梦吧!他姊弟二人最是亲厚无比,就算太子有错,也是偏袒相向,哪里会与你做主,臭丫头,跟我走,再不走,我让你生不如死!”织监令不耐烦剜她一眼,嗤之以鼻。
“织监令此言差矣,翁主虽与太子亲厚,但淮南王却是无为而治,以德懿人,不许伤害百姓。何况扶璎女侠已晓得太子之恶,正前往觐见淮南王,势必就要遣人来接我们出去。织监令高居此地久矣,自然不晓得江湖‘庆云剑’的厉害,就算淮南王未曾见着,等会子定会闯进来要人,你到时无人可放,贵命也难保了。”苦薏侃侃而谈,不卑不亢,越性挺直后背,昂头直视着那令人厌恶的织监令,心底想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