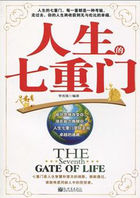穆宗沉默良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甚事?不是内宫坏了,先生怎知道。”究竟是什么事,高拱漏记了关键的一句。据何乔远的记载,这段话是:“非内官辈,先生安得知?盖宫中事也。”宫中事,即皇上的宫闱生活,臣下当然不便细问,皇上也不便明说。两人手拉着手一同默然前行,进入皇极门(金水桥北,前朝三大殿正门),走下丹墀,穆宗向内侍要茶。内侍搬来椅子朝北放下,穆宗不坐,移为南向后,才坐下,用左手拿起茶杯,连饮数口。他的右手仍握住高拱的手不放,抬眼望去,说了声:“我心稍宁。”便在高拱陪同下由东角门入内,一直走到乾清门。乾清门位于建极殿后的云台左右门东侧,夹于景远门、隆宗门之间,是内廷三大殿的正门,再往里是乾清官大殿,是皇帝的寝殿。高拱礼貌地停止了脚步。穆宗意犹未尽,牵着高拱的手说:“送我!”话中显然带有命令的意思。高拱不敢抗旨,便随同进入寝殿。穆宗登上御榻坐定,右手还握住高拱的手不放。从御路一直到寝殿,穆宗始终握住高拱的手,时时颜色相顾,眷恋之情蔼然,言谈间还流下眼泪。
这时,内阁次辅张居正、成国公朱希忠都已进入寝殿,在御榻前向皇上请安。站在皇上身边的高拱一手被皇上握住,只能鞠躬,不能屈膝叩头,面对同僚的叩拜颇为尴尬。穆宗也看出了元辅侷促不安之状,得体地松开了手。高拱赶紧走到御榻下,向皇上叩头,并与张居正、朱希忠一行辞出宫门外候旨。
须臾,穆宗遣内侍将高拱等人召入。高、张、朱站立于丹墀,恭候圣旨纶音。穆宗却命他们再上前,待三人在御榻前立定,他从容说:“朕一时恍忽。自古帝王后事……卿等详虑而行”。三人叩头后,退出乾清门外候旨。少顷,内侍高声传旨:“着高阁老在宫门外,莫去!”高拱随即对张居正说:“我留,公出,形迹轻重唯为公矣。公当同留,吾为奏之。”便对内侍说:“奏知圣上,二臣都不敢去。”
到薄暮时分,内侍传旨:“高阁老宿宫门!”高拱碍于宫内礼仪,回奏道:“祖宗法度甚严,乾清官系大内,外臣不得入,昼且不可,况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当出端门宿于西阙内臣房。有召即至,有传示,即以上对,举足便到,非远也。”显然,穆宗从正月大病后,心有余悸,已经在考虑后事了,今日召见三位亲信大臣时,就流露了“后事卿等详虑而行”的心思。自知去日无多,不知那一天逝去,应预作安排,所以才命阁老在宫内过夜。高拱不愧足智多谋,想出了两全其美的方法,在离乾清官咫尺之遥的西阙太监直庐过夜,静候传唤。既然内阁辅臣留宿西阙,那班五府六部大臣们也都不敢回家,只得留宿朝内,谓之“朝宿”。以后几天亦复如此。不久,内侍传来消息:“圣体稍安”。高拱兴奋得马上写了一个札子呈上:“臣闻圣体稍安,不胜庆幸。今府部大臣皆尚朝宿不散,宜降旨,令各回办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昼夜在内,不敢去。”穆宗以为然,即时降旨,命百官散去。而高拱、张居正仍每日问安如初。过了四天,穆宗觉得身体“益平愈”,便遣内侍慰劳高、张,命他们回家,一场虚惊才算过去。
有一天,穆宗兴致较好,乘坐轿子来到内阁,高拱、张居正大吃一惊,急忙出迎,俯伏在地。穆宗将二人扶起,搀着高拱的手臂,仰望天空良久,欲语还休。高拱搀扶穆宗行至乾清门,穆宗才说了一句:“第还阁,别有论。”到了第二天,又寂然无声息。善于机变的张居正从旁细细观察了皇上的脸色,“色若黄叶,而骨立神朽”,已经病入膏肓,虑有不测,便暗自写了关于皇上后事的处分十余条,密封后派小吏送给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上不豫增剧”的消息,五月二十五日又传出“上疾大渐”的消息。这一天,穆宗召见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到乾清宫受顾命。高拱等急急忙忙进入寝殿东偏室,但见穆宗倚坐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隔着帷帘坐在御榻边,皇太子朱翊钧立在御榻右面。
此时坐在御榻边的皇后,即孝安皇后陈氏。陈皇后无子,因被穆宗移居别宫,抑郁而病。外廷传闻此事,议论纷纷。不久,陈皇后还是回到了坤宁宫。坐在皇后身边的皇贵妃李氏,即皇太子朱翊钧的生母。站在穆宗御榻右边即皇太子朱翊钧。
当时的情景颇有一点凄凉之感。高拱等跪在穆宗御榻下,倚坐在御榻上的穆宗,命高拱伸手上来,自己的手靠着榻上的矮几伸过去,抓住高拱的手,一面望着身边的后妃,一面对高拱托孤,断断续续地说:“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尔后便命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遗嘱有两道,一道是给皇太子的,一道是给顾命大臣的。
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
“遗诏,与皇太予。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
“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竹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这个遗嘱,引起外廷大臣的议论。高拱极力扬言是张居正与冯保所拟,并非皇上本意,尤其对于其中“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攻击最力。这不免有点过分,且不说穆宗托孤时曾亲口对他说:“事与冯保商榷而行”,可以为证。而且,当时在场的皇贵妃即后来的慈圣皇太后,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在一道慈谕中说:“司礼冯保,尔等亲受顾命”云云,更是确证。由此可见,穆宗的遗嘱虽为张居正与冯保所拟,但并未违背穆宗原意。《实录》纂修官在修史时疏于考订,为调和矛盾,竟将遗嘱中“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删除。见于《实录》的遗嘱是这样的:“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高拱亲受顾命,他又从冯保手中领受了遗嘱文本,在回忆录《病榻遗言》中抄录了遗嘱的全文,明白写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而且他事后还多次对这一句话发表议论,以为“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实录》的这种删削,为了某种政治意图,掩盖史事真相,实在不足为训。
高拱等听完穆宗顾命之辞,大为悲恸,不能自胜,边哭边奏说:“臣受皇上厚恩,誓以死报。东宫虽幼,祖宗法度有在,臣务竭尽忠力辅佐。东宫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爱其死。望皇上无以后事为忧。”且奏且哭,奏完便大恸长号不止。在旁的皇后、贵妃也失声痛哭。少顷,两名内侍扶起高拱等,三人长号而出。
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六日,穆宗死于乾清官。他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二十三日,卒于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终年三十六岁(虚岁),在位仅六年。次日发丧,向全国颁布遗诏。遗诏中写道:
“朕以凉德,缵奉丕图,君主万方,于兹六载,夙夜兢兢,图惟化理,惟恐有辜先帝付托。乃今遘疾弥笃,殆不能兴。夫生之有死,如昼之有夜,自古圣贤其孰能免?惟是维体得人,神器有主,朕即弃世,亦复何憾。皇太子聪明仁孝,令德天成,宜嗣皇帝位。其恪守祖宗成宪,讲学亲贤,节用爱人,以绵宗社无疆之祚。内外文武群臣协心辅佐,共保灵长,斯朕志毕矣。”
“其葬礼悉遵先帝遗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毋禁音乐嫁娶。宗室亲王,藩屏是寄,不可辄离本国。各处镇守、巡抚、总兵等官,及都、布、按三司官员,严固封疆,安抚军民,不许擅离职守。闻丧之日,正于本处朝夕哭临三日,进香遣官代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及各布政司,七品以下衙门,俱免进香。”
“诏谕中外,成使闻之。”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按照遗诏的规定在进行着。从遗诏也可以看出穆宗的秉性与风格,他不要大事声张,不让宗室亲王来京治丧,不许封疆大吏擅离职守。他是在明朝历代皇帝中最不显眼的一个,在位仅六年,只比惠帝(建文)、仁宗(洪熙)稍长一点,而无法与其他诸帝相比拟。他虽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却也有自己的特色:清静、宽仁,所谓“清静合轨汉帝,宽仁比迹宋宗”。把他与汉文帝、宋太宗相提并论,未免有点溢美,不过清静宽仁倒是事实。他一上台,就一改先皇(明世宗)的苛政,“黜不经之祀,绝无名之狱,除烦苛,节浮冗,恤贫困,理冤滞,崇奖遗逸,汰斥险邪”。据说,他在裕王府时,厨师常烩制一道名菜驴肠,令他爱不释口。即位以后,问明左右侍从,才知道是烩驴肠,颇为于心不忍。便下令光禄寺停止制作此菜。并对左右说明道理:“若尔,则光禄寺必日杀一驴,以备宣索,吾不忍也。”每逢岁时游娱行幸,光禄寺为供膳煞费苦心,必提前将各种菜单呈上,请旨裁定。穆宗总是选取最简单的方案,以示节俭。他是一个刚德内用,柔道外理型的帝王。在宫闱掖庭,他极严格,“周防慎察,严肃整齐,无敢出声”;而临朝理政,与大臣接触,则施以宽仁柔道。“臣庶廷谒,小不如仪,常假借宽宥左右近侍,未尝轻降词色”。
穆宗死后的第二天,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前往天寿山相度陵墓。九月十一日,穆宗的梓宫(棺材)起程运往昭陵。十七日,张居正前往昭陵,题写神主牌位。据张居正事后的报告,昭陵的玄宫,精固完美,有同神造,山川形势结聚环抱。九月十九日辰时,迁梓宫入皇堂,行题神主礼毕,穆宗遗体即奉安于献殿。未时,掩闭玄宫,葬礼完成。
国不可一日无君。既有先帝付托,穆宗死后的第三天,即五月二十八日,内阁元辅高拱等就上了《劝进仪注》,希望皇太子早日即帝位,并拟就了登极的仪注,也就是穆宗临终前所说的“一应礼仪”。
五月三十日,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在会极门上表劝进。这个劝进表是“一应礼仪”的第一步。表文空洞却通篇充斥莫明其妙的深奥感,什么“伏以三灵协祜,衍历祚以弥昌;四海宅心,仰圣神之继作。传序所属,推戴均钦”;什么“龙髯已堕,徒瞻恋于臣民;燕翼惟勤,诞敖遗于后嗣”;什么“敬惟皇太子殿下,徇齐歧嶷,恭敬温文,日就月将,睿学聿隆”,“惟以承祧为重,固宗庙社稷之攸赖”云云。朱翊钧接到劝进表后,为了表示某种姿态,遵从某种礼仪,没有立即同意所请。他谕答道:“览所进笺,具见卿等忧国至意,顾于哀痛方切,维统之事,岂忍遽闻,所请不准”。
六月初一日,天刚亮,有日蚀。百官们忙于穆宗丧事,哭临于思善门;哭临毕,又赴礼部行护日礼。官员们一律丧服:青服角带,停止鼓乐。礼毕后,仍各就各位,素絰办事。
少顷,朱翊钧身穿縗服来到文华殿。文华殿在会极门东侧,是皇帝与大臣商讨国家大事的地方,前殿匾额写道“绳愆纠谬”。他在这块匾下再次受到百官上表劝进。劝进表重复了上次的语句以外,强调“神器不可以无主,天位岂容于久虚”。朱翊钧看完后,召内阁辅臣人内,交谈片刻,即传谕:“卿等为宗社至计,言益谆切,披览之余,愈增哀痛,岂忍遽即大位,所请不允”。
六月二日,朱翊钧縗服至文华殿,百官第三次劝进。这次,他不再推辞了。阅毕笺文,召见内阁、五府、六部等官僚,稍作商议,传出谕旨:“卿等合词陈情至再至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况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从所请。”
六月初三日,礼部遵旨呈上登极仪注。六月初十日,皇太子朱翊钧正式举行即位典礼,宣布改明年为万历元年。这样,他就成了明朝第十三代皇帝,即明神宗。
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按照惯例颁发大赦诏书,开列了十几条大赦事宜。诸如:
自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以前,官吏军民人等,凡是犯有窃率、逃军、匿名文书、未及害人谋杀人伤而不死者,悉免处死。至于犯该死罪,监禁十五年以上,笃疾者免死释放;
宗室往年因事减革俸禄者,诏书到日,全革者准支三分,减去一分,二分者准全支;
宗室子女奏请名封选婚者,即题覆施行;
凡在凤阳高墙内禁锢的宗室,本人已故,所遗子孙妻妾无罪拘系,未及放回者,奏请释放;
自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元年拖欠钱粮(赋税),除金花银外,悉从减免;隆庆二年至四年拖欠钱粮,减免十分之三;
陕西、苏州、杭州、嘉兴、湖州、应天等处,差人坐守织造之丝绸等项,悉皆停免;
自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后至隆庆六年五月以前,因上疏建言获罪诸臣。如果情非挟私,才力堪用者,议拟具奏起用。
这些,表明了他力图振兴朝政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