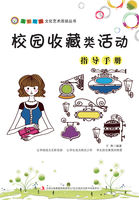刚开始的那些日子,每一天对于玛丽·朗诺克斯都是一模一样的。每天早上,她在挂着壁毯的那间屋子醒来,就会看见玛莎跪在壁炉旁生火;每天早上,她都在那间毫无生趣的“儿童房”吃早餐;每天吃完早餐之后,她就盯着窗外,眺望着那无边无垠的荒原,看着它四处延伸,直到天边;盯了一会儿之后,她会知道要是不出去走走的话,自己就只能无所事事地呆在屋里——于是,她就往外走去。但是,有一点她是不知道的:每次她一开始快步走或是跑起来,浑身的血液就被激活了,让她的身体越来越棒,对抗荒原上刮来的大风是最好的锻炼。其实,她跑起来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暖和些。她恨死了狂风,吹痛了她的脸,在她耳旁咆哮,还把她往后刮——它是那么狂妄,仿佛自己是个巨人,而玛丽却看不到它。但是,每当玛丽大口大口喘气的时候,石楠花带来的新鲜空气却对她那瘦弱的身体大有好处,她的面颊上开始泛起了红色,她那原本呆滞的目光也开始明亮有神起来了。当然,她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在外面疯跑了整整几天之后,一天早上,玛丽醒来后,突然有了饥饿的感觉。在她坐下来就餐时,她不再鄙夷地看一眼稀饭就推开了,相反,她自己拿起了汤匙,开始吃起来,一口气吃了个底朝天。
“你今天早上表现不错,是吧?”玛莎说。
“今天的稀饭真好吃,”玛丽说,自己也有些吃惊。
“是荒原上的空气让你有了胃口吃饭,”玛莎回答说。“想吃又有得吃,你真是命好啊!我们那穷家里可是有十二张嘴没东西吃呢!只要你坚持每天出去跑一跑,你的骨头上就会长肉了,脸色也不会那么蜡黄蜡黄的了。”
“我没玩,”玛丽说,“没什么可玩的。”
“没什么可玩的?!”玛莎惊呼,“我们这儿的孩子玩的是石头啊,棍子啊,到处疯跑啊,尖叫啊,东张西望啊。”
玛丽也会东张西望,但是她不会乱喊乱叫。除此之外,没有其它什么好玩的。她总是在花园里走过来走过去,在公园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有时候,她也会去找找本·威勒斯塔夫。可是,好几次她都看见他在干活,很忙的样子,顾不上理她,而有时候,他又显得太冷漠了。有一次,她正朝他走去的时候,他却拿起铁锹就转身走了,好像是故意似的。
有一个地方,是玛丽最常去的。就是围着墙的那些园子外面,那段长长的路。路的两边,是什么也没种的花圃,但常春藤却爬满了墙头。有一段围墙上的常春藤比其它地方都要长得浓密,绿油油的一片,乱作一团。看起来似乎很久都没有人留意过那个位置了。其它地方的常春藤都袖箭得整整齐齐,但在这个并不是很高的位置,却压根没有修剪过的痕迹。
在第一次和本·威勒斯塔夫说过话的几天之后,玛丽站在那个奇怪的地方,看了又看,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她刚刚消停下来,抬头看着一簇长长的常春藤随风摇摆,这时,她突然看到了一道红光,听到了一针悦耳的鸟叫声。原来,在墙头上,正站着本·威勒斯塔夫的知更鸟呢!它正歪着脑袋、低着身子看着玛丽呢!
“噢!”她不由得喊出声来,“是你吗?是你吗?”毫不奇怪,她完全相信小鸟能听懂自己的话,所以才会那样和它说。
知更鸟没有回答,而是在墙头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叫着,仿佛有很多东西要告诉她。玛丽小姐似乎明白了小鸟的意思,尽管它并不是在说话。它好像在对她说:
“早上好!今天的风儿很棒吧?太阳很棒吧?一切都很棒吧?我们一起跳吧,一起叫吧,一起唱吧。来吧!来吧!”
玛丽笑了。知更鸟沿着围墙飞着跳着,玛丽就跟在小鸟后面。平日里瘦小、蜡黄、难看的玛丽,那个可怜的小姑娘,这时竟然露出了自己美丽的一面,妩媚动人。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她叫喊着,一路上都在喊个不停,她还学起了鸟叫,甚至还试着吹口哨——当然,到了最后她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吹得响。但知更鸟似乎很高兴,也对着她叫个不停。最后,它振翅一飞,落到了一棵树的树梢上,放声歌唱起来。那上面可有它的小巢呢!这让玛丽想起了第一次看到它的情形。
知更鸟一直在树梢上荡秋千,而那棵树就耸立在果园里。其实,玛丽和它们之间还隔了矮矮的一堵墙,玛丽正站在围墙外头的一条小路上,而那棵树却在园子的里头。
“它在那个没人能进去的花园里,”玛丽对自己说,“就是那个没门的花园。它就住在那里面。我多想看看那花园的样子啊!”
于是,她跑向第一天早上进去过的那道绿门,然后又沿着小路跑到另一道门,进了果园。当她停下脚步,抬头看去的时候,发现那棵树却还是在围墙的外边,知更鸟刚刚唱完了歌,正在用小嘴梳理自己的羽毛呢!
“一定就是那个花园,”她说,“我肯定它就是。”
玛丽绕着果园的围墙,慢慢地、仔细地搜寻着,但却一无所获——和前几次一样,没有门。然后,她又穿过菜园子,跑到长长的常春藤遮蔽着的那堵墙。她先在一头细细查看,但那儿也没有门;她又走到另一头,但也没有。
“太奇怪了!”她自言自语,“本·威勒斯塔夫说过没有门,看来的确没有。可是,十年前一定有的,要不然,克拉文先生为什么要把钥匙埋掉呢?”
这样一来,玛丽要想的东西就很多了,这一切都让她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她也不再因为来米歇尔·怀特庄园而难过了。在印度时,她动不动就生气,懒洋洋的,对一切都是爱理不理。事实是,荒原刮来的大风吹走了她脑子里那些乱糟糟的东西,让她清醒了不少。
几乎整整一天,玛丽都在外头跑来跑去,所以,当她坐下来吃晚餐时,已经是又累又饿,但却浑身很舒服。玛莎在一旁唠唠叨叨的时候,玛丽也不生气,她感觉自己似乎很喜欢听玛莎说话。听到最后,她决定问玛莎一个问题。她吃完晚饭,就坐在了炉火前的毯子上。
“为什么克拉文先生会那么讨厌那个花园呢?”她问道。
玛丽让玛莎和自己多呆一会儿,玛莎也丝毫没有拒绝。玛莎年纪很小,早习惯了和一大群兄弟姐妹挤在小小的屋子里。在楼下那间宽敞的佣人房里,男佣和资格老一些的女佣们总是嘲笑她的约克腔,总是坐在一起窃窃私语,总是不把她放在眼里。玛莎喜欢说话。这个印度来的怪怪的孩子、过去一直被“黑鬼”伺候着的玛丽,让她看着新鲜,充满好奇。
不等玛丽请她,她已经一屁股坐到了地毯上。
“你还在想着那花园吗?”玛莎说,“我知道你会想的。我刚刚听说时,也是这样。”
“他为什么讨厌呢?”玛丽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思。
玛莎把腿蜷起来,这样坐着让她很舒服。“你听,外面的风呼啸得多厉害啊!”她说,“今天晚上要是你在荒原上的话,一定站都站不起来。”
玛丽不知道“呼啸”是什么意思,但听着听着就明白了——它应该是指狂风大作,绕着房子咆哮个不停,仿佛有个无形的巨人在摇曳着房子,敲打着门窗,想要破门而入。但谁都知道,它是进不来的。所以,能呆在屋子里,还烧着红红的炭火,真是让人感到既安全又温暖。
“可是,他为什么如此讨厌那花园呢?”她听完之后,再次问道。她想弄清楚,玛莎到底知不知道。
玛莎终于还是决定不再对玛丽保守秘密了。“记住,”她说,“梅德罗克太太说谁也不许谈论此事。这里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随便议论的。那是克拉文先生的命令。他说,他自己的问题不关佣人们什么事。要不是因为那个花园,他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是克拉文夫人的花园,是她自己叫人修起来的,当时他们刚刚结婚。她很喜爱那花园,他们过去都是自己打弄那些花花草草。园丁们都不许进入那花园。克拉文先生和夫人进了花园之后,总是把门说起来,在里面一呆就是好几个钟头,看看书呀,聊聊天啊。那时,夫人其实还是个女孩子。花园里有一棵很老的树,树上有一根枝丫,弯弯曲曲的,长得就像一把椅子。夫人就在那‘椅子’上种了点玫瑰花,她还经常坐在那个地方。但是,有一天,正当夫人坐在树上的时候,那树枝突然断了,她掉了下来,落到了地上。夫人的伤势很重,第二天就去世了。医生们都认为克拉文先生一定会疯掉,然后也死去。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恨这花园。从那以后,谁也没进去过,他也不许任何人谈起它。”
玛丽不再问什么了,她看着红红的火焰,听着大风的咆哮。现在,风儿似乎咆哮得更起劲了,呼啸声越来越大。就在这时,她的身上有了些积极的变化。自从来到怀特庄园以后,她有了四种变化,而这些对她都是有好处的:她感觉自己能理解知更鸟,而知更鸟也理解她;她一直在风中奔跑,浑身的血液都活起来了;她生平第一回有了饥饿的感觉,这是一种健康的体现;还有,现在,她明白了为别人难过是什么滋味。
而就在她听着风的时候,她开始听出了些别的东西,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一开始她根本听不出那和风声有什么区别。那是一种怪怪的声音——似乎是有个孩子在哪儿哭泣。有时候,风儿听起来就像孩子在哭泣一样,但此时此刻,玛丽小姐确信,这声音是从房子里传来的,不是外面来的。这声音听起来很遥远,但却是在房子里的。她转过脸,看着玛莎。
“你有没有听见哭声?”她问。
玛莎突然一脸茫然。“没有,”她回答说,“那是风。有时候听起来就像是有人在荒原上迷路了,在号啕大哭。荒原上有很多声音。”
“可是,你听,”玛丽说,“这声音是在房子里的——在其中的一道走廊里。”
就在这时,楼下肯定有一扇门被打开了,因为有一阵大风冲进了过道里,而她们这间屋子的门也被撞开了,她们都跳了起来。烛火被吹灭了,那哭声穿越了整个走廊,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
“听见了吧!”玛丽说,“我说的对吧!就是有人在哭——是个孩子!”
玛莎跑着去把门关上,想用钥匙把门锁上,但她还没来得及锁门,她们又听到了远处有一扇门“砰”的一声重重关上了。然后,一切都陷入了沉寂,甚至连风都听了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咆哮”了。
“那是风,”玛莎固执地说,“如果不是风,就一定是小贝蒂,小厨工贝蒂·巴特沃斯,她整天都牙疼。”
但是,她说话时的神情显得十分焦虑,很不自然。玛丽小姐非常严肃地盯着她,她不相信玛莎说的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