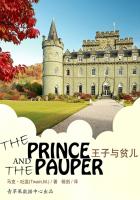据说,马德胜一直抱着林凤鸣的身体哭了老半天,直到林凤鸣的身体在寒冷的雪天里冻成了冰疙瘩,他才在很多人强拉硬扯下离开那具尸体,为了不让人把林凤鸣的尸体抬走,他拔枪顶着医护人员的脑袋,差一点要了那个人的命。林凤鸣被埋葬在朝鲜人民军的英雄公墓里,在战后归国前马德胜还独自去祭奠了他。那一天,他醉倒在了林凤鸣的墓碑前哭了整整一夜。我父亲答应过给他好日子过,可他才结婚九天就接到命令返回了部队,随后奔赴战场。新中国的大门他们都迈进来一只脚了,却没有享受到他们渴望的幸福。
4
尚玉婷在野战医院生下我,她打电话到堑壕里让马德胜为我取个名字。马德胜没好气地说了一句话,还起什么名字,这是个催命的玩意儿,没有他,小林子也不会死,还起名字,叫他催命鬼。尚玉婷很生气,她对着话筒哭着骂马德胜,干嘛诅咒孩子。
从朝鲜回国,我才有了名字。我叫马天龙,名字是母亲起的。这么俗气的名字作为一个符号伴随了我的一生。但在父亲马德胜嘴里,他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叫过我的名字,他张口就是催命鬼。所以,我的小名就叫催命鬼。
马德胜晚年的时候喜欢作画。他的书房门前有他自己的挥毫题名:龙虎斋。推门进去,一张行军床,一个庞大的作战沙盘,沙盘上是两军对垒的厮杀,满屋的墙壁上却龙腾虎跃,纵横山河。他一般只画两种东西——一是龙,二是虎。他的龙虎图画法自成一派,长龙飞卷,时而长啸,时而低吟;猛虎入山,时而怒吼,时而眈目。他的画因技法怪异,构图大气磅礴,笔下龙虎传神,所以在当地很有名气。
我做师参谋长命令下来的那个晚上,他温茶煮酒,为我画了一幅张牙舞爪的青龙,题字曰:龙生云。我接过青龙图,可龙爪之下并没云朵,空荡荡一片。我在他心目中就是这么一条性格乖张、张牙舞爪的龙。马德胜说,如你性格,霸气有余,胸怀狭窄,所以你脚下无云。什么是你的云,云是你的兄弟,你的朋友,团结在你周围的人,他们都是你的云,你要记住,心比天大,情比海阔,否则,你注定是一条脚下无云的龙。马德胜还说,如果不能飞翔,你只能是条蚯蚓,匍匐于大地之上艰难爬行,你飞龙在天的理想最终只会是你的仰天长叹,戎马一生的马德胜说这话的时候像一个极富哲理的诗人。知子莫若父,他对我的了解深入骨髓。这是我的缺陷,很多时候,我因为这样的缺陷把自己陷入困境。
马德胜承认我是一条龙就已经很不错了。我的两个哥哥在他心目中连条虫都不是。我的大哥马天彪在北海舰队当海军,一次海却没下过,在基地的后勤供给部门喂了五年猪,复原时,带着一身猪屎的味道回到了家中;我的另一个哥哥马腾飞在空军地勤,工作还算努力,职务干到了副连长,后来因为跟副团长打架背了个处分转业了。我父亲把我大哥叫作蠢材,把我二哥叫作笨蛋。可就是这两个蠢材和笨蛋,后来个个都成为了商界精英、地产大亨。尽管如此,马德胜临死都没让我的两个哥哥进过他的龙虎斋,他们都有上亿的资产,但从没有得到过父亲的一张画。
马德胜死后留下龙虎图三千八百七十六张,全部随遗体火化,他说这三千八百七十六张龙虎图要送给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这些人活着是他的兵,死后仍然是他的龙虎之师。
我不喜欢我的父亲马德胜,甚至不喜欢他强加在我名字前面的那个姓氏。我母亲喜欢叫我的名字龙,我也喜欢别人叫我龙。我就是龙,可龙行天下,一切从磨难开始。
虎
1
我没有见过我父亲林凤鸣的模样,他也只是母亲段腊梅生活中的一段故事,或者是她回忆里的一阵风,娓娓道来之后,就又匆匆地刮走了。林凤鸣这个有点像女人的名字却一直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作为生命的烙印,伴随我的一生。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被称作英雄的符号。
我曾经无数次对着镜子想象林凤鸣的模样,中等身材,精瘦但很健壮,眼睛不大但很明亮,长着一双顺风耳,想事情的时候耳垂能一竖一竖地动。在母亲段腊梅的语言描述中,他永远穿着一身米黄色洗得有些泛白的军装,一尘不染的黑皮鞋,时光永远停留在他英俊潇洒的青年时代,挺拔,帅气。他这样的形象也曾无数次走进我的梦里,但直到今天,他也仅仅是我的一个传说而已。直到有一天我长到他当年和母亲相亲的年龄,穿着一身军装走向母亲,才饱含热泪地告诉我,是这个样子,你的父亲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林凤鸣和段腊梅婚后只相处了短短九天就走了。他所在的部队正在朝鲜作战,他的假期只有二十天,往返的路上就要走十一天。他们从相亲到结婚只用了三天时间。段腊梅说林凤鸣用九块钱,一袋红薯干面就把如花似玉的她娶进了家门。那时候,林凤鸣是野战部队枪林弹雨走过来的解放军连长,能嫁给这样的男人,她感到无上光荣,即便是不给那九块钱和红薯面,她照样会嫁。
可光荣无法改变贫穷。林凤鸣下面有六个弟妹,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林凤鸣的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多病不能劳作,家徒四壁,六七张嘴就指望林凤鸣一个人的津贴。漫长的贫瘠岁月,饥饿时刻都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尽管这样,段腊梅还是不顾父母的阻拦嫁给了他。
爱情让女人变得如此的愚笨和迟钝。在那个秋阳高照的上午,十九岁的段腊梅得罪了全家的人嫁给了比她大十岁的男人林凤鸣。没有花轿,没有马车,也没有吹吹打打的乐队,林凤鸣牵着一头从互助组借来的毛驴就把她接回了家。林凤鸣说,他不想大操大办,家里也没钱大操大办。而段腊梅竟然就依了他,她说她就相中了林凤鸣这个人。
空旷的田野静悄悄的,深秋收获后深翻的泥土散发着迷人的馨香。段腊梅坐在那头羸弱的毛驴背上,偶尔悄悄掀开盖头偷看一下走在前面的新郎,她心底有着说不出的甜蜜。
段腊梅说,那个叫林凤鸣的男人虽然个子不高,可是聪明,英俊,正是她梦里男人的模样。从见面那天起,她就待见(喜欢)他。婚礼简朴而热闹,全村人都来给英雄贺喜,林凤鸣路过天津的时候买回了两斤大白兔奶糖和两条大前门香烟就算招待了客人,没有办酒席,林凤鸣说等他帮朝鲜赶走美国佬回来就把酒席风风光光地补上。
婚后的几天段腊梅徜徉在无限幸福的海洋里。林凤鸣把家里所有的活儿都干了:翻修房子、砌院墙、干农活……她想帮他,他不让,他让她看着,什么都不让她干。他说他有用不完的力气,要替她把一辈子的活儿都干完。
秋日的阳光落在他赤裸的肩膀上,汗珠在布满弹痕、伤疤的脊梁上滚动着,他很健康,浑身充满了力量。她就依靠在自家的门框上,用无限爱怜、柔情似水的眼神看着他,甜蜜的味道从心底深处溢出来,蔓延到全身的每一个地方。段腊梅说,跟这样的男人呆在一起,哪怕只有一天,也不会遗憾。
2
林凤鸣走的时候,段腊梅一直把他送到了东山口的那棵大柿子树底下。深秋的柿子熟透了,满树灯笼般红得耀眼。我的母亲段腊梅从怀里掏出几个鲜红的柿子递给林凤鸣说,这是我给你烘的,甜着呢。林凤鸣接过柿子放在黄挎包里说,我带到朝鲜去,给我那些弟兄们吃。林凤鸣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把牛奶糖塞到段腊梅的手里说,这糖是我偷偷给你留的,婚礼上你一颗都没舍得吃,现在我要看着你吃一颗。林凤鸣扒开糖纸把奶糖放进了她的嘴里,一瞬间,奶糖的味道一下子就甜到了她心底。段腊梅幸福地对林凤鸣说,奶糖确实比柿子的味道好多了。
甜蜜幸福的日子是短暂的,无边的苦难却很漫长。林凤鸣留下的奶糖还剩下六颗,他就死了,尸首埋在几千里外天寒地冻的朝鲜半岛,母亲再也没有见到他。
半个月后,村长带来了林凤鸣的遗物。他没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件破旧的衣服,一件露了棉花的军大衣,一块怀表、一本《康熙字典》和几本翻烂了的英语书。我们家里,除了那张黑白结婚照,林凤鸣几乎没留下任何光影资料。他在朝鲜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无人知晓,后来上中学的时候我读到著名作家魏巍的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联想到那场战斗中的英雄,我才对志愿军有所了解。
能跟钢铁武装到牙齿,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死掐到底,这些人听起来就很了不起。这是我第一次对我的亲生父亲林凤鸣产生敬仰之情,虽然他永远生活在别人讲述的故事里。
林凤鸣永远地走了。他给了段腊梅9天的幸福,给了她一生的回忆。
我的姥爷段国槐和十七岁的舅舅段建梁风风火火地从家里赶来,看到母亲正呆呆地坐在门口痴痴地望着远方。他们的心碎了。姥爷和舅舅要接母亲走,按照道理,刚结婚就死了丈夫,母亲可以离开这个破败贫穷的家,可以离开无尽的苦难,再找一个能够疼她、爱他的男人渡过一生。可她没有,因为母亲怀着我,怀着英雄林凤鸣的孩子。姥爷和舅舅失望地走了。姥爷痛苦地抱着女儿伤心地说,我的傻孩子呀,苦海无边啊,不听话的孩子啊,你就熬着吧,苦海无边啊。望着我姥爷和舅舅抹着眼泪远去的背影,母亲茫然失措。我猜测,那时候她可能犹豫过,因为她有充分的理由把我扼杀在萌芽状态,那样,对她来说或许是个解脱,可是她最终没有选择从苦难中逃离,而是挺起了细长的脖子迎着岁月的磨砺一直朝前走。
年轻的母亲怀揣着对英雄无限的崇敬,咬牙挑起了沉重的家庭负担无惧无畏地朝前走。
我一直认为是那个虚无飘渺的英雄害了十九岁的母亲。
青春年少的段腊梅,面容秀美,身材苗条,在家乡那个偏僻的山乡里,是个百里挑一的美人。可是漂亮的她却苦苦守了十八年的寡没有嫁人,她守护着我,守护着千疮百孔的那个家,守卫着英雄妻子的荣誉,乐观地活着。
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来为她提亲,甚至没有哪个男人敢对她心怀不轨。那个时代,英雄的妻子只能够用心来敬畏,任何一些非分的想法都是对英雄的亵渎。这也或许正是她人生的悲哀所在。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勇敢地站出来替英雄的妻子分担重负,特级战斗英雄遗孀的身份扼杀了一个十九岁青春少女的情爱生活。
因此,我始终认为她是被那个虚无的林凤鸣套上了无形的枷锁,这枷锁在漫长的岁月里牢不可破。我至今仍然弄不明白,是爱情、是虚荣,还是难言之隐?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是什么原因让她坚守在那个虚无的名份上毫不动摇。我至今仍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对英雄的膜拜使他们固执得像块顽固不化的磐石。
林凤鸣牺牲九个多月后,母亲在遍地金黄的谷子地里生下了我。
3
我出生在一个秋日的正午。虽然是秋天,太阳依然火一样炙烤着大地。我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了满眼的金黄,成熟的谷穗低垂着羞涩的面孔迎接着我的到来。
天高地阔,满地谷香。
段腊梅停下了收割谷子的镰刀,躺在高高堆起得的谷垛上。她拼命地呐喊着,哭嚎着,她要把十个多月来所有的悲痛都化作这一刻的呐喊呼唤我的到来。因为羊水早破了,年轻的母亲似乎还不懂得生育是何等的艰难,全凭着一腔勇气在做无畏的挣扎。
村长用谷子垛成了围墙,急匆匆找来接生婆为母亲接生,她咬破了嘴唇,泪水、汗水、血水混杂在一起的滋味让她一辈子都不能忘记。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没有哭。我想,可能是在母亲身体中培育的日子里,在无数个深夜,我听到了太多的哭泣。很多时候,段腊梅是在无声的哭泣中睡着的;很多时候,她也是在哭泣中醒来的。她总能在梦里梦到她的林凤鸣,她说,那些日子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的父亲林凤鸣站在她的床前。林凤鸣对她说,梅啊,你一定养好我的孩子,看好这个家啊。整夜整夜的思念,让我年轻的母亲泪水流干。
我从小就没有眼泪,我在母亲身体里才几天就失去了父亲,所以我的眼睛是在泪水的浸泡中形成的,泪腺十分不发达。面对这个世界,我很少哭。
我睁开眼睛就用冷漠的目光注视着我的世界,黯淡、冷清、破旧、贫穷。
我最初的名字不叫虎,因为是在谷子地里生的,我的小名叫谷子。或许是母亲长期抑郁和悲痛的缘故,我一出生就没有奶吃。林凤鸣留下的六块奶糖很快就被我吮完了,面对饥饿中瞪着一双眼睛的我,年轻的母亲无所适从。她抱着我走村串户地找奶吃。她走在瑟瑟的寒风中,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就是她的希望。每到一户有孩子的人家她就说,我是林凤鸣家的,孩子没奶吃。那些慈祥的母亲们,她们看到我就会放下自己怀里嗷嗷待哺的孩子把我接过去。直到今天,我都对家乡那片淳朴的土地和善良无私的母亲们感激涕零。
饥饿的岁月里,无论她们的乳房是充盈还是干瘪的,她们都会不顾自己孩子的拼命嚎叫,毫不犹豫地把乳头塞进我的嘴里。在她们心里,能给英雄的孩子喂奶那是天经地义无比光荣自豪的事情。我靠着林凤鸣这个英雄的名字,吃遍了十里八村正在哺育孩子的母亲的奶。
直到后来,有个不知姓名的人定期邮寄来了奶粉,有了奶粉,母亲就不用再为我的肚子发愁了。看着我一天天长胖起来,母亲的脸上渐渐开始有了笑容。
母亲说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寄来钱和物,最重要的是奶粉和炼乳,那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金贵得很。但是这些昂贵稀有的牛奶和炼乳我却吃了两年。每个月的三号,从遥远地方寄来的邮包准时会到,有时候还有小孩子穿的衣服,甚至还有一个拨浪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