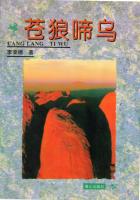消极是我的黎明,我的雪,洛阳,郑州
是我崩溃后剩余的沉默
再一次的平静
消极是我的工作,我恢复的视觉
恐惧的一切,狡猾的一切,新鲜的一切
我不曾忘记的
我已经回想不起来的
读库切
——给张永伟
临睡前,读了库切。他过的日子
就像南非的天空,蓝而瘦峭。枪手
在这个世界上已是目的,库切
眩晕后,讲出了身体着色后的悲哀
我同意他的一些说法,却不认同
他的另一些想法。“自己去猜,向着生长
的黄色,能猜到什么?这里,移除
兴奋源不是什么哑语,不要脸
是因为已没了脸,它是一项标准操作
就是把打死的人抢走,最后
送进亲人不许愿的火焰。”认真
是多么好啊,遥远不是距离,库切
把针孔里的白色当成一个源头,宽松了自己
的较真儿。怎样说,还能怎样说
红旗的裤头儿,就像是
从土里挖出来的,创造了软子石榴
就只能小于呼吸或少于呼吸
在共同的年代,库切或许看到,宇宙真理也回家叠被子去了,不一样的残忍
正追赶这个夏天旅鸟们的叫声
某个时辰,被喇叭花吵醒,只能失去
但不能离去,还能做些什么?这一切
库切告诉了自己,却没说给他人
众多柔软簇拥一个尖锐
——诗人罗羽论
程一身
一
我用这个句子描述羽毛,同时用它描述罗羽的诗。在罗羽这里,我愈发相信名字的塑造力量。罗羽原名罗金羽,但后来他把中间的“金”字去掉了。对此可以有多种解释,比如“金”不(再)是他的取向。我想罗羽的“羽”应该是天然朴素的,而且极有可能是白色的,但不可用“银”字修饰,这都与他的意向不符。也就是说,无论在“羽”前添加什么都会构成一种限制,去掉金银之类的字眼反而显得简洁大气。布罗茨基说:“不能在‘诗歌’这个词前面加上形容词。”罗羽也意识到:不能在“羽”这个词前面加上形容词,于是他舍弃了“金”,这说明罗羽是个信任并偏爱名词的人。改名是罗羽对自我的重命名再定位,是其写作观念在日常行为中的贯彻,其实质是面向自我的一次革命。
罗羽诗歌的命名与此类似。他的诗歌题目多为名词,以及动词,而且偏爱两个字。其中有几首诗都叫《诗篇》。《音乐手册》中收入了五首,分别是《诗篇(七)》《诗篇(九)》《诗篇(十一)》《诗篇(五)》《诗篇(六)》,也可以说是羽毛(七)、羽毛(九)、羽毛(十一)、羽毛(五)、羽毛(六)。由于诗后均未注明日期,难以判断它们产生的先后顺序。不过根据常识,应该是五、六、七、九、十一,而这五首诗在书中却排成了七、九、十一、五、六,并且未集中在一起:七靠前,六靠后,九、十一和五分散在中间。可以说这是一种悖论式排列,而悖谬正是诗人罗羽的强烈存在感。因而这种刻意安排的颠倒分明对应着现实的混乱、断裂,以及缺失。书中看不到《诗篇》八和十,《诗篇》一至四也踪迹全无。或许它们存在着,只是不被诗人看好,因而没有进入公开出版的诗集。我在罗羽博客里发现了《诗篇(二)》《诗篇(十二)》,但仍然没有创作时间,贴出的日期分别是2012年12月11日、2009年4月23日。而《音乐手册》是2010年8月出版的,前者显然与创作时间相距甚远。事实上,我感兴趣的并非这些诗的创作时间,而是它们的名字:《诗篇》,一个极其宽泛的题目,这不等于无题吗?王国维是赞同无题的,按他的意见:“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其理由是“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这当然有道理,但完全废除题目却不可能,也不可取。因为即使题目不能完全反映诗词之意,但它毕竟是一次命名活动,可以体现出所写作品的部分之意,至少能起到区分作用。比如,《无题》是属于李商隐的,而《诗篇》则是属于罗羽的。不过,蓝蓝有一组诗也叫《诗篇》。或许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启示。
在我看来,《诗篇》这个貌似宽泛的命名包含着一种高度自信,因为罗羽把他所写的作品明确称为诗篇,这就像把《庄子》提前称为经典(《南华经》)一样。还有一个值得提醒的文化事实,《圣经》中的诗就叫“诗篇”,其经典性与普及性(尤其是在西方)是不言而喻的。但《圣经》中的诗多为赞美诗,而罗羽这些诗却是写苦难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它们大多和2008年那次地震有关(《诗篇(十一)》除外)。第七首的首句是“毁坏是我们的,她待在液体的时间里”,“毁坏是我们的”,这六个字陡然把灾难和所有在灾难中以及未在灾难中的人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分担的立场与肯定的语气立刻让我想起奥登《战时》第十四首开头的句子:“是的,我们要受难,就在此刻”。面对战争和地震这样的突发性灾难,人们很容易产生否定和逃避的情绪,“我们从来不相信它们会存在/至少不存在我们这里”。而诗人奥登与罗羽的超拔之处在于,他们直面痛苦的真实性,并主动把自身推向灾难的核心:受难的不只是那些身陷战火和地震中的人们,还包括将要陷入战火和地震中的人们。灾难似乎可以把所有人聚拢成一个整体,迫使那些善良的人说出一个共同的名字:“我们”。奥登如此,罗羽也是这样。罗羽的诗中很少出现“我们”,但此刻它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我们”的同义词几乎就是人类。在《诗篇(七)》中,“我们”与“她”构成有待实现而处处受阻的救援关系,被废墟掩埋、随时可能死去的待援者加深了“我们”的焦虑:
半醒着,地面和地下室上浮,所有裂缝
都在吸引我们注意,磁力场
教育香蕉遵守磁力感应
我们的前额碰到阻止悲痛的语言,同一个
星球,有不同的阻止运行
在厄运中,她润滑我们的咆哮
又指导我们瘫痪
我们用固定的手,抓牢我们幻觉的真实
这节诗充满了奇特的对立,反向的摩擦。其关键词是“阻止”。废墟如同灾难的遗骸,将其中的人群视为它的殉葬品,并恶毒地阻止任何救援;救援者此时也无暇哭泣,“阻止悲痛的语言”,只想着破除废墟的“阻止”直接来到待援者身边,让他们摆脱险境。然而,残酷的事实是,废墟的“阻止”占了上风,它让“我们”发出更加痛苦的咆哮,让“我们”的行动如此盲目无力,陷入瘫痪状态。尽管这样,“我们”仍不放弃,而是坚持用固定的手抓牢幻觉的真实。最后这句诗写出了救援者从清醒滑向迷幻的疯狂状态:视幻觉为真实,甚至视废墟为待援者。这就把救援者欲救援而不得的痛苦写到了极致。
在我看来,《诗篇》并非单纯的地震诗,而是把地震隐喻化了,并由此写出了他独特的灾难体验。换句话说,诗人已经把地震这种自然灾害转换为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暴力伤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常生活中那些突发的事件对当事者来说都是一次次震级不同的地震。由此诗人还提出“地震时期”“地震年代”这样的说法,并用于描述相应的历史和现实。于是,经过地震的反复动荡之后,“你的被伤害已是你的语言习惯”。《诗篇(九)》的最后一句“血管抵抗着爆裂”可以视为对被伤害者群体深入体内的精确写照。被伤害无疑会促使血管爆裂,而被伤害者却抵抗着血管的爆裂,以使自己在被伤害中存活下去。这是对当代被伤害者群体存在处境的一种深刻揭示。在《诗篇(五)》中,诗人又把这种日常伤害扩展成民族灾害,并以“她”指代,从而与在地震中那个陷入液体时间中的“她”形成呼应:“民族灾害,让我们与她对应成一个视角/魔法给的措辞,近于律法”。将魔法等同于律法势必释放出暴力,并造成伤害,使死亡“随雨量增多”。一旦面对共同的伤害源,“我们”就会出现。而“她”却是不同的:在地震中,“她”是待援者;在这里“她”却是伤害源。诗人之所以用“她”这个代词,是因为“她”具有孕育的功能,可以完成力量的持续传递。在诗人看来,民族灾害是一种强大而悠远的力量,“她”既是历史也是现实。面对“她”,“我们”难免会产生“被借用”感,而且只能过一种“被她捆住”的生活,并注定成为“被时代用旧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导致“我们”消极的原因,并构成了罗羽诗歌的消极主题。
在《音乐手册》里,《原型诗》《抒情诗》《新约诗,或旧约诗》《补记(政治诗)》,甚至《喝酒诗》都是和《诗篇》相近的题目。如果说后三首接近于题材诗的话,《原型诗》和《抒情诗》明显属于类型诗,因而特别值得讨论。原型诗又叫原始歌谣,是诗的初级形态,往往以二言或三言的形式出现。这是《中国古代诗体通论》里的说法。就此而言,“原型诗”只能是远古诗歌的遗留。而罗羽所写的是另一种“原型诗”,或者说他以此为题其实是对“原型诗”的一次重命名:
计算一下政府机关所消灭的破碎表情,你第一次听到
延缓的引擎的叹息
放下更多的积极,你没有
阻止身体混乱发生
在这里,“原型”无疑是现实生活,它以极其破碎的形式若隐若现于词句间。所引的第一句包含着复杂的现实关系:首先是那些人的表情因何破碎?其次是政府机关为何要消灭它们?最后是计算出来的数目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可以说影响是直接的:“你第一次听到/延缓的引擎的叹息”,如果把“引擎”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装置,它的被延缓就是破碎表情被消灭造成的。而“引擎的叹息”分明是“你”的叹息,这正是使“你”由积极转入消极的原因,但体内持续生成的能量却在造反,反对“你”的消极,身体因此陷入混乱。混乱是罗羽诗歌的关键词之一,而身体混乱则是社会混乱的内化和极端形式,是人主体与身体主体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诗中的“阻止”就是人主体阻止身体主体的混乱,而事实是“你没有阻止”,这里有听任它混乱的意思,这与人主体的消极性是相符的。由此可见,罗羽所写的“原型诗”就是以当代现实生活为原型的诗。从时间的维度来说,“当代”与“原型”存在着张力关系。以“原型诗”为题,也就暗示或沟通了当代现实的远古感或历史感,从而以一种隐蔽的形式揭示当代社会向历史背景的悄然转换,以及当代现实承接历史轨迹的内在逻辑。
至于《抒情诗》,同样是对抒情诗的解构。换句话说,这首《抒情诗》一点也不抒情。上世纪九十年代,抒情诗的意象空洞和赞美倾向遭到普遍质疑,叙事诗盛行一时。《抒情诗》也许是对这种潮流的一个呼应,或者说它以内在的否定颠覆了对抒情诗这个名字的沿用。在诗中,罗羽沿用了郁达夫笔下的畸零人形象,让他游走在时下的消费社会里,呈现在他眼中的到处是阴暗、丑陋、虚伪、荒谬、顽固而凶猛的现实。在“所有反常的事情都有正常的运行”的社会里,“如果不忍受,不乞求,痛苦就没有界限”,这是畸零人领悟到的警句,如同另一种真理。
二
罗羽有意复活《诗经》中的“鸟兽草木”传统,做一位当代的博物诗人。为了具体而准确地描绘羽毛,我搜索了一下百度。这才知道羽毛中间细长而坚硬的部分叫羽茎(或羽轴),和肉体相连的较粗的一端叫羽柄;两边柔软的独立部分叫羽枝,羽枝与羽枝并列在一起称为羽片。“众多柔软簇拥一个尖锐”,这是我模仿罗羽诗歌写的一个句子,写的对象就是羽毛。如前所述,罗羽的诗中很少出现形容词,这里的“柔软”和“尖锐”都是做名词用的,前者指羽片,后者指羽茎。本节谈尖锐。这里之所以用尖锐而不用坚硬,是因为羽茎的特点是细长的坚硬,即尖锐,西方人曾用它制成鹅毛笔;更重要的是,罗羽的诗歌也很尖锐,他的尖锐来自现实感,就像羽茎的尖锐来自鸟的肉身。
现实感是进入诗人心中的现实,以及诗人对它的具体感应。谈现实感,首先要讨论现实。罗羽诗中的现实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河南,一个是祖国。如果说河南是一个本地现实,那么祖国就是一个河南为中心的广大现实,但它们都是整体的现实。当然,河南属于祖国,但祖国并不能取消河南,因为河南不仅是诗人的故乡,更是祖国的故乡。在河南这片古老而富于生机的土地上,交织着辉煌的文明与沉重的苦难,重叠着祖国的漫长历史与驳杂现实。所以,对于诗人罗羽来说,河南既是祖国的核心,也是祖国的缩影。关于河南,罗羽写了元结和徐玉诺这样的先辈诗人,也写了平顶山矿区和米围孜这样的乡土风物。值得注意的是一首诗的题目《背对河南》。尽管河南是罗羽关注的重心,也是他书写的中心,但他其实是河南诗人中的边缘人,因为他坚持作为一个诗人的独立性,“不与刊物打交道”(《一首旧诗》);同时,罗羽的国际视野与先锋写作也是他背对河南和引领河南的体现。罗羽书写河南现实的诗篇可以《年代》和《在石漫滩》为代表。
当泛黄阵营用波涛
设下包围圈
逃难的苇叶多起来,水面
聚集燃烧物
雀舌豆,使母坝消失于平静
子坝的混乱,已没有年代
接生婆对着河的窄处喊
怀孕的鱼游动
嘴颤抖得像个喇叭口
身体的白光
引走
一直想过河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