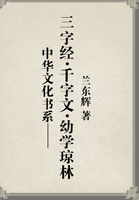罗 羽
1962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河南许昌人。1991年在平顶山与森子、海因等人创办同仁民刊《阵地》,同年中断写作,2002年重又恢复。著有诗集《音乐手册》。有作品入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现居郑州。
罗羽诗选(13首)
旧世界
是这样,欢迎你来到一个旧世界。这里
铁轨闪烁刺眼的明亮,雨中的列车驶过林荫广场
行脚僧也曾在车站的转弯处跺脚
下腭来回错动,在左右不对称的时代吃藕节发出骨节的摩擦
我们总会把衣服反穿一次,这样做,穿衣镜
也认同。你还老看我的旧衣服
此时,这外在的外在正收集着小雪
世界观不应充任宛转的帮凶,想另一个人有什么用?我们才是同一个人
无名指超过食指的人,身上
有柳枝气息。化妆师摩挲你头发的家乡
变化了窗内的声线,而你把我
交给你腰窝的修辞,我怎么去处理欲望中的争吵
我们把互换的俘获物,都抛给最坏的天气
不要太多的幸运,你给我些手指外的剩余就够了
我并不比一些河南人愚蠢,只是他们
更加奴才,我把贺拉斯
抬高到今天,但他们却睁着眼睛也看不见
哭泣的日子,霾是我们肺里的工业鸣唱
在彩虹的法庭,一定要控诉它的亲戚。迂回的虚无
已变为上下移动的暴虐
我不冷静时,就盼革命到来
这我同意啊,不用关灯也能睡觉
或像阿赫玛托娃那样梦游,在被窝坐到天明
还能让我忍住什么,不能忍受什么
霾的国度已像风一样静止
谁也不知道,哪些人会成为现场,正义的力量
情愿不情愿,我都相信你的判别
你开始以盛妆的形式卸下重负,而我在
动怒的语言中,还要栽上几株沉降的果树
诗是什么
我亲爱的拉金,我知道
死亡不会漏掉任何一个人
——米沃什
先是摸你的肋骨,摸那上面
饱受折磨的城市。这个时代,坏人
都忙得像跳来跳去的蟾蜍(拆房、到领事馆喝咖啡
转移财产、开会)。当暮色抱紧太阳和云
青春病发作,去伤害那些亲吻,玩笑里的风景
从你的住处到这里的电梯,有一片
荨麻地的升降。窗外,有人用弹弓射鸟
偷窥的人对着呻吟的回声窥视
这时,摸你的脚,几乎是在喝酒。眩晕后
又想起,莳萝在摇摆中粉碎,获胜的宇宙
生产了你要的避孕药,死亡
不会漏掉害上狂想症的人,处女
弓着脚在飞,找雪地里的诗人睡觉,做他
合法的妻子。“在你的膝盖上,我从来
就没有伸出过脚踝。你所有的歉意都是对的
但要是拒绝新钟表的围绕,我不说话
你就不欠奏鸣曲什么。骑上
你的腰,还能去哪里”
吮吸着你的冰凉,做个避让者
在灯光里活着,而诗也有这样的工作
握着你的脚,像是抚摸到了好诗
诗是什么?是这脚上蓝色血管和脚后跟的颜色
是你踩我时的坚实和轻盈
从此,我更有理由蔑视那些土鳖诗,那样的粗鄙物
土的不是词语,而是韵律后面的思想
脸红的时候,我找到摸你脚
最好的方法。性爱的哲学似乎不是持久
它只是身体最后的肯定。短时的永恒让你知道
一双脚不是器官,它是气息和灵魂的肉体
听不到你脚镯的响动。脚越摸越小
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色情的广阔
昏 暗
——给泉声
露山向昏暗处移去,南水北调总干渠吹过来风
寒霜落到树叶的每一条叶脉,棕熊
爬上梓树。在蓖麻小巷酒馆里,喝着
忐忑酒,我回想自己的半生
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险峻那样?这些年
带着那人的脸,穿过耳朵形的炊烟,被车辆载着
头发贴在车厢壁上,而周围像小神一样安静。算一算
和梅宛陵相比较,活在专制下,雪和恍惚里,我比他
得到了更多的酒。他的酒里有水、绿色蚂蚁
但没有清酒、白兰地的羞耻;他没有喝过
海洋里的舰船、房子后面的屠杀
也没喝过饥饿、民主、蕾丝花边、过膝短裙的忧愁
从睡眠中逃走,这是引逗了林鹬的一天
丐帮的雾霾,蔓延到拆迁的地界,流淌的血停留在
一些事情里,县长、书记,有与没有的预谋,吃了肉桂的信仰
“我会想你的,看来罪行还没有逃远
受苦者的疼痛多过了抽屉”。不要
拿走已低下去的身体,干瘦而凌空
的不会是衣裳,只能是骨架
这个冬天,越来越冷了,把驴都冻跑了
“过来,不要害怕”,哪里消失了
彩虹?哪里是清晨?哪里去钻玉米田的隧道
肩膀、脖子沾满黄蜂们的泥巴
赶赴酒场的人迷路了,端来
羊眼、小白菜、乌梅汤,这里就是终点
在旋转中
“在旋转中,在青虫发声体的干扰下
我把头靠近你的耳朵,不再说话”
“欧洲女人?在自我的殖民地,她们
不是情欲的对象,只是语言的奶酪”
“你是我的相似性。耻骨在叛变中,被风吹动
戳破图形,谁能领你进乌桕的水世界”
“这不是打量,不是拆散,也不是白菜的白
给我一把铲子吧,让我帮你铲雪”
“不用去猜测,我们的诗里一直都有他人
的生活,你跟着我到哀悼日,应带上花环”
“会过去的,以前我什么都不知道
同一种东西的两种叫法,毁掉了灰背隼的嗓子”
“那丝袜带天使不可以是你的样子吗?有些事
不该发生,要怪只好怪酒味太醇了”
“这并不复杂,你只要晕倒一阵子,并为
清醒干杯,远在新疆田野里的棉花就会开在你身上”
“是变戏法吗?虽然音乐你喜欢海顿
但奏鸣曲的色彩,如何跨过海洋的湿润”
“什么才是不确定,什么才是好角色?奏乐人
的袖子上,洒下什么样的灯光才能照见你”
“想想我们谈论过的,白云山的核桃
曾是哑产品,托住它的叶子撕裂才散发香味”
“有空儿就动手做一个你的肉身,这一个
动荡的、低语的,可长久地放在怀里”
“就喜欢这样的,膝盖被床硌破了
旧日的明信片在河流转弯处追上了道路”
“把手插进你的衣兜,引来杉树枝的空气
前面的隧道投来暗影,而灌木丛中的雉鸡翎一闪而过”
遗 忘
喊醒他吧。他被那些面汤、水果
耽误了太多时间
再一次叫醒他吧,在舞者的哭泣中
你是唯一舞者,在树林空地,与他
有顺从的不对等。你想去的地方,只有纸灯笼还在
那些鸟的口涎都包给了饭店。香槟酒,香槟酒
吵闹后,他把牙刷递给你
他居然很无耻地还有性欲,他把热爱现实的情感
转移到你身上
把旧社会放在一边,在打烊的小酒馆门前走过
临睡前喝一碗水,翻完小半本的雪莱
对格调他从来就有自己的想法,这是该做的事情
腾出手,为你拌一盘凉菜,用忠实
养活饥饿与无助者。下雪时
也养活一块白磁铁里的鱼
只能生活在此处,原谅别人的妻子,节省
做梦时的呼吸,用平淡的口气说出那杀人的冤情
他把这里的惯例,看成扬起脖子的公鸡母鸡
凉棚里住不下熊耳河,望上去
凌霄花的秘密更像搜索引擎
过多滋味的享用者,多么愿意把自我拌进滋味
腰以上的凌厉,是你尝过的最新鲜的菠萝
“我从来都是走这边”,这是他找到的好处
有害的、不可靠的、短时的名声,让他低下头来
他只把酒香赋予你
一些时候,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是诗的器官
还是诗过早地长在了身上。在你面前,他到底是说了些话
还是什么都没讲,或者只是诗吐出音节
也只有遗忘才记得清
诗 篇(十九)
从弹簧门出来,到特吕弗那里,凉水下
沉默着激进的人。哪里的河流,有传奇剧
的灾难?一排细浪推动的细节,总有
一些必须挽救的焦虑。凹陷的脸颊,平庸生活
中的来客,如悲伤一样,把我们吓坏了
很多的小聪明,让日子老了好几个月
僵尸舞在黑夜的广场扔下形式的棺木
与杂货铺的轻松交谈,我们为旧居的变形鞠躬
“空姐的双腿在飞机上脱臼”,这已不是原来的意义,面临着相反的处境,缺席者
的乡愁,移进世界的矮小。烧饼歌种植着危房最后的树木,灯盏在月亮上凿洞,嘟哝一阵后
走向专制者形容的天空。一点儿都没错
“海是蓝的,天是白的,自溺者
的衬衣是红的”。我们在河南碰杯,鹰嘴豆的脆弱
也可以是下酒菜,词语转向打击谣言,白发老人
的嫖娼,兴奋于眼睛的愉悦。真的是好笑
尿路感染像水龙头,平民的正确习惯,就是使死
的变成活的。虎皮兰吸着我们的性和骨髓
太可惜了,我们还都是贫民,立场简单得像人类
的院子。我们颤抖,身体发烧,双膝在谋杀案里
给布景一个平行的水手,而批评谈到
的几宗罪造成新的失语。或者我们说透了
或者什么也没说,识破太平洋,只需要盐的嘲弄和憎恨
给糖的一首诗
快要饿的时候,她就吃你
皮肤上的灯光。刚下过雨,加油站
带着苏打气味,逃进桑林
在这里,那些发亮的地方,聚集着毛发。炭火爱着印度外的郑州,被词语搬进屋里
那么多的烤羊排,摆到了床上
盐和孜然像黑丝绒那样
顺从着跌倒。你的手臂挽起她的叫声
(听说很远的那边有了暴动的小猫,在车厢里
喝酒,起伏着柔软
舞会面具,比手掌还要炽热。从脸到她们的腋窝
语言的形象被剃刀刮净
紧身衣的演唱,一直传到升入天空的监牢)
黑夜也过去了。醒来,桌上还剩着早晨润滑的软膏
搂紧她,咬烂的舌尖儿等着头上星体的开裂
“隐形的小斧子更像饿坏精神的知更鸟
从身体挖出的蛋白石却不能让你用一支长笛冶炼
我的额骨更适宜栽种,盖上草叶
长出来的独角兽可以逼退砸你车吓哭你女儿的暴徒”
一代人的恐惧,反抗,瞬间幻化成糖的魔法术
四月七日,去开封见占春、开愚、恪,饮酒,谈论消极性
稠叶李是飞鱼,而一片水的前面
是我们的住宿。稍晚一些时候,云
遮住掂橡胶棍的巡夜人。我没有看见
他们扑打偷自行车的蝙蝠
只是知道,郑州地理少了几只链盒
我们都理解,烧酒是一条河流下游的湖泊
虚弱可以滑到岸边,我们却不能
它的个人性,包含了某个区域
今后不一样的碎片。一阵嘶嘶声
让亲人接受我们与高鼻梁女人的性习惯
当集会不再出现激烈的光线
我们到酒厂捉泥鳅
天阴了,小老鼠蹲到猎枪扳机上
它不射击沙尘大颗粒的沉降,他妈的
不是下雨了,半空以团体的形状下土了
怎样才能确认,睫毛膏来到我们四肢干燥的地方
铁路系统清理非选民的嗓音
我和朋友登上车,帮助引擎向东开
腐败急速地颠簸车厢
闪过的麦子和火车一块绿起来
随着蚜虫紧张地给春天关门
我们应该坐在哪里
现在,我们更明白为什么会害怕
成为一种抑制,比变成另外一些人要容易些
困难的轮廓,正是它被冤枉的部分
扯动安静,嚼烂上一年的苹果
我们是受苹果花安慰的阴影
找一些不同的东西,我过去犯的错误
已积累成一次崩溃。刮胡刀
泛起泡沫,我的下巴
有了有害的幻觉,患上哮喘病
交通不是时代,我们也不是消极的枯竭
诗 篇(二十)——给铁哥
省图书馆的院子里撒满了文件,地鸫
从粮票的束缚中解脱,向追悔迁徙
这在哪个年代已不重要,室内童子尿的香气
被妄想熄灭,二花狗叼着它的嘴,跑向
劳役的灰暗。受伤后,我们住在柿子里
醒过来,却看不见柿树和果园
用以国家安眠的并不是药物,而是
眼眶里的平原,公诉人那里的生活用品
罩上一层灰土,剪刀进行曲在喇叭
的铁质中震颤,起诉书打了流亡者的脸
哭泣,成为广阔里的唯一动静。面对
被大海掀空的椅子,我们想回到
土壤的世界。有人佯装眼前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城管杀死做热糖梨的小贩
邮差闭上眼睛,记住了她掉下的袖子
彗星会在清白的时间敲打库房里的豆粕
洗手间,暗影里的墙壁,记录旁观者的肮脏
在我们收到的礼物中,除了一些害怕,还有缺憾
的变叶木。有电没电的灯泡,都不能蛊惑
动乱,菜园子的晦涩,只有吃生蚝的人在离去的时候
才会最终明白,——为了许诺及向自制面具的妥协
玩 水
仰望,就是抬头看天。雾霾后,这里
下着一场小雪,牵着手,请跟上我的消极
专制者黑到了深夜,我只有
把怯懦送给河流的鱼群
“原来你也在,说出来吧,我在仿写辛波斯卡
比如,和你的睡眠是种需要,但却不能
你正坐在去东南亚的机舱里,像是焦急飞行着人生
嘿,多么及时,就在这一刻
我又看到莎伦在摸索前婚的喜酒”
和父亲是生人,也是熟人,而他
对时代的躲闪,像一次杀猪场的教育
日常的日常性,湿透女儿的玩水
露宿者的灵魂也是雪
喜鹊的胸腔装下世界最小的床
再过些时,你就要乘坐地铁
向上,一层层的泥土松软着高架桥
桥下,发生罪恶的地方围上铁栅栏,摆满绿色植物
邮政车驶过,朝两边推开悦耳的丧失
只有雪,为你的脸颊留下了声音
对 话(三)
“你要不是单身,早就被捕了”
“在纪念日,不要谈论间谍养鸟问题”
“这是炉火燃烧的时刻,只有打铁
才能解救锄头,或一辆机车的构件
当室内的锻炼甜蜜了肢体,亚洲病和羞耻
就会被演奏着的单簧管带走”
“你在追赶一只兔子,公共生活
的信赖,正在解体,水银灯成为野燕麦
兔女郎的田野感性掉进红酒”
“什么都没有了吗?不,这要看
某一天的下午,你会不会被邀请到一首诗里
憔悴,十年的消失,都算不了什么
一件事情发生有它的偶发因素
最近,受反嘴鹬的引导,祈雨师中
的小师,要到瑞典跳舞
因为思想不来自于诗,又没有
否定奴役的勇气,他的燕尾服
只能是低飞的燕子”
“虚构的雪就要落下,北方与你
没有距离。记住那些遗忘,水分子
的时间,谢谢你对监牢世界
的想象,谢谢活着与死去
前面,跳动的是一座城市寒流到来时
的旧事,它们让你劝说挨饿受冻
的人,不要为当代痛哭
要有耐力,等着白额雁最后的空气”
沿淮一带
消极是我的泡桐,我的亲人
在河南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不会
破坏我说出的话
从驻马店到息县,消极是冬天
一座座新坟
是艾滋病围住的麦田,水塘
沿淮一带,消极是低飞的白鹭
平原边的石头山
它有脸一样的豁口,往来的不是
法兰西妇女
是被拖出水的娃娃鱼运黄沙的卡车
(如果来不及消极,会有什么样的平房
居住?伤心的县城,餐具,性爱,谁折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