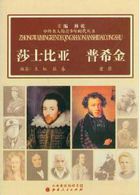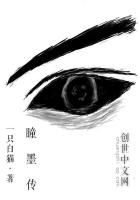此奏章也是一篇万字文。在奏章中,文天祥指出:皇上下了“罪己诏”,虽对弊政有所悔悟,但因未知病根而并没有掌握治理的良方。病根在哪里?就在于奸人当国,排挤能言直士,致陛下言路全被堵断。近几年中外怨叛,蒙军入侵,国家受害,追究其失,都是陛下的亲宠造成的。此人窃弄威权,累及圣德,凶焰威恶,蠹国害民,使陛下失民失土,贻宗社不测之忧,罪恶极大。若不是此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则奸佞丁大全就不能窃取相位,上下官衙就不会相互勾结搜空民财,正直的士大夫就不会被陷害加罪,民心必无变,宗社必无危,则朝廷清一,言路光明。
那么此邪恶之人何以如此嚣张呢?以至陛下何以不知民间疾苦,不知人心叛离,不知蒙军入侵的实情呢?文天祥指出:那都是因为他倚仗陛下的恩宠,一手遮天,蒙蔽天听,把陛下置于幽昧之中,“故颠倒宇宙,浊乱世界,而得已无忌惮,使陛下今日讼过于天地,负愧于祖宗,结怨于人民,受侮于夷狄”。
至当今国势艰危,人心不安,文天祥披肝沥胆地疾呼:“陛下为中国王,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指出,凭着三江五湖不利于蒙古铁骑的险要地势,凭着六军百将接连挫敌斗志高涨的雄风,若“陛下卧薪以励其勤,斫案以奋其勇,天意悔祸,人心敌忾,寇逆死且在旦夕!”但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想阻碍陛下抗敌意志,误导陛下迁都,如让其得逞,则“六师一动,变生无方,臣恐京畿为血为肉者,今已不可胜计矣!”
“小人误国之心,可胜诛哉?臣愚以为今日之事急矣!”小人是谁?奸邪是谁?写到此,文天祥再也遏制不住满腔的激愤,直点其名击之:
不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实,则中书之政必有所挠而不得行,贤者之车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异议,何从而消?敌人之心胆,何从而破?将士忠义之气,何自激昂?军民感泣之泪,何自奋发?祸难之来,未有卒平之日也!
文天祥力劝理宗为保国大计而割私爱,勉从公议,对董宋臣明正典刑,传首以告三军。说如此将天下震动,人心喜悦,将士思奋,虏寇骇退。文天祥引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话作为理论依据:“社稷安危之权,国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内之阴邪,常执其机牙。”据此反复强调处斩董宋臣的必要性。
如今天下之大弊,是言路不通,若除掉董宋臣,言路大开,其他事情就可为了。于此,文天祥为抗蒙的当务之急提出四点主张:
一是“简立法以立事”。文天祥认为:当前烽烟四起,国难当头,朝中议事必须摒弃等级森严的繁文缛节,实行“马上治”的战时体制。为此,他建议:其一,“莫若稍复古初,脱去边幅,于禁中择一去处,聚两府大臣,日与议军国大事”;其二,“宜仿唐谏官随宰相入阁故事,令给舍台谏从两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议”;其三,“移尚书省六房隶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札,兵部得禀枢密调遣之命而发符移。其他事权,一仿诸此”。如此一可提高效率,二可集思广益。
二是“仿方镇以建守”。他认为今日地方抗敌力弱,在于宋初为防止唐末五代方镇割据擅权之祸,把兵权和财权全部收归中央所致。“今日之事,惟有略仿方镇遗规,分地立守,为可以纾祸。”他举江南西路军力布局为例,指出蒙军已攻入湖南腹心地区,江西诸州不能不改变现状,否则将被弃实击虚,逐县攻破。为此他建议:可在吉州、袁州(江西宜春)建立方镇,各辖几个州,选用知兵而有名望的人统领,许以财政和统兵之权,气势便可大增。江东和广东各地也可仿此而行。如能实现,旬月之间,天下必“雷动云合,响应影从,驱寇出境外,虽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忧哉”。
三是“就团结以抽兵”。若按现行方法征兵,“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徒有增兵之名,而无拒寇之实。文天祥建言:若以方镇统一征兵,每二十家抽一兵,每州以二十万户计算,就可得一万精兵,一镇有两三个州,就有兵两三万。东南各路都建立方镇,就能增兵十多万,州郡现存的粮食和财力也能保障供给。“为帅者,教习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锐。山川其便捷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其之相为命也,锋镝之交,貌相识而声相应也。如此兵者,一镇得二三万人,当凛凛然不下一敌国。”
四是“破资格以用人”。朝廷用人专重资格,而且“荐引之法,浸弊于私”,使“有才者以无资而不得迁,不肖者常以不碍资格法而至于大用”。为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办法是:“明诏有司,俾稍解绳墨,以进英豪于资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轻授以官,俟其有功,则渐加其官,而无易其位。”真正的人才破格以用,凡义甲和壮丁中的豪武特达之士,都可以选拔为将帅,甚至是“山岩之氓,市井之靡,刑余之流,盗贼之属”,但有一技之长,均可选来替国效力,并在实践中根据其功绩提高待遇。
这又是一篇近万言书,洋洋洒洒,雄健透辟,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搏动着泣血忧国的赤诚之心。
文天祥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为了能引起理宗重视,或奢望能让理宗有所采纳,也为了抑制董宋臣的报复,在呈上万言书后,即登门拜访了左丞相吴潜,力争求得他的支持。
文天祥对吴潜说,自己奉诏上书,冒死进言,是为了铲除朝政腐败的病根,若病根不除,国家真的是没有希望了。他知道自闯红线,自惹祸端,可能会招致的后果,说,今日之事急矣,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会大祸临头,死于非命,但若能开朝政清明,虽九死而无悔。他恳求吴潜能秉持公道之心,给自己以大力支持。
让文天祥颇感失望的是,与往常不同,他讲了一大通,吴潜只是用同情和理解的眼光看着自己,苦笑,点头,或摇头,却始终沉默不语。
他哪里知道,此时吴潜心头正笼罩着重重的乌云。此前,他也曾像董宋臣一样力倡迁都,并因此遭到了皇上的猜忌。
呈上万言书后,文天祥就忧心忡忡地等待着理宗的裁决。
其结果是,理宗皇帝既没有采纳董宋臣的倡议迁都,也没有如文天祥所愿处斩董宋臣。
没有同意迁都,也并非是采纳文天祥的意见。相反,文天祥的主张,反倒被一些朝臣指斥为迂阔之论。如他们说,宋太祖当初为防止藩镇割据重演,把兵权和财权收归中央,这种情况到南宋已得到改变,自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解除韩世忠、张俊和岳飞的兵权后,各地屯驻大军的兵权已握在各都统制手中,加上当地安抚使和制置使手中的兵权,地方军力规模已大为扩张。但他们仍没有正视南宋恪守以文制武的原则,从骨子里仍然对将帅严加防范,导致兵权掣肘,战斗力薄弱仍然是事实。
理宗之所以没有同意迁都,一是谢皇后也同意何子举、朱貔孙等诸大臣的劝谏,认为一旦迁都,将丧失军心民心,四方民乱蜂起,家国不保。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对左丞相吴潜的猜忌。
当理宗就蒙军进围鄂州问计于吴潜时,吴潜考虑到理宗的安全,回答说只有迁都暂避。理宗又问:那你怎么办?吴潜慷慨激昂地说:臣当死守临安御敌!岂料理宗为之一震,当即掉着眼泪诘问:难道卿家想做张邦昌吗?听得此话,吴潜顿感挨了一闷棍。张邦昌是何人?张邦昌是北宋靖康年间的少宰,汴京陷落时降金,被册封为伪楚帝,其名声比秦桧更臭,在南宋是人人唾骂的汉奸。理宗说他想做张邦昌,表明对他的高度不信任,更是对他的极大侮辱。
理宗如此疑心吴潜,是因为理宗无子,想立胞弟之子忠王赵禥为太子,吴潜不同意,密奏道:“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这句话深深刺痛了理宗借助史弥远篡夺皇位的心结,使他十分恼怒。丁大全的余党便趁机造谣说,吴潜不同意立忠王为太子,是企图为济王立嗣,然后立济王嗣子为太子。又因吴潜之弟吴渊为政严苛,有“蜈蚣”之号,便编造童谣四处散布,什么“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这些话自然要传到理宗耳朵里。朝中质疑自己宗位的潜流一直没有停息,有人图谋篡位不是没有可能。想起吴潜八年前第一次任相时就与自己有隙,干了一年便被罢免,便心生再次将他罢免的念头。
理宗的冷酷无情令人心寒,吴潜再也无语。文天祥上门求援时他也只能苦笑。
至于董宋臣,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理宗皇帝是片刻也离不开的,朝中议论纷纷都不济事,岂能因你文天祥的一个奏章就能舍弃的?
文天祥冒死直谏,以期“万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则臣与国家同享其休荣”,同时又说自己“干犯天诛,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诛,则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将不免”。就是说他并不幼稚,希望只在“万一”,罹祸却在“一万”,他是“事宁无成,而不敢隐忍以讳言;言宁不用,而不能观望以全身;身宁终废,而不欲玩愒以充位”,所以上奏后,就以“有仓促等死之虑,无毫发近名之心”,等待着生死裁决。
但他既没有等来“万一”,也没有等来“一万”。理宗也并没有惩罚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前有宋祖宗不杀上谏士大夫的祖法,后有自己下“罪己诏”要求臣下上书直言。还有一个原因,即“理宗无君人之才,而犹有君人之度”,有的时候,理宗也容得下批评,哪怕是言辞激烈的批评。
至于董宋臣,他从此对文天祥恨之入骨,必欲置文天祥于死地才解气,没有立即下手,实是要等待一个时机。
上奏没有结果,甚至连打击报复的反响都没有,让文天祥极度失望。什么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什么“第名前列者不十年而至公辅”,在如此昏聩的皇帝眼皮底下还能做什么事,在如此黑暗的官场上还能有什么前途?罢了,罢了!不如回家乡读圣贤书去。
就在文天祥弃官离开临安的当口,闰十一月,忽从前线传来鄂州解围的捷报。
这可是冰天雪地里的一声春雷,朝野顿时一片欢腾。理宗更是兴奋异常,即下诏改下一年为景定元年。
可悲南宋!殊不知鄂州解围一事中埋藏着贾似道编造的一个大骗局,这个骗局将成为蒙军手中一个加速南宋走向灭亡的重磅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