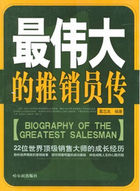《燕台诗》是这段时间里李商隐最有代表性的诗作。在《燕台诗》的总名之下,包含了《春》《夏》《秋》《冬》四篇。此外性质相同的重要诗篇尚有《河内诗》(含《楼上》《湖中》两首)和《河阳诗》等。
这些诗均为七言歌行体,且从用词造语到音律节奏,均具鲜明的李贺风格。
就其内容来看,它们都是讴歌爱情的,既有追求的热切和相恋的激动,也有离别的痛楚,思念的焦虑,更有对于见面团聚和永不分离的强烈渴盼和奇思妙想。读解这些诗,需要破除阅读中国古诗的一种思维习惯,即不要把作品主人公与作者本人等同,不要认为诗中所写都是作者本人经历的真事,而要把它们理解为是诗人对爱情生活的幻想;诗中的男女主人公当然并不是诗人和他的女友;诗所描述的空间和时间都是诗人假定的,因而是虚设的,缥缈无定的,甚至是上天入地,打通了人神界隔,突破了日常生活逻辑的。不过,诗人所写虽不是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但却贡献了喷薄如火的恋爱激情和刻骨铭心的恋爱体会。
几乎所有的李商隐研究者都认为《燕台诗》和它的姊妹篇非常难解。困难的症结就在于我们往往不自觉地陷在读中国古诗的那种思维定式之中。即往往把抒情诗的内容仅仅看作作者的自述,把诗之主人公与作者本人画等号,而诗中所写之事也就必然是其本人之事迹,所抒发的也必为其本人之情感——除却那些明白标出“代”字的作品以外。
许多研究者进而把诗歌当作考据作者生平的依据,抓住诗中涉及的时、地、人、景、物等因素作为确定诗人行踪的坐标。这样做实属无可奈何,有时也能收到一些成效,久之便形成一种读诗解诗的传统。然而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诗歌虽不是小说戏剧,但诗歌也绝不是行踪实录。诗人完全有可能在诗中假托人物、虚构情境乃至编造故事,只是其表现方式不像小说戏剧那样采用作者隐身的叙述或表演之法,而是借了那故事的一点躯壳来抒发感情。故事唯见模糊框架,诗人的兴趣和用力点其实是在抒情。
对于这样的作品——如《燕台》等篇就是如此——按传统方法去解读,用诗人生平去印证,往往左右窒碍,把自己弄得一头雾水。然而如能不被这阅读传统所囿,而把《燕台》等诗中所写的爱情故事看作是李商隐编织来借以抒情的,把这些诗看作相对独立的爱情叙写,而不是硬去牵合诗人生活的事实,那我们的心态倒会比较放松,也许倒有助于我们对这些诗篇的理解和欣赏,也有助于对李商隐心灵世界的了解。
确立了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用放松的、自由的心态来读《燕台诗》。让我们从《春》诗读起: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
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
暖霭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
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
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
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宽迷处所。
衣带无情有宽窄,春烟自碧秋霜白。
研丹擘石天不知,愿得天牢锁冤魄。
夹罗委箧单绡起,香肌冷衬琤琤佩。
今日东风自不胜,化作幽光入西海。
如果一定要把这首诗与李商隐的生活具体挂钩,从中发现他的恋爱事迹,那是会劳而无功的。但若把它看成李商隐编织了一则故事,犹如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似的用来表达一个男子(坠入情网的男子,不是李商隐却可包括李商隐)对爱情的苦苦寻求和因爱而受的心灵折磨,那么这首诗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男子灵魂出窍,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蜜蜂(蜜房羽客;羽客兼喻道士),在春日的街陌上营营地飞,为找到他想念的娇魂,几乎寻遍了所有的花丛和枝叶。突然,在春阳暖照之下,他发现远远的桃树下站着一个梳着高鬟的美丽姑娘,仔细看去,那不正是渴念中的她吗?他是多么惊喜,多么想飞上前去倾诉情意!可是办不到,蜜蜂和人,就像雄龙和雌凤似的,无法沟通。可爱的姑娘哪里知道在她身边营营飞舞、依依不肯离去的,正是她在等待的情人!这种与所爱女子“同时不同类”因而难以沟通的感觉,深深地刺激着商隐,是他一个永难忘却的记忆,后来在《柳枝诗》中曾再一次写到。身为蜜蜂的男主人公怎能不因此心烦意乱!他急得醒了过来,已是黄昏,却是酒后做梦,梦中呓语仿佛仍响在耳旁。
以上是从开头到“映帘梦断闻残语”的大意。我们看到,作者的诗思很大胆,很奇巧,很跳跃,很魔幻,而传达的恋爱感受很强烈。
上面一大段诗意的叙述是贯注着强烈感情的,以下更紧紧围绕着相思之苦而直接抒情。
他想念情人,想用铁网捞珊瑚那样的办法去得到她,但“海阔天宽迷处所”,他根本找不到她。他瘦下来了。衣带无情,越来越宽;光阴无情,默默流逝,春烟自碧,秋霜自白。他每天研丹剖石,精诚不变,可是老天浑然不知。
他痛苦地叫喊:老天你把我这个被爱折磨的冤魂关到天牢去吧!老天依然不理睬,毫无怜悯之心。春天即将过去,夹衣入箧,改穿单衣。东风虽然温暖,但他却不胜悲凉,竟“化作幽光入西海”去了。
晚唐与李商隐齐名的诗人杜牧曾为《李贺歌诗集》作序,充分肯定了李贺的诗艺:“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又说:“世皆曰:使贺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李贺诗风继承屈原《离骚》,但奇特跳跃得太厉害,如能在理路(逻辑)上稍加注意,简直可以超越《离骚》。拿这话用来批评李商隐的《燕台·春》诗,不是也挺合适吗——就想象之大胆不羁、诗思之天马行空、诗中人物之变幻、场景的自由挪移、语言之瑰丽多彩、句式之跳宕多变、韵律之顿挫劲拗诸特点来看,商隐的确是在有意模仿李贺和屈骚。
爱得死去活来,表达呼天抢地,是这一时期李商隐诗歌创作的鲜明特色,也是他的真实心态。这一切像极了鬼才李贺,却还没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也许应该说,这时的李商隐还是一个极富才气的诗歌学徒,正朝着一个成熟诗人的方向奋进。
现在我们来看《燕台·夏》诗:
前阁雨帘愁不卷,后堂芳树阴阴见。
石城景物类黄泉,夜半行郎空柘弹。
绫扇唤风阊阖天,轻帷翠幕波洄旋。
蜀魂寂寞有伴未?几夜瘴花开木棉。
桂宫流影光难取,嫣熏兰破轻轻语。
直教银汉堕怀中,未遣星妃镇来去。
浊水清波何异源,济河水清黄河浑。
安得薄雾起缃裙,手接云 呼太君!
如果说《春》的主人公是男性,主题是他的寻觅和思念,那么这首《夏》诗的主人公则是女性,当然是男性作者李商隐笔下之女性,其主题则是女子的盼望和等待。
前阁、后堂、石城、轻帷翠幕,是她的所居。“类黄泉”、“空柘弹”是她独居无伴的感觉。“蜀魂”二句是她对他的慰问和悬想,同时也就表达了自己的孤独和对他的思念。“直教”二句是她的心愿,并由己而及于境遇相似的他人。“浊水”二句可理解为她感到与他现实处境颇为悬殊,不免忧虑,实为“同时不同类”之意的另一种说法。而末二句则是她的愿望,她向仙女呼吁并求助,当然结果只能是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