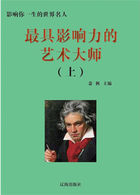江问:“放什么东西?”
答:“按马校长的标准,给您再配些家具。”
江严厉地望了宋一眼:“谁要的?”
校办负责人急忙解围说:“啊,是校办研究决定的。”
江摆手说:“不要,这就足够了。”
“已经通知总务处了。”
“再通知总务处,就说我说的,家具不要,让他们只办一件事,要快一些,把电话装好,是归总务处管吗?”
校办负责人诺诺着出门了。
住进中国的最高学府,乔迁新居的第一个晚上,夫妻俩竟因家具一事弄得怏怏不快,临上床的时候,江问宋:“是不是你去办公室要的?”宋说:“要了又怎么样?难道不对?莫忘了从今天起,你要领导的是堂堂北大,出出进进都是些有学识有地位的人,再艰苦朴素也不能有失身份,北大又不是延安。”
“你呀,你呀,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些呢?”
之后是长久的沉默。夫妻俩并排躺在双人木板床上,仰望着古香古色的天花板,吮吸着充满书香味儿的清新空气,各自在想着自己的心思,谁也不说话。
这是一对互敬互爱的革命伴侣。他曾是她的老师、领导、同事进而结为夫妻。她也习惯了他的严厉和严格,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从不掺和他的工作,只过问衣食起居的习惯。也不是没有磕绊,但他们化解矛盾的独特方式是长久的沉默。沉默解恩怨。沉默增感情。她知道,沉默之后会有和风细雨、如丝如缕的谈心。
一抹如银的月光从窗玻璃泻进来,铺洒在床上。夫妻俩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窗外,看见了秋风摇曳的树梢,树梢上明净如洗的夜空,夜空中繁星簇拥的一轮皓月。好圆好大好迷人的月亮啊!宋超倏地坐起身,惊讶地说:“呀,今天,不,明天是中秋节!”
“是吗?唉,我把这些事全忘了。”江隆基并没动身,只是望着圆月,又平静地补充了一句,“明天你给孩子买点月饼水果吧。”
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遇事不惊,事情愈纷杂外表愈平静。他何尝不爱这明丽的夜空皎洁的月光?激情不是诗人的专利。不作诗的人照样有诗人的激情,所不同者只是深深地沉在湖底而已。在已经逝去的生命岁月中,他读“四书五经”时眷恋过巴山汉水的月光;转战晋陕时眷恋过九曲黄河上的月光;延安窑洞里眷恋过宝塔山上的月光;还看过西安古城里战火中的月光,沙滩红楼上腥风血雨中的月光;还在东京看过东太平洋的月光,在柏林看过北大西洋的月光……月光属于全人类。月光是纯洁高尚的象征。月光给他以理想、追求、奋进、知识和品格,不管用不用语言表达,他都愿将自己变成一轮圆月,永远地清正洁白,光彩照人。
涌起这番思绪,他便觉得有话要对妻子说,转身来轻轻按妻子躺下,爱抚地摸着她的两腮。
“西北教育部时咱住什么房子?”
“两间小平房,没地板没顶棚,没厨房也没卫生间,夏天热,冬天冷,还不如陕北的窑洞。蚊子真多,还有蝎子,西安怎么那么多蝎子?我最怕蝎子,你不在的时候,我用蚊帐把床沿包得死死的,就怕蝎子钻进来。”
“能住两间就不错啦。西安潮湿,蚊子蝎子哪家都多。那……咱俩结婚时住什么房子?”
“呵呵,还房子呢?一面黄土坡,一溜土窑洞,是中央党校装柴草烧开水的,腾出来清扫了一下,两个单人床单一个挂窗帘,一个挂门帘,两个铺盖并―起,三块钱的南瓜子,一包边区自制的香烟,热热闹闹打发走战友们,就算入了洞房呗。旁边有个羊圈,睡觉都能闻见膻味儿。”
“你记性真好,那……我们家的老祖宗住什么地方?”
宋超只在解放后去过一次江的老家西乡白杨沟,下着绵绵秋雨,住过几天,回忆着说:“髙耸入云的大巴山下,由南向北逶迤出一道弯弯曲曲的山梁,山梁端头的半坡上,就是你们家。周围松柏竹林,两侧两个池塘,门前一条清澈的小溪,是块风水宝地,所以……就出了你这么个人物。”
“你也迷信风水,我问房子怎么样?”
“房子倒不怎么样。你们陕南的木材多,盖的房子却不敢恭维,简简单单,傻大粗笨。”
“这就对了,小超,我们家,还有你们家,祖祖辈辈何曾住过这么好的房子?住这么好的房子还要求这家具那摆设,难道真要我江某当王爷府里的王爷不成?”
“哎呀你呀,套来套去是在做我的思想工作呀!”
夫妻俩会心地发出了一串笑,笑解百愁。
江隆基睡不住了,起身到写字台前打开台灯,从刚刚收拾好的抽斗里取出笔记本,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
过去就听说燕京大学的校舍建筑得很漂亮,但我从来没有来过。
今天一看,果然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草木秀丽,形同公园。学校给我分配的宿舍是一中式外貌、西式装潢的住宅,里面有客厅、有卧室、有书房、有暖气和抽水马桶的设备。我自有生以来,从未住过这样阔气的房子。骤然搬到这样资产阶级的住宅里,内心颇感不安,我担心孩子们的生活贵族化,同时警惕自己的意识里滋生某些资产阶级的因素。自参加革命以来一贯过着供给制的生活,从来没有为吃饭穿衣的琐事而操心,现在,为了吃饭,喝水,必须另起炉灶,过小家庭的生活。这就整个制度上来说,虽然是前进了一步,但就个人的革命修养上来说,则可能发生某些退化的现象,不可不深自警惕。
中秋节之夜,江隆基去拜访校长马寅初。
对这次拜访的时间、地点,谈话的口气和方式,他都是再三再四地斟酌推敲过的。自己上学时,马寅初已是月薪六百大洋的名教授,只站在远处听过几次讲演,并无面对面的接触。其后马因无情地掲露四大家族的贪污腐败而触怒了蒋介石,关监狱遭软禁长达四年之久,江在延安,只知道个大概。解放后,马寅初是由周恩来、董必武派人从香港接回来的,最初任浙江大学校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陈毅点的将。调来北京后,出任国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副主任还有一位是薄一波,马和薄的办公桌对在一起,现在还去那里上班。
还有一层,在马老之前,中央曾动议派另一名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出任北大校长,但遭到北大教授们的强烈抵制,说他的学问是花架子,领导不了真学问,后决定派马寅初时,教授们竟一致赞同。
更有一层,谁都知道,他江隆基是以党的领导干部的身份出任北大副校长的,而北大现有校级领导中,就他一个是党员,故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将被视为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这责任这担子可想而知!
马寅初是三级干部,属国家领导人,与这样的大干部、大学者初次接触,他不能不想得细一些,透一些。他估计这将是一次艰难的谈话。上而言之,推心置腹地探讨一下如何搞好北大的工作,达成共识;退一步讲,是一次纯属礼节性的拜访,即便如此,也是十分必要的,非做不可的。
晚饭之后,江隆基动身去马老的住宅63号。两处相距很近,他踏着月光徒步而行。
夫人王仲贞将他领进一间宽大的会客室,安排坐在大沙发上,端来一盘显然是过中秋节的月饼和一盘水果。茶几上四五只干干净净的玻璃杯里,早已冲满了凉开水。之后说:“马老正在冲澡,你稍候,我去叫。”
江隆基没动月饼和水果,只端起玻璃杯呷了口凉开水,左右打量着会客室,果然与自己的迥然有别:铺着绒地毯,周围一圈沙发,一溜古香古色的茶几,同样是古香古色的橱柜里陈列着瓷器古玩和各种纪念珍品。顶壁悬着大吊灯。墙角有君子兰花架。一盏台灯下的小桌上,摆满了中央与各省的最新报纸。
尤其醒目的,是正面墙壁上悬挂着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联名书赠的贺寿联: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做伴支床有龟
另一侧,挂着一条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的已经有些褪色的红绸缎,是新华日报社送的贺联:
不屈不淫征气性
敢言敢怒见精神
两幅都是为祝贺马老的六十寿辰而作,而马老的六十寿辰是1942年在重庆蒋介石的监狱里度过的。现在读起来,更感是对马老人生品格的真实写照。江隆基正在仔细品味着,隔壁卫生间里隐隐传来哗啦哗啦的泼水声。
须臾,走廊上传来了朗朗的呵呵声,脚步声;接着一个浑圆敦实的小个子老头出现在客厅门口,趿着拖鞋,拖着浴巾,人未到声先到:“欢迎欢迎,有失远迎!”
“马老,您好!”江隆基起身迎上去,准备握手,不无歉意地说,“我来得早了点。”
马老用浴巾擦着肌肤,摆手说:“坐,江副校长你坐,在我这里不讲客套。”
夫人抱来一堆衣服,马老就地换穿。江又回到原位落座,借机仔细打量。
只见马老肌肉结实健壮,圆脸红润有光,头发花白且有些谢顶,但面部看不出褶皱,天庭饱满,笑口常开。若不是早知今年他七十大寿,就眼前的模样,怎么看去,都像个年富力强的少壮派!
“兄弟我有个洗冷水澡的习惯。刚才冲了个澡,让你久等了。”马老穿好衣服,过来坐在江的对面,抓起杯子喝了一气凉开水。
江惊异地问:“冷水澡?马老您这大岁数了,还洗冷水澡?这都中秋节了。”
“呵呵,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兄弟这个习惯,可以说是积习难改秉性难移。蹲蒋介石监狱的那几年,这点自由他还得给。开始也不给,我就跟他讲理说,你手下有个军界头目都说凉水洗鸡巴越洗越硬,难道你要我马某人当阴阳人不可!呵呵,咱当然不是为了那个对不对?咱得学会斗争。冷水澡对身体有好处嘛,用新社会的话说就是革命的本钱嘛。去年兄弟来北大,全校师生开大会欢迎,会场上学生打着‘热烈欢迎马校长’的横幅,要兄弟发表演讲。兄弟就指着那条横幅讲,大家既然热烈欢迎我,就得跟我好好学。学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学洗冷水澡,先在热水里泡了,把臭汗挥发出去,再在冷水里泡,一年四季,看谁坚持得好。还有,就是星期天跟我去香山登‘鬼见愁’,看谁爬得快?”
马老“兄弟”长“兄弟”短地谈笑时,很有点老顽童的脾性。江隆基也故意问:“马老,那么这凉开水……”
“是的是的,兄弟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水。兄弟浙江绍兴人,好茶有的是,偏偏无缘,就爱喝个凉开水。这也有理论根据,咱们老资格的共产党瞿秋白先生就说过,豆腐最好吃,白开水最好喝,此话有理。”说到这里顿住想了一下,突然朝里屋高声喊,“仲贞贤妻,给江副校长沏杯茶来!要龙井!”回头又说,“怕你喝不惯凉开水,好茶兄弟有。”
这种无拘无束、妙趣横生的谈话使江隆基的疑虑冰释了。初步形成的印象是,马老是个胸怀开朗、容易共事合作的长者,而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在切入正题之前,觉得有必要表达一下自己真诚的愿望。
“马老,对您我可以说是仰慕已久,只恨相识太晚,还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曾一度很想参加您领导的中国经济学社……”
“啊!”马老的表情出现了很大的惊叹号,“你也是北大毕业?好呀好呀,这可是有缘相会喜相逢啦!”
“不敢说毕业,只读了两年预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就去日本了。”
“兄弟我也是1927年离开北大的,当了十年教授,前几年还马马虎虎,后来的情况你也知道,总之是好人待不住,浙江省主席屡次来请,就拍屁股一走了之。”两人不约而同地陷入对往事的沉思。静默了一会儿,马老突然说:“看来,兄弟向毛先生的意见没有白提,提对了。”江隆基慢慢反应过来他所称的“毛先生”就是毛主席之后,睁大了眼睛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