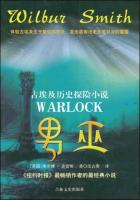弟弟砸烂农民赤卫军牌子的那天,县当局已经实行大肆清党。有人来村里调查谁是共产党。他们怀疑我与弟弟。许跃辉说:“我两个侄子哪里会是共产党,他们只会瞎起哄。“来人将信将疑,折腾了大半天,在酒足饭饱后回县城去了。我组织的农民赤卫军、渔民友谊社和创办主编的蚕桑报,就这样在白色恐怖中自行解体和停办了。那些剩余的蚕桑报,全都被弟弟烧毁了。看他胆小的样子,我心里很不高兴。我想我经叶天瑞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还不到两个月,革命工作的火炬刚刚开始燃烧就被迫熄灭,这让我多么愧疚难当。于是我给叶天瑞写信,告诉他我们这里的白色恐怖,并要求参加他那里的浙东秋收大暴动。
我的信一发出,心里便舒坦些,仿佛回到了组织的怀抱里,等待消息和命令。
婉玉自上次和三哥来荻港村后,一直住在我家里。我们的恋爱,少不了我的老同学三哥的触台。他把妹妹留在我身边,我与婉玉的恋爱便在外港埭走廊和曹溪河畔生根发芽了。自从家里有了婉玉,便有了人气和欢乐。婉玉咯咯笑的声音,阳光般明媚,使我渐渐从母亲去世的悲伤中走了出来。
那段日子,我在等叶天瑞的回信。漫长的等待,让我决定先抽空与婉玉去一趟盐官镇。我要向婉玉的父母求亲去,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出发的鄢天,我身佩宝剑,像个侠客一样,还雇一辆马车,带上送给婉玉父母的求亲礼物,并让车夫在马车的座位上,安装了篷布。一路上,篷布把我们围得严严实实。尽管有些闷热,但随着马车的颠簸,我们也快乐地颠簸起来了。中午时分,旷野上的阳光热腾腾地晒在篷布上。我们的体内,也是热腾腾的。婉玉从篷布小方格的窗帘上,伸出一只白白柔嫩的小手,把一团黏稠的碎纸扔出了窗外。纸屑就像白蝴蝶那样飞舞起来,落人远处开满山丹红花的土地上。黄昏时分,我们仍沉浸在无限的柔情蜜意中,马车倏地停住了,车夫大声说:“风情街到了。“我们被车夫的刹车和喊声,猛地一惊后,婉玉先下车去了。
我对车夫说:“把车子再往前挪几步,停在两扇黑漆大门口。“车停稳后,我从车上一件一东西。这时我看见管家与小娟来到马车前,而婉玉却不见了踪影。小娟一见我,冲我眨眨眼睛说:“你用东西来拐骗我们小姐,老爷可不会答应呢!“我问:“老爷和太太都在家吗?“小娟说:“在,在屋里头呢!你小心挨骂。“我说:“你个乌鸦嘴,别瞎嚷嚷。“我与管家把半马车的农副产品扛到客堂时,老爷和太太已经从里屋出来了。老爷说:“你就是长根?“我说:“是。“老爷说:“你会武功?“我说:“是,会一点儿。“太太从头到脚打量着我,就像打量一个外星人一样。接着她看看地上堆着的农副产品,笑眯眯地对我说:“路上辛苦了,请坐。“老爷请我与他面对面坐在木椅上。小娟给我递过来一小碗茶时,冲我眨眨眼睛。太太说:“带这么多东西来做啥?这些鸡啊、鱼啊、兔啊,是你们家里养着的吧?这丝棉是你们自己养蚕缫丝而成的吗?“我说:“是啊!都是自己家里的东西。“太太说:“你们那里可是笪米之乡啊!好地方,好地方呵!“太太胖胖的,穿着丝绸的大襟衣衫,走起路来两只丰满的乳房抖动着,像一种母亲的召唤。我面对老爷和太太,一下不知说什么。但叉不想冷场,便愣头愣脑开门见山地说:“老爷、太太你们好!我是婉玉三哥的同学,这回来府上,一是送婉玉回来,二是求亲。我要娶婉玉。“老爷皱着眉头冷冷地道:“我们婉玉已经有媒人说了亲。“老爷话音刚落,我的脑袋像爆炸一样,轰的一下晕眩起来。片刻,死一般的沉寂。接着老爷又说:“你把东西拿回家去吧!我们不缺这些东西。“老爷起身进里屋去了。他冷冷的语言,让我仿佛坠人冰河。
我沮丧极了。心想如果求亲不成,也要像我的表妹那样私奔吗?我这么想的时候,太太忽然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这老头子,人家辛辛苦苦来,摆什么冷面孔?别泄气,看你厚道,我帮你想办法说服老头子。“太太的话让我感到温暖,同时也看到了希望。
婉玉从她的厢房里出来时,换上了一身白底碎花衣裤。她的长辫子高高地盘在头顶,有一种成熟女人的妩媚。她走近我时,尽管为她父亲对我的态度让人有些沮丧,但依然遮不住荡漾在她脸上的幸福感。
老实说,她的幸福感增强了我的自信心。
天渐渐黑了下来。我告别太太和婉玉后,直奔小客栈。我要在小客栈住一宿,再回荻港村。小客栈里,依然是乱哄哄的。我穿过门口的小酒馆,到里面住宿处订了一间房。在房间里,我洗了把脸,然后到小酒馆吃饭。
小酒馆里,四张八仙桌坐满了人。有打牌的,有划拳的,有妓女唱歌的,有穷人讨饭的。那个由母亲陪着的小女孩乞丐,向我伸出了脏兮兮的手,我就给了她一个铜板。她们转到另一桌时,那些划拳的酒鬼正在兴致上,见来了这对要饭的母女便取乐。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两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呀,嘿!石头、剪刀、布。“然而他们说着说着,就下流起来。划拳赢的那个男人,耳光打到了小女孩头上。小女孩哇哇地哭起来,母亲忍不住嘀咕了一下,却被他啪啪扇了两个巴擘。
我路见不平,血气方刚地走过去给那个划拳赢了的男人两记耳光。
那男人先是一惊,接着便与我打起来了。和他一伙的那几个男人,也都参与我们的打架行列。杯盘碗筷嚓啷啷地打碎了。孩子哭,女人叫,小酒馆一下乱翻了天,顾客们仓皇而逃。我一拳一个对付着这些狗杂种,还从裤袋里掏出一根九节鞭,啪啪耍了几下。那威武,让这伙狗杂种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逃跑了。我大大地施展了侠客一样的功夫,让酒馆老板害怕得只能对我点头哈腰,重新给我温酒上菜。
我坐回桌边,跑堂的给我提来一坛绍兴黄酒,端来几盆小菜。这一回,我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跄跄地回到客房,和衣躺在床上。第二天醒来,我发现自己身上还佩着宝剑。早上洗脸刮胡须时,我看见自己的脖颈上,有被抓伤的痕迹。于是我换上一件灰色的中式褂子,那高高的领口,正好遮住脖颈上的伤痕。
我一直在等婉玉,可她迟迟没来小客栈。我有些不安,但也只得打道回府了。回去我不再雇马车,而是坐船。坐在船上,我浮想联翩。我想着婉玉,想着与她的肌肤之亲,想着我们的美好未来,便有些感动和自豪。回到荻港村,我决定把家里的每一间房都粉刷一下,让它们增添喜气。我买了石灰、水泥、油漆、涂料等,并让精武会的李阿二、庞九斤、丁一松、高大年、严家辉、杨鸿庆来帮忙。几天后,他们就把我家涂刷和油漆得一新了。新瓦屋里,我把父母和姐姐们的遗像都藏到了抽屉里,取而代之的是杨柳青年画。家里顿时洋溢着一股喜气,仿佛那漆过的门窗,那粉过的雪白墙壁,都在等待着、迎接着婉玉的远嫁而来。
我知道老爷后来同意婉玉嫁给我,是斟为婉玉怀上了我的孩子,生米做成了熟饭。老爷很重家族名声,痛恨伤风败俗之事。他对婉玉痛骂一顿后,约法三章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不准再回家来。“婉玉低头哭泣着。父亲的绝情,让她恨死了封建礼教。
太太是个善良女人。她见老爷绝情,便亲自为女儿准备嫁妆。婉玉的嫁农,是太太亲手缝制的。结婚前一天,婉玉的嫁妆装了满满一马车。有丝棉被子、床单、大小木盆等。我们的婚礼很简单,不过是三哥代表女方的家长,弟弟做证婚人,我的那些师兄师弟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罢。
婚礼上,婉玉头上戴着我送给她的一只漂亮的银色蝴蝶型发夹;那是我双胞胎姐姐大蚕花姑娘的定亲礼物,戴在婉玉头上闪闪的光芒就像银色蚕丝,美丽极了。我们的新房,就做在我父母从前卧室的那一间。那个晚上我和婉玉紧紧拥抱在一起,就像当年父亲和母亲制造风声那样,我如虎似狼地制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强劲风声。那一刻,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月光明晃晃地从天花板上透射进来。躺在床上,我们可以看见天边一轮银白的月亮。那月亮上有嫦娥奔月,有玉兔和木匠。但我不看,我把头埋进婉玉的怀里,告诉她我从来没有这么温暖幸福过。她天真地问:“是吗“我就吮吸着她的一对丰满乳房。我称它们是我的太阳和月亮,是北高峰和南高峰。她就咯咯地笑,把我搂得更紧了。我说我永远爱你,海枯石烂不变心。她被我的话感动了,紧紧抓着我,我们一次像浪推舟那样,颠簸晃荡起来。
与婉玉完婚后,我又进入了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小娟随婉玉嫁到了我家,家里就多了两只花蝴蝶。我是家里的主人了,小娟管我叫老爷。她再也不与我做怪相了,我们的距离忽然就远了。婉玉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大得出奇。我每天晚上都会趴在她肚子上,听我的宝贝儿子在她肚内徜徉,蹬腿。一种马上要做父亲的感觉,溢满我的胸间。太太让三哥送来了小棉衣、小衫儿、小鞋子。婉玉自己编织小毛衣,我则用藤条编了一辆婴儿车。
小娟是于活儿的一把好手,她把家里收拾得千干净净。那个西厢房给她住后,窗帘上丁丁当当地挂着她做的手工布艺制品。有小老鼠、香袋、鸡心、布娃娃等。我知道小娟是到了该嫁人的年龄了。我想纳她为妾,可她娘家忽然传信来让她订亲去。女大留不住啊!她想走就让她走,其是婉玉舍不得。婉玉对小娟说:“你订完亲马上回来。我要生孩子了,家里少不了你。“小娟噢噢地应着。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突然感到一种失落和期盼。
小娟回家乡去后,我找了师傅独眼龙的女人王二婆子来家里帮忙。
王二婆子是个喜欢搬弄是非的女人,又是一个骚婆子。她东家长西家短川总有讲不完的新闻和是非。她说大肚子要多走走,生孩子便快。于是,婉玉每天都去村里和田野散步溜达。那些日子,婉玉出门散步溜达时,王二婆子总是不失时机地与我讲她和师傅独眼龙的故事。几个月下来,我听得烦了,心想这王二婆子简直如同妓女一样,毫无羞耻。
那天,王二婆子趁婉玉散步溜达去了,又与我讲独眼龙是男人中的男人,是一块钢。她反复说这话,好像我不是男人中的男人,不是一块钢似的。他妈的,我一恼火,那种对女人的占有欲就上来了,我粗暴地一把将王二婆子摔到床上。
婉玉回来时,我们表面上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但我心里明白,我与王二婆子这么一来对婉玉的爱就不那么纯粹了。我心里恨自己,更恨王二婆子。我想这个骚婆子,就是再白给我,也不干了。我对婉玉有一种内疚,想用男人的温柔来对她做些弥补。于是这晚我给她洗脚,剪脚趾甲。婉玉抱着我的头亲昵地说:“你真是一个好丈夫。“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等叶天瑞的回信,可是迟迟不来。眨眼已是深秋了,与叶天瑞失去联系,也就是与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让我惶惶不安。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浙东秋收大暴动。叶天瑞将负责组织占领上虞县城,肯定有不少工作等待着我去做。然而在这节骨眼上,他却毫无音讯了。我们县的白色恐怖依然未解除。我的一举一动都在暗狗子的监视中。我组织的农民赤卫军、渔民友谊社和创办主编的蚕桑报停顿后,一时很难复原。我只好又像儿时那样,到外港埭走廊的小戏院里去蹭戏听大书了。没有了革命工作,我就盼着婉玉生下儿子来。
那天,我去外港埭定廊听大书,说书先生吴雪雷精神抖擞,中气十足,仿佛越活越年轻了。他仍然讲《三国》,讲《水浒》,讲《红楼梦》;这些被他讲了多年的大书,每回讲都能讲出新意来,让人常听不厌。这使他的名声,比我们村庄从前出过五十多名进士、状元和一百多名太学生、贡生、举人的名声要大得多。大家亲切地叫他”吴先生“,而我叫他”吴说书“。吴说书通过说书,让村里的文盲都知道了古典文学名着中的人物名字和故事。所以我们村的村民,即使吵架骂人也会搬出贾宝玉、林妹妹、薛宝钗、王熙风、曹操、武松、宋江等人的名字,显得很有文化味。
完大书,我从庙前桥下来,遇上了弟弟许长海。许长海刚刚当上村长,脸上遮不住内心的喜悦。母亲去世后。二叔大部分时光是懒懒的井寸里的事不管不问,人也越来越瘦了,还经常咳嗽。大家觉得他已经不适合再当村长了,就推荐弟弟当村长。经投票选举,弟弟以满票被选为村长。这会儿弟弟对我说:“小山给你来信了,你回去看。“我觉得有点奇怪,写信向来是小妹的事,小山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怎么写?莫非小妹出事了?我这么想着,心怦怦地跳起来,快步如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