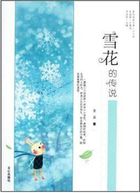他知道今晚走不了了,低头无语。
“双喜,你爹就你一个儿子,你要走了他可指靠谁哩?你知道么,你这些日子没回家,你爹你妈都急疯了。你要这么偷着走了,还让他们活不活?”吴富厚卸下他肩上的行囊,拍着他的脊背说:“回屋睡去吧,再甭耍娃娃脾气了。”
他知道有师傅盯着,他插翅也难逃,沮丧地回屋了……
时隔一日,秦盛昌把账务交给儿子管理,并让小伙计满顺专一伺候儿子。满顺看上去有点儿憨相,办事有点儿粗脚大手,却深得秦盛昌夫妇的信任。
两年前满顺来到秦家扛活,整天价嘻嘻哈哈秦腔乱弹不离口,似乎他到秦家不是当长工而是享福来了。秦杨氏很是奇怪,问当家的是咋回事。秦盛昌笑道:“穷娃心里不装事,不知道愁苦。”秦杨氏不以为然。秦盛昌便说,他有办法让满顺不笑不唱,秦杨氏不相信,问他有啥办法。秦盛昌笑着说:“办法先不给你说,几天后你自然就知道了。”
第二天,满顺喂牲口时在草料堆中捡到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一百块银洋。他心里突突直跳,慌忙四顾,草料房里除了他,只有一只老鼠在房梁上爬行,黑豆似的眼珠子在窥视他。他急忙把布包揣进怀中。喂了牲口,他回到伙计房里,把布包塞到被子里,觉得不安全,取出来又塞进鞋窝,还是觉着不妥。一时间他拿着那个布包犹如捧着一个火炭,不知往哪里放才好。吃午饭时,秦杨氏发觉到满顺不对劲,平日里嘻嘻哈哈乱弹不离口的满顺一反常态,不笑不唱,一张憨厚的娃娃脸上愁眉不展。秦杨氏大为惊讶,私下里问当家的是咋回事。秦盛昌笑而不语。
往后两日,满顺不仅不笑不唱了,饭量也大减,干活丢三落四,丢了魂似的。秦杨氏着急起来,再三追问:“你使了啥魔法,看把人家娃愁成啥了。”秦盛昌笑道:“我给草料堆放了一百块银元,让满顺捡去了。”秦杨氏先是一怔,随后慢慢有所醒悟。
到了第三天晚上,满顺走进了秦盛昌的屋:“老爷,我在草料堆里捡了一百块银元。”说着把布包放在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秦盛昌笑道:“你捡的就拿去使唤吧,给我干啥?”
满顺急得直摇手:“不不,钱是在秦家的草料堆里捡的,这钱是你秦家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说罢抽身就走。
第二天,满顺一扫愁容,又唱起了乱弹。
打那以后,秦盛昌夫妇对满顺信任有加。秦盛昌让满顺伺候双喜,一是信任满顺,二是希望满顺历练历练,将来能像吴富厚帮他一样帮双喜。可双喜并不领情,老是找个差事把满顺支开。他把自己关在账房里,终日不出门,连饭也懒得吃,秦盛昌就让丫环菊香把饭送到账房去,秦杨氏见儿子终日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忧心忡忡地给老伴说:“喜娃不愿管账房就算了,当心把娃憋出病来。”
秦盛昌瞪着眼道:“真是妇人之见!他想干啥就干啥,咱秦家的基业还要不要!”
秦杨氏自知老汉说的话在理,不再吭声,只是在心里暗暗为儿子担心着急。
这日中午,双喜坐在账桌前正在烦躁地拨拉算盘,喜梅拿着一个风筝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哥,放风筝去!”
双喜立刻兴奋起来,把算盘推到一边,站起身来:“走,放风筝去。”
秦盛昌端着水烟袋忽然出现在门口,威严地咳嗽了两声,瞪了女儿一眼:“你跑到这达来干啥?还不出去!”
喜梅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撅着嘴转身跑出了屋。
双喜叹了一口气,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拨拉起算盘,算盘珠的响声无序而嘈杂,带着烦躁不安和憋闷……
秦盛昌出了账房,回到屋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一脸的忧郁之色。竹帘一挑,秦杨氏走了进来,看到老汉的模样,讶然道:“又出了啥事,看把你愁的。”
秦盛昌叹气道:“我是愁双喜哩。”
“双喜又咋了?”秦杨氏大惊失色。
“唉,他的心野了,一天到晚心不在焉。”
“这个我也看得出,我真怕把娃憋日塌(坏)了。”
“也憋不日塌,咱得想个法子把他的心拴住,你说说,啥能拴住他的心?”
“能拴住男人心的,只有女人。”
“你是说给喜娃娶个媳妇?”
“双喜已经二十出头了,早该成家了。以前那么多人上门提亲,都让你给回了,真格是的!”秦杨氏不无怨言。
“不是我回绝人家,是喜娃不让急着给他说媳妇么。”
“这事就由着他咧?”
秦盛昌自责道:“这事怨我,咱立马给他说个媳妇,说好就娶。找个门当户对的。”
“不光是门当户对,要紧的是模样要俊。”
秦盛昌有点疑惑地看着太太。
“看我干啥?想当年你还不是看上了我的模样……”秦杨氏说着羞涩地笑了,似乎回到了少女时代。
秦盛昌心里不禁一热,双手一揖:“夫人言之有理,为夫一定照办不误。”
“看你,老了老了,倒不正经了……”秦杨氏攥起拳头捶打老伴的胸脯,秦盛昌抓住她的手,轻轻一拉,她顺势倒在了老伴的怀中,俩人无声地笑了。
这日中午,双喜正襟危坐在账桌前,一手执笔,一手拨拉算盘,口中念念有词。这几日,他狠下决心,使自己心无旁骛、凝神贯注料理账务。他想事情已经这样了,就应该把账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不能让父母失望。
喜梅悄悄走了进来,他全然不觉。喜梅爬在他的耳畔突然大叫一声,吓了他一跳,他扭脸一看是妹妹,佯嗔道:“鬼女子,别捣乱!”
喜梅咯咯笑道:“哥,别假正经了,到外边耍去。”
双喜惶然地望着门外。
喜梅笑着说:“爹在客厅跟人说话哩。”
双喜刚下的决心一下子就垮了,雀跃而起。这时,满顺走了进来:“少爷,你干啥去?”
“不干啥去。”双喜眉头皱了一下,随口道,“满顺,你去杂货店一趟,把上个月的账本给我拿回来。”
满顺答应一声,出了门又转回头来:“少爷,你可不要乱跑。”
双喜不耐烦地摆摆手:“快走快走!”
满顺走了,双喜喜笑颜开,问妹妹:“咱耍啥去?”
“放风筝!”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双喜故作正经地吟了一首诗,随后摇头道,“那是娃们在春天玩的耍货,现在都过小满了,放风筝没意思。”
“那咱耍啥?”
双喜忽然想起了什么,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红绸小包装进衣袋。喜梅问:“哥,啥东西?”
双喜诡秘地一笑:“先不给你说。”
兄妹二人悄悄地溜出家门。双喜孩童似的欢奔着,犹如出笼的鸟儿。喜梅在后边边跑边喊:“哥,等等我。”
节气已过小满,小麦已灌浆,日渐成熟,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摆起伏,扑打着他们的衣襟。刚刚下过一场雨,树木格外翠绿,天格外蓝,几只燕子在自由地翱翔。双喜扬起双臂大声说:“在屋里憋死我了,今儿个要美美地耍耍。”
喜梅追上来,喘着粗气说:“哥,给你说个事。”
“啥事?”
“你知道这几天咱家客人不断是为啥事么?”
“不知道,为啥事?”
“给你说媳妇哩。”
“你胡说哩。”
“谁胡说了?不信你问咱爹妈去。”
“他们是瞎操心哩。”
“哥,你不想娶媳妇?”
“不想娶,我光想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喜梅,你尝过失去自由的滋味么?我可尝过,那个罪可真难熬哩。”
“哥,你别卖文了,自由不就是耍么?谁不爱耍。”
双喜笑道:“对对对,自由就是耍,咱到那边耍去。”
“那边是土崖,有啥好耍的。”
“走吧,哥给你看个耍货。”
村北有一道沟,沟两边是土崖,土崖上长满了刺槐,沟底杂草丛生,十分背静,很少有人来。兄妹俩来到土崖边,双喜从衣袋掏出红绸包打开,是一把锃明发亮的小手枪。喜梅惊喜地叫道:“手枪!哥,哪来的?”
“别人送的。”
“谁送的?”
“一个同学。”
喜梅狡黠地眨眨眼:“我不信,同学给你送书送笔,我信哩,哪有这东西送你?一定是那个郭鹞子的女子送你的。”
双喜笑着在妹妹的额头上戳了一指头:“你真是个人精,可不许给爹妈说。”
“那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啥条件?你说。”
“教我打枪!”
“行。”
双喜压上子弹,瞄准崖下一棵槐树射击。喜梅惊叫着,急忙捂住耳朵。枪声惊起一群山鸡,扑棱棱飞起,向远方逃遁……
就在双喜兄妹玩耍兴头之时,秦盛昌夫妇在客厅里和邻村的刘媒婆也说得正热火。刘媒婆是初次到秦家。进了秦宅,她只觉得眼花缭乱,边走边咂舌,啧啧有声,显然是少见多稀奇。来到客厅,刚一落座,便有丫环端来糖果和茶水。刘媒婆肚中空虚,并不青睐茶水,却对糖果情有独钟,不等主人礼让,伸手就抓了一个糖果塞进嘴中,吃得太急,噎着了。她急忙端起茶杯,茶水太烫,又烫了嘴。秦盛昌夫妇相对一视,忍俊不禁。刘媒婆也感到自己有失体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随即用手帕擦了一下嘴,说道:“秦掌柜,秦太太,要是换上别家,我才不跑这个路呢。是你家的少爷,那我是没说的了。你们秦家家大业大不必说,人也都是好人哩。”
秦杨氏含笑点头,随口问道:“那个闺女长得咋样?”
刘媒婆赶紧说:“那闺女长得鼻是鼻眼是眼的,没有一点儿弹嫌的地方,跟你家少爷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
“我儿子可在省城念过书哩。”
“那闺女虽说没念过洋学堂,可她爹小时候给她请过先生,闺女聪明,识了不少字,知书达理,十分难得。”
秦盛昌插言说:“女娃娃家识字不识字倒也没啥,可得有模样。”
刘媒婆急忙说:“有模样有模样,简直就像从画里走下来的人儿哩。她要模样差池点,我也不会来给你家少爷提这门亲。”
秦杨氏道:“不知人家愿意不愿意跟我老秦家结这门亲?”
“愿意愿意。他们听说是昌盛堂的少爷,一家人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你家少爷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也难找哩。”
秦盛昌笑道:“这就好,这就好。”
“秦掌柜,秦太太,好事宜早不宜迟哩。”
秦盛昌看看太太,秦杨氏点点头。秦盛昌转脸对刘媒婆说:“你给女方家回话,这门亲事我们答应了。”
秦杨氏说:“我们择吉日就把聘礼送过去。”
“那我这就去给女方家回话。”刘媒婆起身告辞。
秦杨氏给菊香使个眼色,菊香会意,拿过一个大手巾把盘子里的糖果包了起来,塞给刘媒婆。刘媒婆欢天喜地地走了。
送走了刘媒婆,秦盛昌来到账房,只见账桌上的账本胡乱摊着,算盘抛到了一边,不见双喜的人影。
他当下沉下了脸,叫来满顺,问少爷哪里去了。满顺刚从杂货店取账本回来,支吾说:“少爷上茅房去了。”他肚里有气,立马让满顺去茅房叫回双喜。半天工夫,满顺哭丧着脸回来了,说少爷没在茅房。他让满顺赶紧再去找,满顺站着没动。他勃然大怒:“你耳朵聋了,没听见我的话么?!”
满顺吓傻了:“老爷,前院后院我都找了,不见少爷的影子……”
“不见影子?你是干啥吃的?”
“我,我,我……不不,是少爷让我去杂货店取账本……”满顺语无伦次,吓得变颜失色。
就在这时,窗外传来双喜兄妹的欢声笑语。秦盛昌站住脚,怒目瞪着门口。
双喜一脚刚踏进账房门,看见父亲满面怒容,笑容僵在脸上。喜梅瞧见父亲,吓得一吐舌头,急忙躲到一旁。秦盛昌摆了一下手,满顺急忙退了出去。账房里只有父子俩。
“你干啥去了?”秦盛昌怒声喝问。
双喜垂下目光,不吭声。
“你一天到晚不着家是想弄啥哩?!我白供你念了这么多年的书!”
双喜木橛似的戳在那里。
“你呀,让我失望得很!”
双喜自知有愧,一声不吭。
秦盛昌息了息心头的怒火,缓和了一下口气:“喜娃,你都是要娶媳妇的人了,往后可不敢再逛荡了,要生心哩!咱家可就你这一根顶梁柱!”
秦盛昌吸了一口烟,少顷,又说:“喜娃,爹给你说了个媳妇,模样人品都没弹嫌的地方。明儿个我让你师傅把聘礼送过去。好事宜早不宜迟,这个月十五就成亲。”
双喜十分惊愕,半晌,叫了起来:“爹,这不行!”
“咋不行?”
“说媳妇你咋不给我说哩?”
“我这不是就给你说哩嘛。”
“我不娶媳妇!”
“不娶媳妇?”秦盛昌一怔,随即笑道,“是男人谁能不娶媳妇?你都二十二了,早该成家了。”
“不,我不娶媳妇。”
秦盛昌脸色难看起来:“你再说一遍!”
双喜也犯了犟脾气,一口咬住屎橛子不松口:“我不娶媳妇!”
“你把书念到狗脑子去了!老子的话你也敢不听?”秦盛昌勃然大怒,“娶不娶媳妇由不得你。”说完拂袖而去。
第二天,秦盛昌备了份丰厚聘礼,让吴富厚给女方家送去。他要趁热打铁。
转眼到了农历四月十四,秦家的伙计丫环里里外外地忙乎着,张罗着给双喜娶亲。宅里已搭起了席棚,厨子们在厨房里杀鸡宰鸭,刮鳞剖鱼,煮肉烧汤,烹炸肉丸……忙得不亦乐乎。吴富厚指挥几个伙计给大门口张灯结彩,秦杨氏吆喝着丫环接待来客。秦盛昌端着水烟袋,踱着方步里出外进地巡查着,不时吆喝几声,面露满意的微笑。宅里宅外忙而不乱,营造着前所未有的喜庆气氛。
双喜躲在账房里,坐在账桌前发呆,他似乎是个局外人,宅里的事与他无关。其实,他此刻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麻。说实在话,他很想娶媳妇,他二十出头了,身体又没毛病,能不想女人?可他心里想娶的是林雨雁那样的知识女性,或者是郭玉凤那样豪爽开朗的女子。他读过不少书,知道什么叫“爱情”。他想自己给自己找媳妇,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父亲强迫他结婚,他都不知道那个女子姓啥名谁,是个光脸还是个麻脸。他无法想象和这样的一个陌生女子怎样在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