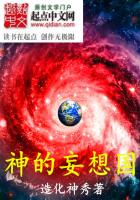这里的中心问题是把日常的生活现象提高到典型的真实,也就是要把真实性与典型性结合起来,实现更大限度的真实性。我认为,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务须处理好以下几个范畴的关系:
第一,关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文艺反映现实生活,不能脱离开生活存在的具体感性的实存状态,这决定它要以生活现象为反映的对象,并把生活的生动现象化为艺术形象。可是我们在长期的文艺史上看到,艺术中的形象表现,却并不止于现象的展现,它乃是借现象的表现而同时表现本质。
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的内部联系,这种联系是由事物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构成的。虽然内部联系隐藏在各种偶然现象当中,但各种偶然现象与本质的距离程度并不同样远近,对本质所承担的负荷量又不完全相同。为此,作为艺术所表现的对象,并不是可以不加选择的。我们看到历史上许多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都很注意选取最接近事物本质的现象、最富于本质性的对象。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很是注意“研究偶然”的,但他却明确地意识到,还要从无数的偶然中划分出他的创作所需的“主要事实”、“主要事件”,并要“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寻出隐藏在广大的人物、热情和事故里面的意义。”《〈人间喜剧〉前言》。他认为,仅仅是“严格摹写现实”,可以成为画家、剧作家,但不一定能成为艺术家;艺术家须有对现实现象的选择,有选择之后的意义发掘,以及发掘中的“对自然法则加以思索”。
从现象入手并选择现象来加以表现,这是现实主义的真实论。莫泊桑从现实主义艺术家都从“充满了偶然的、琐碎的事件的生活里,采取对他的题材有用的、具有特征的细节,而把其余的都抛在一边”的实践经验出发,提出现实主义的真实应该有别于生活的“平凡照相”,应该用“选择”和“修改事实”的方法,达到超过“事实真实”的“逼真的真实”。他说:“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是个艺术家的话,就不会把生活的平凡的照相表现给我们,而会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我们。”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艺术表现生活不可能也无必要描述生活中的一切现象。用莫泊桑的话说是:“把一切都叙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做,每天就至少需要一本书来列举我们生活中那些无数没有意义的琐事。”
有一种看法,它把现象与本质完全等同起来,以现象表现本质来否认现象的差别性,并进而把现象权威化。这种观点付诸创作实践,肯定是不利于艺术的典型的真实性的。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艺术不同于科学,但在分析现象、选择现象,并披露现象的内在本质上,它们却有某种一致性。我们的艺术创作应该通过对于现象与本质统一的生活描写,达到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统一。
第二,关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由于作家在作品中要表现人生世相的具体状貌,他不仅在选取情节事实上注意材料的个别性,而且见诸艺术形象时也是个别的,力求达到不可重复的特殊地步。歌德说:“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摹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个别性对于艺术来说,是艺术真实的具体存在条件;失去了个别性,也就等于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形式。列宁说:“只有个别的东西才是现实的。”从个别性是真实性的显现条件来说,个别性是很重要的,因而也是不可不追求的。
然而对个别性的追求,却不能不考虑它与一般性的关系。按生活辩证法来对待事物,事物的一般性都是借个别性以存在的。这种一般依存于个别的关系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怎样理解列宁讲的“个别就是一般”,却是要费一些工夫的。“个别就是一般”,是讲对立面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不能在个别之外存在一般。艺术中表现人物也是如此,不能在个别性之外去要求一般性的概括。问题虽然如此,却不能对任何个别都认为具有同样的一般的意义。因为个别之间所包括的一般性,不仅程度、方面不同,以至意义也不同,更何况个别都不是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的。因为,“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因此,当艺术家面对个别的人物素材时,透识其与一般的联系程度、所代表的一般的具体方面,就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了。如果一个作者不善于进行这种工作——即在典型塑造的目的下,从真实的生活具体中,选择、集中个别的人物素材,由个别向更突出的一般接近,再以个别体现出来,达到个别与一般的统一——而是由个别到个别,甚至是猎求奇异,像列宁所指斥的,“把种种‘惊闻奇事’串在一起”,这不仅反映不了生活的本质真实,反而容易形成对于生活的歪曲。列宁在评论文尼阡柯的小说《父亲们的遗嘱》时指出:“像文尼阡柯所描绘的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个别的在生活中是有的。但是,把所有这些凑在一起,并且是这样地凑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在绘声绘色地描述骇人听闻的事,既吓唬自己又吓唬读者,把自己和读者弄得‘神经错乱’。”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作者应予注意的问题。我们所追求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应该在个性的典型化概括中得到实现。
第三,关于人物与环境的关系。
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内容,就本题所指的真实性与典型性的关系而言,则是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对于人物的表现,作家可以把他放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中。但这不同的环境条件,基本上只有两大类,一种是比较自然形态性的环境,一种是通过具体人物关系所表现的社会典型环境。应该说这两种环境都是具体的、真实的。但也必须指出,从典型塑造的高度来说,这两种真实,在意义与程度上是不同的。作家的创作要追求典型的真实,不能不把人物的表现放在典型环境之中,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作品中的人物只要有他的存在空间,就意味着是有环境的。有经验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仅善于安置人物活动的场景,也很注意人物产生、活动和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并在艺术描写中,让这些社会历史条件转化为具体的人物关系,以情节中的人物关系体现社会历史的典型环境。这样表现人物,可以把人物从个人自在的环境中,引入到广泛的社会历史潮流之中,使人物的思想、行为、命运具有更充分的社会历史性,更大程度地体现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红楼梦》的作者,如果不是把荣国府与清中叶封建宗法制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深入观察社会的新旧矛盾,概括出一个富有历史真实性的“混世魔王”,而是采取肤浅的事实,写一本才子佳人的小说,使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它的真实的意义与程度,都不会像今日《红楼梦》这样独有殊荣。这种艺术成就,归根结底是曹雪芹把人物与社会历史的典型环境联系起来,高度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的真实。
文艺反映生活的历史经验证明,按生活中发生的真人真事来如实地构造作品,不考虑时代历史的特点,不按生活的客观逻辑规律去进行艺术地改制与加工,往往是欲求其真,反致于假。因为,生活的自然形态中,存在着“最相异、最意外、最相矛盾、最不调和的事物”,“它是粗糙的,没有次序,没有联贯,充满了不可理解的变故。”所以,对这些自然形态的生活事实,必须加以选择、取舍,存废增删的标准,取决于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需要。用“生活中有”为理由反对典型化的处理,是不合乎艺术反映生活的规律的。
当然,我们坚持按照恩格斯提出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要求人物与情节的真实性,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具有一定真实性的作品。恩格斯自己在提出了有名的现实主义全面要求之后,也仍然给他所不甚满意的小说《城市姑娘》,以应有的肯定评价,说它在自身的环境与性格的关系中“是够典型的”,只是革命的艺术家还应有更高的自觉争取的目标。我们今天在此重谈这个问题,根本目的也完全是在这里。
艺术表现中的真实性的追求,牵涉到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以及艺术处理的各个环节。在这两方面的问题中,深入、广泛地取得生活之本原,使作品的实体内容切近世相是一个方面;而在艺术加工中,把多方面表现提高到典型概括的高度上来,正是保证达到反映本质真实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