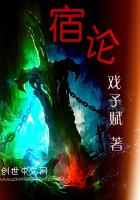四
第二天是个艳阳天,太阳红艳艳地照着,夜里那一山的浓雾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消退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王安全睁开眼睛的时候二颤正弯着腰在灶前煮粥,包谷糁的香气弥漫在清晨的空气中,温馨而舒展。北面铺上的人已经起来了,正蹲在床前翻弄他的口袋。见王安全醒了,那人主动打招呼说,你睡得好死,外面的鸟吵得昏天黑地也没把你吵醒。王安全朝他笑笑,以表示友好,对方个头不高,高颧骨深眼窝,说话略带沙哑,看模样是个精干的南方人。
南方人说他姓佘,佘太君的佘,叫佘震龙,今年43岁,又问王安全贵姓,王安全说了,老佘说王安全长他两岁,应该是大哥了。王安全问现在几点了,老佘说九点半了。王安全没想到后半夜这一觉竟睡得这么实,坐在铺上愣愣地看了半天脚底下,想着夜里床上那一盘蛇,总觉得不真实。回过头看身后的娘娘像,慈眉善目地也正看着他。娘娘的披风端端地在身上披着,他掀起娘娘的衣角往里瞅,里面是泥像的座椅,再往里就是砖墙了。放下娘娘的披风一回头,他看见二颤正用蛇一样的目光使劲盯着他。
吃过早饭,老佘提着口袋要出去,被王安全拦了,王安全说东边山顶有雨云,呆会儿会有场不小的雨。老佘半信半疑地留下来,坐在台阶上等着下雨。果然没有半个时辰,天空就被云彩遮严,噼里啪啦掉起了雨点。开始雨水顺着房檐往下滴,很快就流成了一条线。一道电闪,将天地连接,几声炸雷,在脚下炸裂,轰得地动山摇,整座山头要塌了似的。雨越下越大,雨借着风势将草木砸得歪斜,匍匐到地面,狂暴的水帘好像将人间的所有水流汇集在这里,倾泻,一味地倾泻。一只狐狸,从雨中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到庙檐下避雨,狐狸好像对这里很熟悉,它心安理得地蹲坐在台阶上,也不避人,像是农家的小黄狗。王安全和老佘看了半天下雨,都显得有些无聊,老佘继续变戏法似的在翻检布口袋,在上面寻找破洞,后来又将个白玻璃瓶子对着窗户使劲照,说是二颤偷了他的白酒。
大雨倾盆,没有停止的迹象,雨水顺着西墙往下流,王安全帮着二颤用塑料布遮挡那个窟窿,搞得浑身精湿。老佘拿一块干馍馍逗弄檐下的小狐狸。小狐狸睬也不睬,端坐着,很严肃地看着雨中的山林。
王安全换了身干松衣裳穿了,对老佘说,你招它干什么?
老佘说,好玩儿。
二颤要出去,王安全拽过二颤,将他的腕子按在小饭桌上,给他号脉。二颤不愿意,身子在桌边扭了几道弯,王安全在他的肩上用力拍了一巴掌才不动了。老佘见王安全会看病,也好奇地凑过来,想听听王安全说些什么。
下雨天,闲着也是闲着。
王安全在二颤的腕子上按了半天,脸上渐渐现出疑惑,按完了左手按右手,没按出半点儿名堂。应该说王安全是个很不错的中医大夫,在学院也是个副教授级人物,望闻问切,辨证施治,临床经验也相当丰富,带出的学生一批又一批,其中不乏杏坛优秀,而这会儿竟然被二颤的脉象难住了。王安全说不清手底下是怎么回事,二颤这两个手腕,六脉不分,寸、关、尺混成一统,用力按之,指下如循游蛇,虚滑流利,弯曲绵延,说是肝肾虚弱,风寒异受,似又不是,看脉象已病入膏肓,无药可医,应该是起不了床的,而眼前的二颤却是这般灵动强壮,脉不应病,实难解释,除非他不是人。
王安全看了看二颤的舌头,舌头黑紫细长,吞吐灵活,只那么虚虚地晃了一下便将王安全吓了一跳,险些没从凳子上翻下去。
天哪,这是什么舌头啊!
老佘饶有兴致地看王安全诊病,见王安全号完脉立即追问,这个精身子满山跑的黑汉子得的是什么病,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王安全说二颤的病他看不了……
王安全还是第一次在人跟前说这样的话,这对大夫来说真是很丢面子的事。老佘说不用号脉他也知道,这个二颤在娘肚子里没长熟就出来了,呆笨憨傻,不懂人事,是介乎人和虫之间的物件。
二颤用蛇一样的眼睛将老佘翻了几翻,老佘说,你甭这样看我,我说的就是你,别看我是你哥的朋友,可不是你的朋友。
王安全对老佘说,二颤不傻,你别当着面这样说他。
老佘说他怀疑二颤是从蛋里孵化出来的,正常的人不应该是这个长相,这个做派。
凶猛暴烈的豪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太阳从云彩后面绽露出来,万道霞光普照着滴翠群山,西边天际现出一道彩虹,七彩缤纷,随着云气的浮动越来越近。于是,远处的山峦便浮现出连绵不断的淡蓝淡紫的线条,山川草木反射出晶莹的光亮和浓郁的清香。
二颤抱着一摞碗到泉水边去洗了。
小狐狸悄悄钻进了草莽之中,两只太阳鸟在松树上叫。老佘有一搭没一搭地拨弄着王安全的半导体,音乐台正在播放民乐合奏《金蛇狂舞》,旋律活跃欢快,优美流畅,老佘将声音放得很大,半导体的音量已经调到了极限。
王安全说,你给我省些电池罢。
老佘说,怕什么,用完了我让人从山外头给你捎来,不就两三块钱的事儿么。
王安全不想跟老佘再说什么,一抬头他看见二颤在阳光里随着音乐在扭动着身体,他那活泛柔韧的身子忽而蹲下蜷成一团,忽而站起抻成一条,胳膊随着身体变化上下伸展,“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二颠的动作颇像训练有素的舞蹈家,衬着雨后青山,衬着霞霭蒸腾的山谷,伴着传统经典民族旋律,二颤昂着头,伸展着臂膀,看着遥远的天边,沐浴着灿烂霞光,脸上的表情幸福舒朗,如入无人之境,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
王安全说,二颤在跳舞。
老佘说,这不是人,这是一条长虫。闻乐而舞,跟印度耍蛇人口袋里随着笛声摇摇晃晃的长虫没有不同。老佘说着啪地关了半导体,音乐戛然而止,二颤像受到什么指令,突然地恢复了常态,他呆呆地愣了一会儿,从地上抱起那摞碗,跟刚才完全判若两人。
王安全说,这倒怪了。
老佘说,这有什么怪的,长虫是没有听觉的,它是靠振动来感觉旋律的,二颇为什么不会说话,因为二颤根本听不到声音,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凭感觉。老佘告诉王安全,二颤是二颤他妈和长虫杂交的产物,是个地道杂种。
王安全问谁说的,老佘说山上山下人都这么说。王安全说这是一派胡说,人和蛇就不能相交,就是交了也产不出任何结果。老佘说二颤他妈殷姑娘活着的时候会下蛊,大颤的爹就是殷姑娘蛊来的,他爹原先是华阳那边塑神像的工匠,有一年背着家什跟着他父亲出山去找营生,爷俩走到长虫坪又渴又饿,就歇在了殷姑娘门口。殷姑娘生得俊,爹妈早早死了,是个孤女,见来了两个过路的,很是殷勤招待。这爷俩知道长虫坪的女人惯会干那种事,心里警觉着呢,坐在殷姑娘门口老老实实只啃自己的干粮,不碰主家一点儿东西。殷姑娘看不过去,从屋里拿了一个碗,当着父子俩在屋边的流水里一遍遍洗了,恭恭敬敬地端过来。也是父子俩太渴,也是殷姑娘的模样可人,爷俩想,这么个小姑娘,料也不会使那手段……就喝了水,也的确没见怎的。歇够了脚继续上路,殷姑娘送出几步说,下回还来啊!儿子回过头也向殷姑娘挥手说,回来路过还喝你屋的水。应了姑娘“下回还来”的话,没走出五里地,儿子就犯了病,脸色煞白,口吐白沫,肚子疼得直不起腰,眼看命在旦夕。当爹的明白是姑娘给水里下了蛊,背起儿子就往回跑,来到殷姑娘家门口,扑通给殷姑娘跪下了。姑娘说,老爹你这是干什么?当爹的连连磕头,只求姑娘救儿子一命。姑娘说,我哪儿会救命,你儿子是得了绞肠痧,是吃了不洁净的东西。当爹的求姑娘手下留情,只要救儿子一命,要什么给什么,倾家荡产也行。姑娘没说话,到屋后揪了一把扁豆花,煮了,给儿子灌下,儿子到半夜病情便平息了。后来这个儿子就不走了,后来就成了大颤的爹。
老佘说,大颤说他妈根本没给他爹下什么蛊,是他爹看上他妈,故意使了个留下来的小心计,哪儿有什么绞肠痧,都是瞎掰。但是村里的人一直认为是殷姑娘在水里下了蛊,下蛊的手法很多,可以把蛊虫藏在指甲缝里,当面洗碗不过是个障眼法。
王安全说,扁豆花倒是用得很对,那是治疗肠炎解痉镇痛收敛的主药。
老佘说,山里女人懂得什么主药次药,野方子罢了。
王安全说,有时候野方子也能治大病。山野的事,常常让人说不准。
老佘说,可不说不准,这个二颤就是个来历不明的东西,他哥说了,他妈怀了他六个月就生了,生下来细长的一条,不会哭,就会嘶嘶地叫唤。
王安全说,怎么可能,六个月的胎儿根本就不能成活,他身上的许多器官还没发育完全。
老佘说,长虫蛋的孵化期是多长时间?六个月大概够了。
老佘指着殷娘娘像说,这座像就是照着二颤妈的样子塑的,塑像的是二颤的爹。
王安全就看那像,果然与见过的神像不同,隐约间透出了乡村妇女的风韵,除去那些凤冠霞帔,眉眼与大颤倒有些相像。王安全说,大颤、二颤一母同胞,性情竟是不一样。
老佘说,大颤是人,二颤是虫,虫怎么能跟人相比。二颤一落生,他娘没来得及看他一眼就咽了气,他是喝风饮露长起来的,禀性不同于常人,连他的哥哥大颤也摸不透他的脾气,二颤是长虫坪一怪。
王安全说,不是怪,是神智上有问题,大脑发育不全。
老佘说,二颤是长虫托生无疑,人们都说他身上长满了鳞,隔一段时间就要脱层皮,肚子上的刀痕是有目共睹的,那是取胆留下的痕迹。
王安全问老佘什么时候看过二颤的肚子,老佘用手比划说二颤睡觉的时候他看过,在右侧,长长的一条。
王安全问老佘怎么认识大颤的,老佘说他和大颤是战友,一块儿在新疆当过骑兵,友谊牢不可破。现在他在城里干餐饮,开酒楼,发了点小财,他也得让大颤发,要不怎么叫战友呢。王安全问怎么发,老佘说这是商业秘密。王安全说他是教书的,跟商业没搭葛,让老佘但说无妨。老佘这才向四周巡视了一遍,确认二颤真的不在,小声说,就地取材,逮蛇,蛇肉烹饪,蛇胆泡酒。
王安全说,一个长虫坪有多少长虫能取多少胆?
老佘说,长虫坪蛇胆固然有限,但是“长虫坪纯天然蝮蛇胆酒”牌子一打出去,就鸡鸭猪狗什么胆都可以弄来充数了,关键是头三脚必须得像回事,得货真价实。
王安全问这事可跟村里打了招呼,老佘说大颤知道就行了,再没必要跟其他人宣传,长虫坪的长虫是自然的,就像河里的石头山上的草,都是没主儿的东西,搬块石头难道还要跟村长打报告。王安全说这些东西生在长虫坪就和长虫坪有关系,就是到河里挖沙子还得给当地交自然资源费呢,没有白拿的事。老佘说事情从大夫嘴里一说就变得复杂化了,说王安全在山上到处挖药,是不是也该交资源管理费。王安全说性质不一样,他是为了教学,不是为赢利。老佘说,高调谁都会唱,现在办学校比哪个行业都赚钱,师道已经不再尊严了,教师也进入了经济市场,要是不赢利,投资办学的也不会蜂拥而起。
倒让王安全没了话。
五
半山有狗在吠,不大工夫草棵里钻出只细狗来,细狗的模样长得怪,瘦腿长脸细腰,丑陋无比。因为雨水,一身毛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像只正换毛的小鸡子。细狗是大颤养的,跟二颤也熟,常山上山下地蹿,有时跟着人来,有时也自己来。细狗很熟稔地在庙里转了几个圈,这儿嗅嗅,那儿瞅瞅,颇有视察派头。老佘跟在狗后头转,给狗吃鸡骨头,拍狗的马屁。
一会儿,松贵从山道攀上来,披着块塑料布,气喘吁吁的,说是来请王安全下山,长禄病了,病得不轻。王安全一听,赶紧收拾家伙,准备跟松贵下去。松贵喊来二颤,传达村长的话,让二颤别靠着西墙睡,说才下过雨,西边山墙说塌就塌。二颤很听话,当下把铺横过来,挪到神案下头,然后又把西边的东西依次搬过来。二颤搬东西的时候细狗就在二颤的腿间盘来绕去,故意捣乱,二颤也不恼,时不时地推狗一巴掌,狗就使劲儿摇尾巴。老佘说这是条名贵狗,产于梁山,有皇族血统,是狩猎撵兔高手,山外有细狗撵兔协会,隶属于体育界,年年进行比赛,冠军狗价值上万。老佘说着很爱惜地抚摸那狗,狗一闪身冲老佘一龇牙,“呜嗷”一声,吓得老佘蹦了个高,嘴里直说,这狗,这狗,怎是个这……我在大颤家吃了那些顿饭,喂了它多少腊肉它还是个生生。
王安全跟着松贵往外走,开玩笑地对老佘说老佘一定是属兔的,招得狗不待见。老佘说他是属老虎的,专跟狗斗。松贵说老佘应该跟长虫斗,龙虎斗才是真斗。老佘说他们南方有这道菜——龙虎斗,把猫跟长虫在一个锅里炖。
老佘见王安全要下去,也跟着一块儿下,他不愿意一个人和二颤呆着,说是跟那条长虫在一起厮混害怕。于是三个人就顺着精滑的山路往下走,细狗不下,细狗今天想留在山上跟二颤亲热亲热。
山很陡,松贵走在前面,不时地回身招呼王安全。王安全问长禄怎的病了,松贵说早起还好好的,喝了一大碗甜汤,吃了一块糍粑,要给孙子编草蚂蚱,低头揪马莲草,就歪下去了,抬进屋里,当下人就不行了。
王安全沉吟半晌说,麻烦。
松贵说,可不麻烦么,不麻烦也不会上山来请城里的专家。
王安全让松贵快些走,于是大家都加快了速度。
下山的路,不是松贵护持着,王安全得摔成泥猴,老佘在后头走得也很艰难,他边走边向草丛间寻睃,看见长虫便用带弯的铁棍喳地压住脖子,用两个指头捏住蛇头,容不得长虫挣扎就丢进了布口袋,速度之快,动作之熟练,让王安全吃惊。
松贵说,你逮它们干什么?
老佘说,我就爱逮它们。
进到村里,老佘口袋里大大小小已经装了不少,蛇们在袋子里不安分地蠕动,看着让人心里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