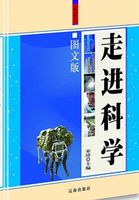儒对猎取野物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山坡上有嘎嘎鸡,竹林里有竹鼠,坟圈里有獾,麦田里有兔,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只要被他发现了,他决不会放过。儒逮野物的本领很强,无师自通,太婆说这是继承了他祖父的遗传,儒的祖父霍光地是搏熊馆村最出色的猎人,是人中的精英。祖父的枪法是百发百中的,祖父下的套子是永远不会落空的,尽管没像汉武帝那样一天打过三十只熊,祖父也徒手搏过金钱豹。祖父的死也是壮烈的,他在骆峪被一群豺狗掏空了肠子,抬回来的时候人还能说话,还能跟太婆开玩笑……没有了肚肠的人如此坦然,只有真正的猎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儒很敬重他的祖父,虽然他跟他的祖父在这个世界上连擦肩而过的机会也没有,但是祖父的精神魂魄却是深深地留在他的骨子里了。现在的搏熊馆,早已没了虎豹豺狼,因为打了农药的缘故,地里连兔子也很少见了。儒也很想让豺掏空了肚子,可他上哪儿去找它们呢,甭说豺,附近三四个村子,连只正经的狗也见不到了,巴儿狗倒是有不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农民都改养巴儿狗了。法的屋里也养了一只,塌鼻子突眼,脑袋上还扎一个小辫,见谁给谁摇尾巴,一副媚态。儒看见那狗就踢,看见就踢,那狗看见儒就跑,看见就跑。
儒想,搏熊馆这样的地方竟然出现了巴儿狗,羞先人哩。
太婆让儒去寻找法,儒不去,儒说他不想见五柞宫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巫婆。
太婆说,怎么是老巫婆,那是个正儿八经的出家人,你不待见她,不跟她说话就是了。
儒说,可她跟我说话呢。
太婆说,你不要找借口推,不去也得去。
儒不吭声,大口大口地吞他的鸟。
太婆说,你的鸟放些时候再吃,也亏不了什么。
儒说,凉了再吃就不是鸟了。
太婆一字一板地说,我告诉你,这天气,法娃上了五柞宫……
儒不接太婆的茬,歪着脑袋继续啃着那些麻雀,嘴上手上满是油,细小的骨头在他的嘴里发出嘎吧嘎吧的声响,很脆。太婆也很拗,她在孙子跟前站着,就是不动窝。儒拿眼瞄了一眼祖母,服软地笑了笑,将一串焦黄的小肉递了过来。
太婆气吭吭地说,我没有牙,你要咯死我吗!
儒告诉祖母五柞宫的后墙新近出了个洞,是獾干的,他一定要把那个家伙逮回来,弄个笼养着。
太婆说,逮它干什么,獾浑身上下除了油没别的,一股腥气,你要是真馋肉了我明日跟法娃要些钱,你到终南镇上割它五斤大肉,一次吃个够。
儒说,谁稀罕大肉,现在的猪都是激素催的,还要配上什么瘦肉精,本来大半年出栏,如今发展到两个月就进屠宰场,咱们不是吃猪肉,是在吃猪饲料呢。
太婆还要说什么,外面有人在喊,山水下来了……
儒一听,扔下他的乌,腾地蹿出了灶房,往渭河边奔去了。
每回搏熊馆闹天,渭河就小小地涨一次水,这水来自秦岭田峪、骆峪、埂峪、景峪、就峪几条峪口,水一出山,渭河便会水波荡漾几个时辰,届时,鱼也游了,鳖也冒了,小水鸭子也欢了,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但一切就像海市蜃楼一般,瞬间即逝,水来得快,干得也快,一眨眼,说没就没了。
太婆立在房檐下,看着头顶旋转的黑云而忧心忡忡,山水来得这般快捷,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回遇到的,这边还没有下,那边的水已经到了,不合规矩……
在这很没有规矩的时候,她的两个孙儿都在外头。
法到傍晚也没回来。
法的媳妇抱着孩子过来了两次,想的是让儒到五柞宫找找。儒偏偏的不在屋,吃饱了烤麻雀的儒从下午出去了就再没见人影。太婆很着急,她坐在门口骂,骂法和儒,说他们是畜牲托生的,她都这把年纪了还要为他们操心,她也是活够了,她明天就去死,接着太婆提出了十几种死的方法,在她的嘴里,每样死法都很精彩,都很有意思,都让人觉得值得一试……
太婆骂得很有韵律,像唱歌一样,几个小孩子吃过了晚饭,坐在旁边听太婆骂,这就更助长了太婆的威风,骂到后来,不但将身边几个小崽子捎带上,连村长、书记,包括前几日县上下来的调研员和收生猪的老赵也都捎带上了。骂来骂去早已忘了主题,压根没有法和儒什么事了,变作随心所欲,信口而来的评论。村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听,谁都知道这是九十多岁的老祖宗闷得慌了,在解心烦,败心火,当然也有倚老卖老的成分在其中。
半黑的时候孙媳妇给太婆端来一大碗苕子面,太婆就着一头紫皮蒜吃了,吃完抹抹嘴,接着骂,声调比原先又高了许多。
太婆骂几句喊两声,喊她的法和儒。
大月亮从东边升起来了,黄亮黄亮的,映着房脊,映着树梢,映出了门楼前太婆拄着棍的身影,一幅很温馨很幸福的景致。
村长披着衣裳踱过来说,婆,你也该歇歇了,不累么。
太婆说,你个死东西到现在才来,我这大半天骂的就是你,你就没听着?
村长说他早上到乡里开会,天黑才回来。
太婆说,一找你就拿开会说事,天知道你开的是什么会,哪天我跟你一块儿到乡上去,把你的会账好好对一对。
村长说这样最好,他早被没完没了的会弄烦了,下届村长就让太婆当,让太婆也过过会瘾。
太婆说,你别以为我当不了,一解放我当妇女会主任那会儿,把村里的男女老少管得齐齐整整的,那时候你那死鬼爷爷是个不折不扣的二流子,耍钱、打牌、抽大烟,坏事干全了;你大刚封上开裆裤,到处偷鸡摸狗拔蒜苗,不是个省油的灯,“文革”时候又追城里下来的女知青,拖家带口的人了还见天给人家大姑娘抱柴禾烧炕,亏得没追上,要不你得比现在还张狂;你娘每次上工回家都有“捎带”,开了几回会也不改,落下毛病了,你们家让我费了多少心呢……正说着,洋葡萄开着客货两用车从村街上过,见了村长和太婆,赶紧把车停了,蹦下车来打招呼。村长对洋葡萄说他现在正在收听“揭老底战斗队”的广播,洋葡萄来了,这个频道就该换换了。村长问了问洋葡萄今年的收成,洋葡萄说有万把斤,三四万的底是保住了。村长听了拍着洋葡萄的车说,他干革命工作的时候别人都致了富,他一想就不能平衡,有机会了他给洋葡萄去打工,说不定还能赶个发财的尾巴。
洋葡萄只是嘿嘿地笑。
太婆让村长帮她去找法,说法去了五柞宫。村长说法不是小孩子,丢不了。
太婆说,下午的时候皇上回来了。
村长说太婆迷信。太婆说她从来就不迷信,她科学得很呢,她知道西边的杨凌克隆出了两只一模一样的羊,就跟她的双生孙子一样,不同的是她的孙子是兄弟,那俩羊差着辈分。太婆说她不明白为什么要人工制造山羊,羊也用不着计划生育,尽可以随便生,科学家也是钱太多了,干点什么不好,冬天种出了茄子,春天收了洋芋,把个世界搞乱了不说,把她搞得也越发地糊涂,比五柞宫的老尼还糊涂。她现在年纪大了,没精神顾及农科城的山羊了,只好关心她的孙子,孙子于她是最重要的,要是谁趁她睡觉的工夫给她克隆出一打孙子来可怎么得了。
村长说,那多好啊,您能当班长了。
太婆说,你去给那十二个老爷们儿找媳妇吗?一个儒就够让我糟心的了。
扯了半天闲话,村长还是不想上五柞宫。村长说,黑灯瞎火的……
洋葡萄说他反正没什么事,可以替村长跑一趟,他把车开到山底下,用不了十分钟就上去了。村长就让洋葡萄去五柞宫看看,说有事到会计霍成社家里找他,他要跟成社商量点事,说罢背着手朝东去了。
太婆看着村长的背影说,商量什么事呀,别当我不明白,打牌罢了,你们这些干部啊,别的长进没有,牌是越打越精了,靠打牌能吃饭吗,能打出社会主义新天地来吗?
洋葡萄问太婆,法是什么时候走的?太婆说晌午饭前就上去了,又对洋葡萄说今天一变天,她的心就开始嘣嘣地跳,怕不好。
洋葡萄说,太婆你放心,什么事也没有。
洋葡萄走后,太婆没有回屋,她在门口的石鼓上坐着,朝着五柞宫那边使劲望。南边山林黑沉沉一片,望不出所以然,几只白色的鹭鸟,在月光下突地飞起来,又落下去,不知哪儿来的一阵风,将那片松林刮得呼呼响,风停了,一切又归于寂静。近处,谁家的小孩子在夜哭,一只猫,从房脊上蹿过去了……
太婆在门外坐到半夜,露水下来了才进屋。
儒在渭河边激动地徘徊。
渭河的水涨了,又很快退了,退下去的水在主流南侧形成了狭长的一个水洼,长有两里,宽不过一丈,乍看水也大也深,其实是一片不流的死水。经过沉淀的水洼清澈而沉静,在河道里摊着,深处透出了即将消失的无奈和被停滞的忧伤。这道不引人注目的水引起了儒的注意,凭着猎人的敏锐,他感到了它的与众不同,无风的水面,时时地泛起一阵阵微波,波纹有时从东向西,有时从西向东,来回荡漾,极有规律。儒在岸上向水里搜寻,终于他看见了一条鱼在水洼里游动,在不动声色地寻找着出路。静谧的水底,那条鱼好像一道黑色的闪光,游到东面,一个优美的转身,再游到西面,一次次地重复,一次次地重复,没有停歇。水无声,鱼无声,无声的水和鱼传达出了一种焦躁,一种恐怖逼近的绝望,就像关在笼子里的狼。
儒从没见过这样的鱼。
鱼很大,头有点儿扁,身体匀称,披着大片的黑鳞,鱼尾处有些微微泛红。这是一条什么鱼,它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出现在渭河,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儒想也没想,儒关注的是这条黑鱼的处境和它即将变为他手中猎物的事实。对狩猎者来说,生擒一个鲜活的生灵,不在于结果和价值,而在于过程和设计,无论是美丽动人的金钱豹还是毫无用处的小黄鼠,都是一样的。儒观察着黑鱼,随着鱼儿来回奔走,鱼向东他向东,鱼向西他向西,很快他明白了,水洼还有一些深度,黑鱼暂时还存在着一方天地,明天大太阳一照,加上干枯河床的渗漏,水洼很快会变浅,黑鱼势必浮出水面,到那时一切都是唾手可得的了。
儒只需等待,时间就是一张无形的大网。
一想到抱着大鱼进村的情景,儒兴奋得连气也喘不匀了。
月亮升到了头顶,儒眼前的河滩和身后的山林一片光明,天光很亮,儒在河边坐着,抽着劣质的卷烟,听着汩汩的水声,脑海里一阵阵发懵,好像是在做梦,他感到自己不是活在现实,而是活在以前的什么时代,比他的掏空了肚肠的祖父还要早。在搏熊馆这个满是英雄和鲜血的地方,他待了很久很久了,哪年哪月,他就在河边坐过,那情景和现在一模一样……儒似乎看到了结局,有关他的结局,一个很幸福很完满的结局。黑鱼在月光下游动,儒透过水面可以看到它光亮俊美的脊背和灵活有力的尾鳍,哗地一闪,哗地又一闪,黑鱼游动的频率在加快,也就是说水洼的面积在缩小,偶尔地,鱼还在水面翻起个小小的水花,“噗”地一声,像吹了一口气。
儒下到河滩,站在水洼跟前,以便更加清楚地看到水里的鱼。儒试了试水的温度,水洼的温度明显地高于主流,他的心里有底了。儒在主流一侧弯腰撩水的时候,发现那边水里也有一条同样的鱼在翻卷,那条比水洼里这个似乎更大,更壮硕。
主流里的黑鱼和水洼里的黑鱼在同步游动,它们共同朝东又共同朝西,露出的滩将它们隔开,使它们无可奈何。儒扔掉了手里的烟,叉着腰站在两条鱼当间,看看这条,再看看那条,把他们一次次地加以比较,最后得出结论,除了个头不一样以外,它们应该属于同一个种类。河里那条鱼也看见了他,一个翻转将身子沉了下去,再不露面。儒知道,主流河床,北通甘肃乌鼠山,南达风凌渡入黄河,长数百数千里,那条鱼的天地广阔得很呢,自己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逮不到它。
天快亮,儒回家拿了一趟家什,他看到法的屋里还亮着灯,他搞不懂法这个家伙这个时候怎么不睡觉。
法的确没有睡,他靠在被垛上,正惊魂未定地大口喘气,媳妇用湿手巾给他抠鼻子和耳朵里的土,已经换了几盆水了,还没抠干净。法一口一口地唾着,唾出的都是黄泥,把屋里搞得一股腥腥的生土味。炕沿下,一双沾满了泥的解放鞋旁边撂着一个鸭蛋型的面目狰狞的大陶罐,这是法在五柞宫冯公冢里折腾一整天挖掘出的“宝贝”。
法是下半夜被洋葡萄用车拉回来的,洋葡萄说冯公冢的墓塌了,法被闷在墓道中间,他费了好大劲才把法挖出来。不是听了太婆的话,他怎么也想不到里面还会有人,真是玄极了。法的媳妇一听,眼泪刷刷地流,千恩万谢地说了不少感谢的话,差点没给洋葡萄跪下。洋葡萄说别谢他,应该谢太婆,太婆的感觉真灵,他要是再晚到一会儿,法就是另一回事了。法的媳妇忙着点灶要给累了大半宿的洋葡萄烧甜汤喝,洋葡萄却急着要走,说是明天一大早要到咸阳机场赶飞机,葡萄眼瞅着就下来了,他在上海的客户还没有落实,上海那地方是个大市场,晚去一步就被人抢了。媳妇又让喝水,洋葡萄水也不喝。
法的肋间差了气,一喘气就疼。一喘气就疼,偏偏的,法还要喘气。
洋葡萄临走告诉法的媳妇,天亮一定要带法到医院看一下,要是没有车可以用他的客货两用,他的员工小施也会开。
洋葡萄走后,媳妇给法沏了一碗糖水,法喝下去了才感到好些,闭着眼睛不住地哼哼。媳妇埋怨法不该去碰那座坟,说千百年来没人动自有没人动的道理,出了这样的事,听着都让人后怕。法哼哼叽叽地说即便他不碰也会有人碰,他是看到东墙根被挖出了个洞,才下决心动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