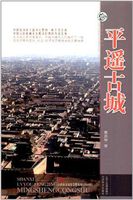我们也都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开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见敌国的居民呢。在路上,当我听见空空如也的山村传来雄鸡的啼鸣,当我看见被战士们解开缰绳的水牛在安闲地吃草和散步,看见路边的桔子树上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的时候,我就想:假如躲在山上的越南群众肯回来看上一眼,他们对我军传单上申明的一切就容易理解了。现在,你看这几位老人的笑容象无云的天空一样晴朗,完全没有恐惧、疑虑或是屈从、谄媚的影子,乍一看,就象我们国内的老大爷在路边迎接野营拉练的队伍似的。他们的笑容是一面镜子,它能反射出中国军队两天来留下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大家草草吃了一点干粮,就各忙各的去了。我们跟上做群众工作的一路,回头来访问这座在地图上时过无数次的小镇。我们了解到,这条街总共有二百多户人家,除了少数农户和官员家属而外,大部分以经营手工业和小买卖为生。其中有四十多户华侨,凡留下的,都在近两年加入越南籍了。县医院旁边有一间“中华会馆”,墙壁已斑驳残旧,里面堆放着一些积满灰尘的条桌和长凳,其冷落凋零的局面,正与当局迫害、歧视下侨民们的处境相似。但它与侨民们同样是无辜的,门旁那一副被青苔剁蚀的对子:“越都过国来此地共叙乡情,隆梓兴桑登斯堂必恭敬主。”表示了我国侨民安分守法的态度。
在百货商店旁边的一幢房子里,我们访问了一位六十八岁的华侨老人。他租籍广西,过来已经五代了。早年以伐木为生,识得一些草药,略通医道,晚年便成了他糊口的生业。老人一边整理他的药材,一边告诉我们,他老伴和三个孩子都上山了,公安逼着走,不走不行,他自己腿脚不好,偷偷躲在防空洞里了。他说他不懂也不敢过问国家的事,但是他说,一九七四年以前和中国友好,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每月口粮是十六公斤。现在不和中国好了,每月口粮是十公斤,其中一半是玉米。烟、酒等日用品也没有了,只有干部才能得到。一架单车,卖给干部是二百多元(越币),他们一倒手,上了黑市,卖给老百姓就得七百多元。政府总说苏联好,肯帮助我们,可是除了门口贴的苏联纸旗和商店里的黄头发塑料娃娃,什么东西也没看见。
现在家里的用具都还是七四年以前的。他一提醒,我们才留心这小小厅堂的摆设。只见一套茶具,是景德镇的瓷器;铁壳热水瓶是“西湖”牌的;倒扣在空酒壶上的玻璃酒杯虽然没有中国标记,但我认出,它和我家里用的是一模一样。这些小小物件虽然微不足道,可它证明,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已通过无数的毛细血管渗透到越南人民的生活中,黎笋集团纵有造谣的天才,想抹掉它也是不容易的。
离开老人的家,但见街上又有一些部队和支前民工开上来了,纷纷坐在路旁喝水、休息。政治部的同志办事利落而又周到,已在街口立了两块大黑板,一边写着:“同志们,辛苦了,保卫祖国边疆立功劳!”一边写着:“部队和民工同志们,遵守纪律,勿入民房。”为了防止后来的部队分不清机关和民房,他们在所有民房的门上都贴了写着“禁人民宅”字样的封条。商店和仓库都派了岗哨,等侯统一清点和处理。
政治部的杨管理员也展开了他的工作,正提着缴获的半口袋硬币,四处张罗着买点青菜为大家“改善”一下。
可是他困难很大:小小县城既无菜店,也无菜园。居民们门前虽然种了一些,可是主人不在,提着钱袋寻不见卖主。
最后经请示,决定用粮食换一点。就这样,他请翻译写了张条子,压在二三十斤大米下面,然后割了十几斤青菜提走了。
中午,我们回到驻地,看见门前有一群入围着什么吵着骂着。近前一看,原来是一袋从敌人仓库里缴获的大米,邪麻袋是翻过来用的,打开一看,里面印着四个大字:中国大米!
不会儿,清查敌人军火仓库的同志也回来了,在这里共缴获重机枪四十四挺,步枪、冲锋枪三百余支,地雷五百个,六〇炮弹七十三箱等一大批弹药。其中不少是我国当年援助的!
中午这顿带菜叶子的大米稀饭本来十分难得,可还是压不住大家肚子里的火气,边吃边骂着越南当局背信弃义。
和这样的敌人打仗,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回头再想想我们的战士,忍着一路战斗跋涉的劳苦,宁愿顶着太阳坐在路边,披着露水宿在草坪,也不动一动民房,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
离开东溪以后,我们又到过省会高平和几个县城,但总是忘不了东溪的一切。那里后来成了我军的临时战勤基地,前运的大批弹药、给养和后送的俘虏、伤员,都从那里经过。我们的工兵战士还修好了几台打米机,把从当地国库缴获的稻谷加工成米,直接运往前线。撤退之前,有几位记者又到东溪去了一趟,他们带回的消息说:那里虽然有大批人马经过,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秩序。驻东溪的部队、医院和俘转站撤退之前,又对全城进行了一次大扫除。考虑到群众回来后缺粮吃,他们在每家都留了一些大米和盐巴,后来觉得米太少,又给每家添了一些稻谷。
“老百姓回来了没有呢?”我在东溪时,就听一位老人念叨,他的老伴和孩子走时都没带衣服,这几天在山上可受苦了。早知道中国军队是这样,何必上山去受罪。-那时距现在已二十多天了。
“回是回来了一些,但是……”接着,他们告诉我一个令人发指的惨剧。那是在东溪附近的一个山村,有一天,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回家来拿东西,被我战士看见了。他们给她一些吃的,告诉她我军不杀老百姓,也不要你们的东西,让她回去告诉爸爸妈妈不要怕。小女孩回家一看,果然,东西一样没少。第二天,她就把全家八口都从山洞里领回来了。爸爸郑春碧是个砖瓦工人,抗法战争时期在我广西边境一带打过游击。他说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军队会杀老百姓,要杀哪用等到今天!十七日早晨,全村老少往山上跑的时候,中国的坦克就在他们屁股后头,坦克兵怕轧着他们,还伸出头来直摆手,让他们躲开点呢!可是政府头头和公安不让下山,也不许说这样的话。
郑春碧下山后第三天的傍晚,全家正在吃饭,突然门被踹开了,两名越公安把住门口,二话不说,端起冲锋枪就扫。郑春碧刚往床下钻,屁股上已中了两弹。等越公安仓惶逃走,他往外爬的时候,听见三岁的小女儿在叫他:
“爸爸,我的身上有血……”他流着泪说:“孩子,你忍一忍,爸爸去找中国叔叔来救你!”他爬到我军的驻地,战士们火速赶来,见他的妻子和六个女儿已全部惨死在血泊中。
后来,郑春碧含着满腔悲愤,给部队,给下山来的越南群众和俘转站的俘虏,讲他一家的遭遇,连几个俘虏也听得流泪了。
就在我听到这个故事的第二天,郑春碧被送往我后方医院治伤,途经我们驻地的时候,我见到了他。这位四十九岁的老工人已经没有哀伤,恨火把他的脸庞熔铸得更加棱角分明,目光咄咄逼人。他说:真没想到他们会下这样的毒手。我有什么罪?我的孩子有什么罪?现在我没有别的报仇手段,我只好跟你们到中国去。可是如果你们有困难,我也愿意留下。我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可是我用七条命换来的真理,不能白白地烂在肚子里,我要告诉所有从山上下来的人;我的一家是谁打死的!
1979年2-3月,断续于行军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