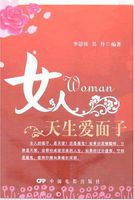从小筱无比郑重地告诉我,这是我崭新的生活开始的那一刻,我开始了解到,某些发生过的事情注定会被人遗忘掉,而遗忘它的最好方式,就是没有人再向你提起这些事情的任何细枝末节。当时间已经腐朽到了可以令事情糜烂在记忆里的时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包括曾经是否出现过的人,和说过的话,我都将不再记得,也没有人会记得。
不知道小筱从哪里买回来的猫,全身黑色的毛,一个月大的小猫窝在她怀里,用它怯生的眼睛望着我。我过去抱着它,脱口而出一个名字,小若。
啪嗒。杂志从小筱手中掉下来砸在茶几上,猫被吓的忙缩回我怀里。怎么了,小筱。
呃,没事没事。她捡起杂志重新放好,然后问我,你叫它什么?
小若啊。
呵呵,听起来像是人名呢。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想这么叫它。小若,小若。我专注地看着猫,忽略了一旁小筱的表情。
我说,小若这名字很有亲切感,是不是,小筱。她极力点头同意,然后去厨房煮牛奶。
自从出院以后,我似乎对很多东西有感觉到亲切,这房子里的一切,或者是在大街上看到的某些东西,以及小若这个名字,都让我倍感亲切。我猜想这些东西是否曾经出现过我的生命中,或许是我对事物的依赖更加明显了。毕竟一个二十岁的女子现在要面对的是自己一无所知的过去,而且在黑暗中需要独自来对抗恐惧的降临。我只能承认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因为我实在是没办法回忆起那些东西。比如小筱说我以前常写写文字,我高中退学,我在几年前就开始写点东西赚钱了,我喜欢泡在一些网络BBS上,我总是结交很多论坛上的朋友,我的生活黑白颠倒着昼夜不分。对于她告诉我的这些事物,我总是表示深信不疑的态度,我相信她,因为我知道她很爱我,她所做的都是为我好。
某天下午,小筱从学校里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宜昌的冬天是看不见雪的,我们可以去她出生的古镇住段时间。雪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陌生的事物,所以我想我会喜欢它的。很快,小筱请好了假期,准备了去古镇的车票。她整理着我们的行李,大量保暖的衣物,生活用品,以及很多药物。我提议带上小若,以免她一个留在屋子里。
古镇是小筱出生的地方,那里是个无人打扰的小城镇,人们极其和谐的生活在那里。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入了冬,我抱着小若坐在大巴上,窗外的景色渐渐脱离了城市的冷漠,乡土风情已显现出来。大片的田地,以及远处的山脉连绵不绝。
漫山的红色枫树叶遍及整个山头,笼罩了一片又一片的视线。已经收割了的玉米地被切割整齐,有的被集体烧掉,有的还剩下枯黄的枝杆在勉强支撑着。道路两旁匆闪而过的一排排桐树依旧耸立在此,叶子依旧青绿。偶尔有几颗小白杨,还能够看见鸟窝的枝头显得格外凄凉。小筱一直在向我描述这些景色,包括那远处的天空,已经流走的云,和仓皇而过的候鸟。
三个钟头后,我们到达古镇的村口,下车后风直往我的大衣里灌,空气冰冷但是清凉透彻。我们顺着石板小路朝镇里走去,沿路的两旁开满了野菊花,各种色彩交织着。它们迎风摇曳着弱小的身体,很是努力地仰起脸,如同非洲菊般的花盘向我展示着它的美好。我仔细看着这些在路边极力生长的植物,直到风把它们吹的无法站立。小筱提着大包的行李走在前面,大风把她的大衣吹的鼓起来,如同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
石板小路阡陌蜿蜒,两旁古老的房屋看上去有上百年的历史,墙壁上遗留着班驳的岁月痕迹,枯黄的爬山虎部满了灰黄色的墙壁,然后垂沿下来。小筱的家在这里还有一间房子,两层楼的格局,完全的木制小阁楼,古老的红木制作的大门上挂着古铜色大锁,小筱打开门,然后我看到黑暗的大厅,以及里面滚滚而来的潮湿而阴暗的空气。常年不见阳光的屋子总避免不了有一种潮气,我怀里的小若开始叫起来,可能是冰冷的空气让她感觉到不安。我抱着她慢慢走在楼梯上,全木制的小楼梯,踏在上面发出吱嘎的声响,扶手很光滑,似乎可以看到木头的纹路。
楼上的两排房间,一排朝南,一排朝北,里面的格局大多一样。窗帘布都是蓝白相间手工印花的料子,摸在手里着实有亲切的触感,这同样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古色古香的房子,无论是床或衣橱,还是桌子椅子,其它的东西,大多数都是以红木或者檀木为材料制作的。梳妆镜前的玻璃略带暗黄,抽屉上的把手有着精致的雕花。当我下楼的时候小筱已经在大厅升好了火盆,大大的金属火盆中燃烧着木炭,空气一下子变的温润起来。我把小若放在火盆边,她很乖巧地缩在一旁取暖。我说,小筱,古镇真的会下雪吗。
嗯,每年的这个时候就会下很大的雪,有时候连西边的西凉河都会结冰。大概再过一两天这里就应该会下雪了。她从厨房找出水壶,乘满了水放在一旁的煤炉上加热。木炭燃烧时发出一些轻微暴烈的声响,偶尔惊动了小若的休憩,它会忽然睁着眼望着跳动的火焰,伸出前爪想要去抓。小若啊小若,每当我唤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一种无力的挣扎,在心里慢慢纠缠着。似乎是在一座孤单无助的虚无城堡中求救的声音,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个晚上的古镇异常寒冷,至少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冷。我卷缩在被子里抱着小若,冰凉的身体一直无法安然入睡,只有小若的身体有一丝的温度,在胸口可以感觉到勉强的体温,那么微弱的温度。半夜里,我终于抑制不住寒冷,穿上大衣坐在床上抽烟。黑暗中我的烟头一直在闪烁,烟雾瞬间弥漫开来,我的嘴唇在发抖,然后我在想,以前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出院之后妈妈问我需不需要手机时,我反问她,我用手机给谁打电话呢?那个时候我是绝望的,她们并不能够了解到我在心里无尽的恐慌,她们总是希望我将过去的事情抹掉,希望我不再记得也不要提起。可是,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够问,不能够了解自己的过去,我如同被忽然洗掉了声音的磁带,卡在那里,无法前进,更加无法后退。只是她们并不知道,她们愈是隐藏,我就愈想要了解。她们是否能够了解,失去了一切过去的我有多么绝望,这样的我又有什么资格继续存活下去。我很害怕这种一无所知的空白和黑暗,我甚至感觉自己丧失了生存下去的权利和能力。
我的生活瞬间失去了一切颜色,在我某天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被颠覆的物是人非。我找不到丝毫的线索,无论是在哪里,公寓里没有任何以前的痕迹,在我出院之前所有与过去有关的东西已经被她们藏了起来,甚至是电脑的文档里,也是完整的空白,小筱不是说过,我靠文字为生,可是为什么我找不到以前的文字,甚至是日记,书信,全部都被删除的一干二净。这就是我突然被人扼杀的记忆,被人掐断了脖子的记忆。
想的太多了,头开始疼。窗外慢慢透进一些光来,天就快亮了。我穿好衣服走到窗前,撩开窗帘的一角,看到的是一个令我惊颤的世界。白,所有事物都是白色的,远出的房顶,街道,路边的大石头,田地,一切的一切全部变成白色。窗台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雪,空中还有片片雪花飘落着,我打开窗户,并没有风吹进来。这个世界真美好,这一刻我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