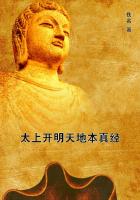诗曰:
春到迷楼亦太浓,锦香绣月万千重;
笑他金谷能多大,羞杀巫山只几峰。
屏鉴照来真富贵,车帷度去实从容;
只愁云雨遭兵火,若个佳人留得侬。
话说炀帝与道人赌游迷楼,叫道人与道姑走在前面,自家坐了转关车,紧紧随着。其余宫人内相,俱跟在后头,不许人人开口。那道人对炀帝打一个稽首说道:“贫道告唐突了。”遂用手携定道姑,二人逍逍遥遥,信着步子儿往里便走。却也作怪,就像走过几千万遍一般,四下里都是透熟,逢着转弯便转弯;遇着抹角便抹角,该上楼就上楼,该登阁就登阁;门关着,他竟用手推开;屏拦着,他便侧身转入。无一个幽微曲折之处,不被他串到;无一层锦闱绣闼之中,不被他游来。不多时,将一座夸大宫诧仙府的迷楼,早已团团游遍,不曾遗了一处,仍旧转到殿上来说道:“陛下还有什么幽房邃室,乞再赐贫道一游。”炀帝惊得呆了半晌,不能答应。正是:
世间那有迷人物,原是疾人自着迷;
试看神仙迷不得,迷楼何似武陵溪。
炀帝见二人有些奇异,因惊问道:“你二人姓甚名谁?”道人笑道:“俺们道人家,草木形骸,那有什么姓字?”炀帝道:“姓字既无,必有一个乡贯住坐。”道人道:“天上的白云,山中的野鹤,便是俺们的乡贯住所了。”炀帝道:“既如此无个定纵,朕盖一所庵观与你住好么?”道人笑道:“好便好,只恐怕不长远些。”炀帝道:“朕钦赐盖的,你便好徒子徒孙终身受用,如此不长远?”道人笑道:“陛下怎么等得这等长远,此时天下还有谁来盖观?
就有人来,只怕陛下也等不得了。倒不如随俺两个道人,到深山中去出了家,还救得这条性命。”炀帝笑道:“这道人为何一会儿就疯起来!朕一个万乘天子,放着这样锦绣窠巢,倒不受用,却随着两个山僻道人去出家,好笑!好笑!”道人道:“陛下不要太认真了,这些蛾眉皓齿,不过是一堆白骨;这些雕梁画栋,不过是后日烧火的干柴;这些丝竹管弦,不过是借办来应用的公器,有何好恋之处?况陛下的光景,月已斜了,钟已敲了,鸡已唱了,没多些好天良夜,趁早醒悟,跟俺们出了家,还省得到头来一段丑态。若只管贪恋火坑,日寻死路,只恐怕一声锣鼓住了,傀儡要下场去,那时节却怎生区处?”炀帝笑道:“这一篇话儿,人都会说,说来倒也中听,只是天地间,那有个不死的仙方,长生的妙药?你只看秦始皇、汉武帝,何等好神仙,到头来毫厘无用,这便是个样子。”道人道:“秦始皇错用了徐福、汉武帝偏信了文成五利,故没有功效。俺二人却非其类,陛下不要当面错过,后来追悔。”
炀帝笑道:“朕这里琼宫瑶室便是仙家,奇花异草便是仙景,丝竹管弦又有仙乐,粉香色嫩又有仙姬。朕游幸其中,已明明是一个真神仙,你们山野之中,就多活得几岁年纪,然身不知有锦绣,耳不知有五音,目不知有美色,却与朽木枯石何异?”道人笑道:“山中倒也颇不寂寞,只怕陛下没有造化去游。若肯随俺回去出了家,管你受用不尽。”炀帝道:“你且说山中有何景界,朕就没造化去游?”道人笑道:“是陛下也不知,待贫道略说一二:
居住的是瑶宫紫府,出入的是碧落玄穹,吃几碗胡麻饭,怕的是疱凤烹龙;饮几杯紫琼浆,爱的是交梨火枣。穿一件云霞百补衣,冬不寒,夏不暖,春秋恰好。戴一顶日有九华巾,风不增,花不减,雪月相宜。霓裳羽衣,常奏于不谢花前;小玉双成,时伴在长春帐里。要游时,白云为车,天风作御,一霎儿苍梧北海;要睡时,高天为衾,大地作席,顷刻间往古来今。那计是非,并无荣辱。羞他世上,马牛不识死生,谁知寿夭,笑煞人间短命。”
炀帝听了呵呵大笑道:“纯是一派胡言!其余还一时考校不出,你既说天风为御,白云为车,为何两只草履都走穿了?”道人道:“因要劝陛下出家,故信步而来。陛下既不省悟,贫道只得去了,只怕明日白龙围远之时,好苦楚也!”说罢,向天叫一声:“彩云何在?”忽见半空中悠悠漾漾飞下两片云来,炫然五色,道人与道姑走在上面说道:“陛下请了!日后火起时,思想贫道,只怕迟了。”炀帝慌走下殿来,刹时那两片云彩,早已飘然腾空而起,渐入云霄,倏忽之间,就不见了。正是:
神仙到处皆游戏,只恨凡夫认未真;
金马滑稽翻不信,文成五利转相亲。
炀帝见二仙乘彩云而去,又惊又喜,又有几分追悔。因对众美人说道:“大奇!大奇!不知他是两个真仙,倒是朕当面错过。”袁宝儿说道:“便不错过,却也无益。”炀帝道:“为何无益?”袁宝儿道:“他要万岁随他去出家。万岁肯舍下这些繁华富贵,向深山穷谷中,粗衣淡饭去修心炼性么?”炀帝笑道:“修炼实难,繁华富贵却也舍他不得,只好送朕一丸丹药吃了,做个现成仙人,依旧同你们在宫中受用方妙。”众美人一齐笑起说道:“万岁便说得这等容易,不修不炼或者还可,只是天下那有个好色欲的仙人。”炀帝笑道:“若好不得色欲,则仙人苦于凡人多矣!早是放了他去,不曾被他误了,弄做个一家货的神仙。”说罢,大家都笑做一团。笑了一会,炀帝仍旧上了转关车儿,推入迷楼中去。正是:
肉可销魂骨可怜,人生只恐不当前;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炀帝进了楼,也不管到何处,任着车儿推去。推到一层绣闼之内,只见几种幽低,低压着一带绿纱窗儿,十分清幽有趣。炀帝认得叫做俏语窗,窗下忽见一个幼女在那里煎茶,炀帝看见便下了车儿,走到窗下坐了。那幼女真个乖巧,便慌忙取一只碧玉瓯子,香喷喷斟了一瓯龙团新茗,将一只尖的纤手,捧了送与炀帝。炀帝接了茶,将幼女仔细一看,只见他生得莺雏燕娇,柳柔花嫩,袅袅婷婷,只好十二三岁。又且眉新画月,髻乍拖云,一种孩子风情,更可人意。炀帝看了,早有几分把捉不定,因问道:“你今的十几岁?叫什么名字?”
幼女答道:“小婢今年一十三岁,小名叫做月宾。”炀帝笑道:“好一个月宾!朕今日与你做一个月主何如?”月宾虽然年小,却是吴下人,十分伶俐。见炀帝调他,便微微笑答道:
“万岁若做月主,小婢焉敢当宾?只情愿做个小星罢。”炀帝说道:“做了小星,便要为云为雨,只怕禁当不起!”月宾道:“云雨虽则难当,雨露却易消受。”炀帝见他应答甚巧,喜得心花都开,遂一把将他搂在怀中说道:“你还是个小女孩子,便晓得这般戏谑,真可爱也!”一时高兴,便有个要幸月宾之意;又虑他年纪甚小,恐难胜大任,心下尚恍恍惚惚,遂叫取酒来吃,左右忙排上宴来。炀帝不放月宾下怀,就将他搂在膝上坐了,靠着脸儿同饮。炀帝吃了几杯问道:“这绣闼中,只你一个在此,还有别人?”月宾道:“只小婢一人,再无别个。”炀帝笑道:“亏你一个,倒不骇怕。”月宾笑道:“就骇怕也没法奈何,谁人肯来相伴?”炀帝笑道:“朕今夜相伴你何如?”月宾道:“万岁相伴的人多,正好轮不到小婢,小婢也没有这样造化。”炀帝满肚皮要幸月宾,只愁处幼惧怯。不期他全不在心,言来语去,转挑拨炀帝。炀帝喜不自胜,又笑说道:“你要造化,却也不难,但不知到临期是造化是晦气?”月宾笑道:“万岁只管讲他怎的,且请吃酒。”随斟了一杯,奉与炀帝。炀帝吃了半杯,剩半杯递与月宾说道:“你不吃,单叫朕吃,有些甚趣?”月宾笑笑吃了,又斟了一杯奉与炀帝说道:“这一杯却不单了。”炀帝笑道:“你也吃一杯才算不单。”二人说说笑笑倒吃得十分有兴。正是:
莫言野马难收辔,缚束鲲鹏只藕丝;
小小宫娃才一笑,九重天子已情痴。
二人欢饮多时,不觉天色昏黑,左右慌忙掌了灯来,把琐窗闭上。炀帝被月宾脂香粉嫩,在怀中偎倚了半日,情兴荡漾已久,再吃到醺酣之际,一发把持不定,抱了月宾,低低说道:
“朕醉了,同去睡罢!”月宾孩子家,只要勾引君王,不知道风流的苦处。见炀帝调他,便含笑说道:“这里睡不打紧,只怕误了万岁别处的好受用?”炀帝笑道:“这里的受用,难道不好?”遂不吃酒,走起身携了月宾,竟进寝房去睡。众宫女见炀帝注意月宾,寝房中早将鸳衾象枕,打点的端端正正。炀帝到了房中,便解衣就寝。月宾要君宠幸,口里虽十分承应,然终是女孩儿家,及到临寝,叫他解衣,忽不觉羞涩起来,倚着床帏,半晌动移不得。
炀帝情兴勃勃,连催数遍,只是延捱不肯脱衣。炀帝欲火如焚,那里等得他来,遂探起身子,把月宾扯到枕边,替他将衣带松开,轻轻脱去,银烛下露出如雪一般的身躯。月宾一发害羞,倒慌忙往被里一钻。炀帝因等待的兴浓情急,月宾上得来时,也没工夫温存调戏,便在意狂逞起来。不想用力太猛,月宾还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如何禁当得起,忽大声啼哭起来。
炀帝听不进,连忙把身躯往上一松,鸳被上早溅了无数的淫秽,月宾痛楚欲死,得这一松,连忙背过身子,朝着床里曲做一团,咬牙啮齿的呻吟。炀帝见月宾这般模样,心下甚是怜惜,不舍得再来强他。然香温玉软,抱在怀中,一腔欲火,却又按纳不下,只得再三婉转,要月宾转过身来。月宾就像怕老虎的一般,听见叫他,吓得魂魄俱无,那里敢动一动。炀帝叫的缓些,月宾声也不做,若是叫得急了,月宾只叫:“万岁可怜罢!”若将手去扯他时,月宾便号号的哭将起来。炀帝没法奈何,欲要以力强他,却又不忍;欲要让他睡了,却又难熬。
在他身上抚摩一会,又在他耳根边,甜言美语的央及半晌,月宾只是骇怕,不敢应承。急得个炀帝翻过来,覆过去,左不是,右不是,十分难过。捱了半夜,情兴愈急,便顾不得怜香惜玉,只得使起势来,将身子欠起,用力强去拔他。月宾见炀帝性起,慌做一团,又不敢十分推拒,又其实痛楚难胜,慌得只是栗栗而战。炀帝虽是用力,然终有爱惜之心,被他东撑西抵,毕竟不得畅意,又缠了半晌,不觉精神困倦,忽然睡去。正是:
猛经风雨花魂碎,虚抱芳香蝶梦痴;
欲避不能侵不得,快活时是可怜时。
月宾见炀帝睡了,心才放下。又怕醒来缠他,不敢十分睡着,只朦朦胧胧的捱了一夜。到了次早,日影儿才照上窗纱,便悄悄的走了起来,穿上衣服,也不敢走远,就在锦幔里面立了。炀帝一觉醒来,余兴未已,还有个找零之意,忙向被窝中一摸,早已不见了月宾。急探起身来看时,只见月宾不言不语的立在旁边。炀帝见了,又好恼,又好笑,便假假的嗔说道:“你这小妮子好大胆,也不等朕睡醒,就先走了起去,既是这样害怕,昨日谁叫你那般应承?”月宾低低说道:“小婢自知万死,然情非得已,只望万岁饶恕。”一边说,一边就跪了下去。炀帝本是爱他,又见他这般模样,更觉可怜,连忙穿了衣服,走下床来,将月宾挽起说道:“昨夜之事,就依你饶了,今夜若再如此,便饶你不得。”月宾道:“万岁肯饶,除非饶了今夜,若只是昨夜,便不要万岁饶了。”炀帝笑道:“饶了你便要弄嘴。”二人说笑了半晌,方同到镜台前去梳洗。梳洗毕,左右进上早膳,炀帝就叫月宾同吃,刚吃完了,忽一个太监来报道:“前日献转关车的何稠又来献车,现在宫外等旨。”炀帝听了,即到大殿上来见何稠。何稠朝过炀帝,随献上一驾小车,四围都是锦帏绣幔,底下都是玉毂金轮。
炀帝看了,便问道:“此车制造得精工小巧,到也美观,不知有何妙处?”何稠道:“此车无他妙处,只得行幸童女最便。”炀帝正没法奈何月宾,听见说幸童女最便,不觉满心欢喜,便立起身走下殿来问道:“幸童女有何便处?”何稠道:“此车虽小,却是内外两层,要幸童女,只消将车儿推动,上下两旁便有暗机,碍其手足,毫不能动。又且天然自动,全不费行幸之力。”遂将手一一指示与炀帝看。炀帝看了大喜道:“卿之巧思,一何神妙若此!”因问道:“此车何名?”何稠道:“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望万岁钦赐一名。”炀帝道:“卿既任意而造,朕复任意而乐,就取名叫做任意车罢。”随传旨照项升一样,也赐何稠五品官职,以酬其劳,何稠谢恩退出不题。
却说炀帝得了此车,快不可言,那里等得到晚,随即推到绣闼来,哄月宾说道:“何稠献一小车,到也精致可爱,朕同你坐了到各处去闲耍。”月宾不知是计,随走上车儿,炀帝忙叫一个内相推了去游。那车儿真制得巧妙,才一推动,早有许多金勾玉轴,将月宾的手足紧紧拦住。炀帝看了笑道:“有趣有趣,今日不怕你走上天矣!”随将手来解衣,月宾先犹不知,见炀帝来解衣,忙彻手去搪,那里动得一毫,方才慌起来,说道:“不好了!侬是死矣!”
炀帝见月宾惊慌无措,更觉快畅,那里顾他死活,解了衣服,便恣意去寻花觅蕊。痛得月宾娇喘不递,浑身上香汗沾沾,真是笑不得,哭不得,气嘘嘘只叫万岁可怜。炀帝笑道:“正好出昨夜之气,谁可怜你!”月宾虽然痛楚,然经过一番狼藉,毕竟稍稍减些。况炀帝用力不甚勇猛,故悲啼几声,又笑着脸儿,情恳几句。炀帝总不理他,只是捧定香肌,细细赏鉴。
月宾含颦带笑,一段楚痛光景,就像梨花伤雨,软软温温,比昨夜更觉十分可人。怎见得?但见:
心惊香玉战,喘促乳莺低;
红透千行汗,灵通一点犀。
虽生娇欲死,带笑不成啼;
谩惜花揉碎,蜂痴蝶已迷。
炀帝尽心受用,恣意为欢,只蹂躏有一两个时辰,方才收云散雨,叫把车儿停住。月宾孩子家,被炀帝苦了半日,才抽出手来,便不管一二,竟连身子倒入炀帝怀里说道:“万岁也忒狠心,便不顾人死活。”炀帝抱住笑说道:“顾了你的死活,朕的死活,却教谁顾?”二人偎倚了一会,方走下车儿,依旧同到绣闼中去玩耍。正是:
儿女情无限,风流事转多;
若非为酒困,定是被花魔。
炀帝因月宾是吴人,说的吴语好听,便口口声声,也学吴语情话,自家转不称孤道寡,只是侬长侬短。自此之后,淫情愈不可制,便日日捡有容色的幼女,到任意车中来受用。终日淫荡,弄得那些幼女痛楚难胜,方觉快畅。这个尝过滋味,便换那个;那个得了妙处,又更这个。也不论日,也不论夜,尽着性命,在迷楼中受用。怎奈迷楼中选了三千幼女,这个似桃花,红得可爱;那个像杨柳,绿得可怜;一人能有许多精力,如何得能享尽?淫荡的不多时,早已精疲神敝,支撑不来。谁知精神虚的人,欲火更盛,心下火焚,焚要去淫荡。只恨气力不能鼓舞,往往到了临时,弄个扫兴。因心生一计,叫画院管将男女交合的春图,奇奇怪怪,画上无数,遍迷楼中都悬挂起来。却携了幼女,细细观看,看到兴动之时,不觉精神震跃,就乘着兴头与幼女去宣淫狂荡。略不济事,便重新又看。只因这个法儿有验,便差人各处去寻求巧妙的春图。
一日正与幼女观图戏耍,忽有太监来奏道:“宫外有一人叫做上官时,自江外得乌铜屏三十六扇,献与万岁。”炀帝道:“什么乌铜屏?快抬进来看。”太监领旨,不多时将铜屏抬入。炀帝定睛一看,只见那铜屏有五尺来高,三尺来阔,两边都磨得雪亮,就如宝镜一般,辉光相映,照得彻里彻外皆明,下面俱以白石为座,炀帝看了大喜,随命左右一扇一扇的排将起来。三十六扇,团团围转,就像一座水壶;又像一间瑶房;又像一道水晶屏风。外面的花阴树影,映入其中,又像一道画壁,人走到面前,发形容,都照得明明白白。炀帝看了十分欢喜道:“琉璃世界,白玉乾坤,也不过如此!”遂叫了吴绛仙、袁宝儿、杳娘、妥娘、朱贵儿、薛冶儿、月宾一班美人幼女,回到中间坐了饮酒取乐。众美人你来我去,一个人也不知有多少影儿,炀帝在中间左顾右盼,但见容光交映,艳色纷飞,竟辨不出谁真谁假。因大笑道:“何其美人之多乎!令人在接不暇?”袁宝儿道:“美人未尝多,还是万岁的眼多。”
炀帝大喜道:“眼到不多,自是这一片柔情多耳!”大家说说笑笑,尽情欢饮。炀帝饮到陶然之际,见众美人娇容体态,映入屏中,更觉鲜妍可爱。一时情兴勃勃,把持不定,遂叫宫人将锦茵绣褥,移入屏中,亲同众美人幼女把衣裳脱去,裸体相戏。众美人这个含羞,那个带笑,你推我,我扯你,大家在屏中,欢笑做一团。炀帝东边也采一阵,西边也揉一场,那些淫形态状,流入鉴中,纤毫不能躲避,真个是荒淫中一段风光,有《鹊桥仙》词一首为证:
香肌泼墨,玉容染翰,形儿影儿难辩。君王痴眼醉模糊,但只见春光一片。
镜中花豹,烟中粉黛,画出莺莺燕燕。娇深媚浅不争些,便胜似丹青无限。
炀帝狂逞多时,满心欢畅,因说道:“绘画的春图,不过只描写大意,怎知鉴屏中活活泼泼,神情态度,都摹画出来,真令人销魂欲死也。此铅屏胜似春图何止万倍,上官时之功,不可不赏。”遂传旨赐上官时千金与官一级。正是:
只为风流影,全消浪荡魂;
君王拼性命,去搏佞臣恩。
不知炀帝得此乌铜屏,毕竟又作何状?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