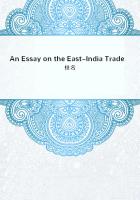刮嗒刮嗒的怪响盈耳。遂吩咐春芜道:“此事不可向人说出,倘老爷知道,如何处置?”悄悄回房,心下甚是不悦。少顷天成事完,缩来睡在小姐脚后。小姐道:“走来,我与你讲话。”天成扒过去,小姐道:“你原来是一个畜生!”天成道:“为何今日破口?”小姐道:“我看你不顾葛履之谊,那管雄狐之诮!兄妹之间,岂堪如此,非畜生而何?”天成道:“岂有此理!你太疑心,所告者过耳。”小姐道:“我适才亲眼见的,有谁对我说来?”天成掩饰不过,乃道:“非我亲妹,望你周旋。”小姐道:“即非亲妹,如红拂妓见张仲坚,道妾也姓张,合是兄妹,邪念就不起。况有兄妹之称,岂有苟且之理?还不快央媒人嫁之,若留在此,恐生讥谤。倘露风声于外,你我何以做人?你若看得我身边丫头们不中意,我自去寻媒人,密访傍搜,聘个丽人与你。明公正娶,讨了一房妾在身边,怕谁议论?”于是天成哀告道:“非蒙小姐如此爱我,我也不敢说明。你道我这妹子是谁?”小姐道:“是谁?你实对我说,或者是你情人,不好说出,故以妹为名么?”天成道:“非也!”又不说出。小姐钉紧,要他说个明白。于是才道:“我娶他在家已一年有余,夫妻困苦,再无怨言。因凤兄有书见招,我已绝望。他道:‘我与你贫苦已极,朝夕薪水不敷,不如我且出家,你去成了这头亲事,有便人寄些东西与我,可不两全?’我断然不允,他便寻起自尽来。我没奈何,只得强他到此,安顿别处,还好亲自照管。不意令尊翁有此美意,允同进来,故假作妹子,连凤兄也不知其细。”小姐道:“这人自然不知,若知如何肯对我爹爹说亲?如此看起来,这位女娘人间少有。你不早说,倒等他受此一向寂寞。只是我爹爹知道怎么?”天成道:“万望小姐且瞒着岳父,待后再觑机会。若得周旋,有个敢忘小姐恩义的么?”小姐道:“说那里话!我与你夫妻之间,丈夫娶妾二三个也不为多。况只一人,如此贤淑,我岂忌他?我房中只有春芜知道,吩咐他不许说出。”遂拉了天成手道:“我与你同去见他。今后不可没廉耻,又做这狗窃鼠偷的事。”同进爱姑的房,小姐道:“姑娘!”复道:“啐!如今是姐姐了。”又叫:“姑娘,你不必瞒我,前后的事,我都知道了。世上要加你这样女人也少,你既要成全丈夫,难道我到破败丈夫?你长我一岁,我与你趁此明月,拜为姐妹。”小姐道:“明月在上,霍氏若生妒忌心,使姐姐不能与丈夫同处,不得我生于世。”爱姑亦道:“明月,午氏若辜小姐之恩,使丈夫不得与小姐谐老,亦不得久长于世。”盟毕,小姐遂拽爱姑与天成同睡,道:“你也熬得够了!”爱姑反面红一块白一块,不肯去睡。小姐道:“如今倒做作起来。”与春芜同推二人上床。天成连小姐也扯在身边,三人解衣共寝。从此朝欢暮乐,内外不知。
却说那午慕泉,眼巴巴望女儿,两年不见归家。便置些货物,发到江西货卖,打听女儿、女婿消息。竟到理刑厅衙门前,尽道如此这般,谋相公已赘入霍廉使衙中了。午慕泉便将始末告诉了一遍:“如今不知这畜生,将我女儿放在何处?”众人都说:“原系无妻,我老爷才肯做媒,若有妻的,霍小姐肯与人做妾么?”午慕泉含了眼泪,又到霍廉使处访问一番,女儿竟无下落。心中痛苦,谋天成不得见面,不如写一禀帖送进,便有分晓。
禀曰:
具禀人午冲,禀为杀妻别娶事。切冲系福建福州府福清县人,生女午氏爱姑,凭媒配与同里兽婿谋天成为妻。做亲一载,陡以抽丰为名,携女同往江西。孰料不思结发恩重,谋陷尸骨无存。讯问来历,始知已赘府中;蒙蔽隐情,那晓弃妻地下。情极事急,控诉无门,巨恶昭张,难逃法网。恳恩追究女尸,生死衔结。上禀。
门上传将进去。霍廉使一见,暴跳如雷,忙呼小姐问其来历。小姐道:“谋郎君子之人,料得不肯害妻别娶,其内毕竟还有隐情,待该儿问其详细,再报爹知。”廉使以禀帖付小姐道:“既是有了妻子,我的女儿肯与人做妾么?气死人也!可恨那凤理刑也来哄我,便宜他钦取去了,不然我怎肯放他?这畜生我与他誓不见面,连他的妹子也赶出去!”小姐再三劝解,廉使之怒不息。
却说天成知此一节事端,忙着大门上人请了午慕泉到后门进厅。同爱姑见了父亲,道及小姐贤慧,已拜为姐妹相处。午慕泉跌脚道:“我那里知此?”谋天成道:“我也无颜在此,同午爹寻一下处读书,你姐妹好生过日。”于是出门,寻一关王阁上藏修。小姐朝夕着人送茶送饭,极其丰盛精洁。迟一二天,天成即私回家,夫妻一会,只瞒着丈人。如此半年,夫妻姐妹愈相绸缪。一日霍廉使忽染一病,不起。天成私自回家,延医调治。天数该终,再救不好。病在危笃田地,廉使叫小姐请天成来说话。翁婿才相见,廉使对天成道:“你虽作事乖张,伦理情义上还未缺欠。我今病危,与你永别,你可好看成我女儿。些须家业,归你掌管。”把帐目文书都抬过来,交付天成。天成拜倒于地,哭不出声。不一会儿廉使已长逝矣。举家号哭震天。天成乃小殓大殓,开丧闭丧,出殡安葬,祭奠之礼,尽半子之孝毕,然后请午慕泉回家,同享安乐之福。
此皆天成不忍弃妻而别娶,贤女不忍听父而忘夫。在廉使不得不恼,在小姐不得不周。一门贤孝,各尽其道,所以后日子孙荣盛,夫妇同谐,作一段奇文。
第十四回
骚腊梨自作自受
诗曰:
行藏虚实自家知,祸福由来却问谁;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这首诗乃梓童帝君醒人圣语,不过要劝人行些好事,不可暗里损人。你若算计了人,天的算盘丝毫不爽。
因话说镇江府丹徒县,北门外有一裁缝姓俞名木。讨妻吕氏,年二十三岁,七月初七日生,小名叫做阿巧,人都呼他为巧姐。收一腊梨做徒弟。三口过日。却说那巧姐乃狂骚之物,且少年有色,如何遏得这欲火炎蒸?裁缝年近半百,性嗜酒,而酒下这一字,不消说起。这徒弟虽然貌丑,然香臭是知道的。日逐挨肩擦背,打牙犯嘴。巧姐无奈,也有三五分在腊梨身上,要煞火的意思。
一日腊梨穿着单裙,在师父面前做生活。巧姐走来,彼此有心,腊梨不觉裙内的东西凸凸的跳,动个不了。巧姐看见,欲火点着,强遏不下,而阴物也休休的动将起来。以手将竹头,向腊梨敲他一下。骚腊不敢声扬,将此物夹了过去。而巧姐脸上红一阵,热一阵,无处发泄。正值酒鬼有人招他吃酒去了,骚腊梨道:“师父娘,适才亏你割舍得,将我的这东西着实打这一下,至今还是疼的!”巧姐道:“谁叫你老子也来颠头播脑的,不打他打谁?”骚腊梨便涎了这脸道:“正是我老子,我一向不曾寻得坟地葬他,没奈何你有那好穴,把他安身儿,生死不忘大恩!”于是见没人,一把扯妇人进去。巧姐道:“啐!我又不是风水先生,我身上又没坟地!你来,你来,我再着实敲他几下!”骚腊梨道:“你身上有个好穴,我看想已久,没奈何,赏我葬了他罢!”一把扯了巧姐进去。正是《西厢》上说得好:姐姐虽然口硬,脚步儿早已先行。
妇人被腊梨扯进,也不甚拒,立着凭腊梨做作。只见那腊梨扯落巧姐的裤儿,攥起单裙,就随妇人立着,将此物连槊是槊,忙忙的一口气抽了二三百抽,禁不住一泄如注。一来恐怕人撞,二来耐得不奈烦了。只见那巧姐渐渐身子酥将倒来,正在美处,半腰里折了。腊梨一把抱住,系上裤子,扶将出来。巧姐面红耳涨,一先同在外边做衣服。
诗曰:
满眼风流满眼迷,残花何事滥如泥;
只因浪蝶浑无觅,飞入梨花暂解颐。
骚腊梨道:“我往常本事极好,今日不知为甚,一上场就完了。”巧姐道:“此事只可你知我知,不可与人知道。”腊梨道:“这个自然。只要师父娘常常如此,不可有别人,又抛撇我。”妇人骂道:“骚腊梨,又来乱语了。有了你罢了,难道又寻别人?”腊梨道:“我不信,你若有此好心,对天盟个誓才信你!”巧姐道:“痴腊梨,我若有此心,不逢好死。你也要罚个咒,你在人前卖俏,说出些长短来怎么?”腊梨道:“皇天后土作证,我若对人说些长短,身首不得完全,死于刀剑之下!”于是两人一心一意,只要等酒鬼出门,就弄耸起来,无日无夜。正所谓:拳无正行,得空便打。
却说裁缝有个酒碗弟兄,姓马行九,领一后生送到俞木家做徒弟。这后生姓戈名利,人都唤他做小戈。有一首词,单道好处。
词曰:自幼聪明伶俐,风流博浪牢成;面庞俊雅自天生,更喜满身丰韵。莫羡点头解尾,休夸识重知轻;只有一件不堪闻,见了佳人是命。
右调《西江月》
却说巧姐见了这个标致后生,就如天上掉下来一个活宝,满面堆下笑来,千欢万喜,煎茶暖酒,款待马九老出门。这小戈见了这妇人,看他容貌有千般娇媚,万种妖娆。乃自暗喜道:“这也是天缘辐凑,聚在一家。就是不能勾到手,朝夕等我饱看一回,也使眼目清亮些。”一日两,两日三,看看熟落,不拿强拿,不做强做。又是两心相得,四目相看。你贪我爱,只恨一时走不拢来。那腊梨见二人调得火滚,恐怕插了趣去,张眼空与巧姐温存。怎奈这妇人有了小戈,那里还看得腊梨在心上,倒惹厌起来。那后生是头上一记,脚底板上响的人,见腊梨如此光景,有个不解的?乃忖道:“如此一个标致娘子,难道到与这臭腊梨刮上了不成?我不信,且去混他娘!”于是眉来眼去,妇人笑而不言。
一日师徒三个在店内做生活,妇人立在桌横头。那小戈以脚向巧姐金莲上一踏。巧姐只道污了他鞋,忙惊去瞧,原来小戈先脱掉了鞋子,光袜子踹上一脚。巧姐带笑瞅他一眼。那酒鬼犹在醉乡,这腊梨是贼的,瞧见这个光景,心中暗气道:“他自罚咒的,如何又看想他?一有他则没我了。不要慌,让我搅搅臭着!”于是再不出门。正是:蚂蝗叮了鹭鸶脚,你上天来我上天。
那巧姐与这小戈火热,恨不得一霎时到手,到碍着这腊梨眼睛,左支他不出门,右唤他不离户,一步不离,到你这妇人就是他娶的一般。小戈欲待打成一家,又不惬气。若不,又掣肘难行。正在两难之际,只见巧姐暗自道:“我的身子,怎么倒与这腊梨管紧?”于是走出来叫道:“小戈,你进来,我与你说句话。腊梨,你在店里看着,不必进来。”那小戈就走,这腊梨也跟进来道:“有话当面说,怎么要进来说?如今快说完了,好同出做生活。”那巧姐把腊梨一推,将中门闭上。这腊梨暴跳如雷,嚷道:“青天白日,像什么模样?看师父来我说不说!”那巧姐忙出来一个叹唾道:“蠢腊梨,关你甚事?我是你的老婆?要你管我?对那酒鬼说不说怎的?老实对你讲,你若和同水面,大家混混。你若钉清捉螺师,我就说出你的故事来,连你也在这里安身不牢!”腊梨便喃喃呐呐的道:“只要师父娘把我一般看待,我还有甚屁放出来?”那小戈就接口道:“腊兄,今后不要你长我短,我与你师兄师弟的,既承师父娘如此看待我们,各要尽心。你有事,我来帮衬,我有事,你来护卫,不消顾得前后了。你道如何?”腊梨道:“只要依得你口里话才好!倘若后边要更改起来,却是如何?”小戈道:“断不更改!”腊梨道:“既恁的,你们去完了心事罢。”那小戈听了一声,就同巧姐到床边,急得把妇人的裤带都址断了。挺出腰间阳物,往里一顶,没根露脑的捣起来。但见:一个喜孜孜不顾丈夫利害,一个热极极那管上下尊卑。一个将朱唇紧贴,樱桃口微微气喘;一个将粉脸邪偎,杨柳腰脉脉春浓。正是星眼朦胧,细细汗流香玉颗;酥胸荡漾,涓涓露滴牡丹心。
却说这小戈自小盗得些采阴法,将阳物只往上下两旁,摇摇拽拽,寻花觅蕊。巧姐淫兴勃发,囗囗囗(此处删去九个字)口如小娃子拓食一般,以身子渐渐偎下迎凑。那小戈就晓得是生得浅的了,于是只向这花心中刺去,连射了三五百下。只见那巧姐四脚软瘫,口里话都说不出来。小戈趁此光景,尽力奉承七八百抽,两下都泄了。却说腊梨等事完,扯开小戈,也要上香。巧姐怪道:“梅香也要递一钟?明朝罢!”腊梨那里肯放,将向妇人乱躅,不上几十躅就完事了。巧姐笑道:“何如?我道这蠢东西,躅这两躅有甚妙处?”指着小戈说:“就像他,一到里边,对着花心擂上擂下,真令人如在云雾中,如醉如迷,有许多说不出的妙处。像你的不来,到省得垃垃圾圾,弄得人不爽快。”说得这腊梨满面羞惭,往外去了。
心中甚是不平,道:“不要慌,等师父来,放他一个边箭,看你快活得成么?”巧姐有了这小戈,似漆如胶,有说有道。视这腊梨就如粪土一般,不瞅不睬。腊梨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