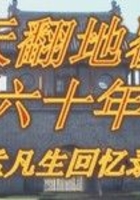却原来是蜜边箕约了杨蚕子等辈,瞧着巴不着进门,他便用此计较。巴不着害怕,连忙拔出囗囗囗(此外删去七个字),下楼与苟子美大开门,弹着提琴,以教曲子为名。那些邻舍有两个走进门听曲子,一混散了。
巴不着回家又生一计,叫苟子美来道:“我叫河房下灯船一只,叫妈同郎家奶奶男扮了,寂寂出门,上船玩玩。”巴不着叫着一只灯船,原来这船,原是一个行不出的光棍王炎的船。他家中一小使叫做王龙,也在裤子巷左边居住。少停二妇人俱带了巾帻,同苟子美上船,那巴不着已在船上招呼。到舟中饮未数杯,巴不着与郎氏已进舱内。王龙不见二人在席,门缝一瞧,原来是一妇人掇起双股囗囗囗(此处删去十九个字)。只见那妇人如发摆子病的一般,一个寒噤,一个寒噤,正在要死要活的时节。王龙忙跳上岸,叫了家长王炎来,轻轻进舱,一把拿住。诸氏身边带得数两银子,忙来递与王炎,求他释放。王炎还争多道少,只见蜜边箕寻着羊振玉道:“有一灯船内,有二三内眷在内干事,我访得亲切,邀你去赚他几两银子。”羊振玉原吃这一碗衣饭的,听了欣然同来。上船见诸氏、巴不着都央求王炎,羊振玉一时怒发,把王龙挥上几掌。那王炎、巴不着俱一溜烟走了。只存储氏、苟子美、郎氏还失了小衣。羊振玉反埋怨蜜边箕道:“你既知道此事,也须明说,如何哄人到此?”蜜边箕也竟去了。郎氏反喃喃呐呐的骂道:“狗忘八,你既是好汉,如何妻子有得与人诈害?”
羊振玉道:“我还做什么好汉?如今事已至此,作带归家。”领了郎氏,男扮回家。振玉只是叹气,目瞪口塞,不出一言。冷静几时,羊振玉要做好汉的,如何被人指触得过?遂移清凉门去住了。羊振玉却气小巴不过,监中牢头禁子,都与振玉相厚,有一起江洋强盗下来,私下买嘱了他,一口咬定已高,后在狱中而死。你道内可惧的么?惟惧了他,是然把你如掌中儿,何事不忍为?较之跪与打尚小者耳。人喜惧内,吾甚不解。
第十二回
小鬼头苦死风流
词曰:
遴选嫔妃下玉音,陡将闺阁一时倾;
可怜错配多情种,赢得高唐梦不沉。
这首诗单表弘光南都御极,钦天监看出太阴星照在浙江,奉旨来杭遴选淑女三人。此风一播,慌得那有女儿的人家,已定的,竟送到夫家,不必说起。如未定的,哪论年纪少长,哪论门第高低,只要有人受纳就罢了。因此有幼女配个老男,有少男反娶了长女。其间不知错配了多少。惟其错配,自然于中做出事来。
话说宁海地方,有一姓殷名富,倚着是个旧家,又颇过得日子,养一女,名唤掌珍,东不成,西不就,蹉跎到十八九岁,尚养在家里。闻得此风,脚忙手乱,也不去打听,也不去求卜、凭媒说合,成了一家十二、三岁孩童。这孩童也是个好人家儿子,姓毕名达,请一先生在家读书。但此子:
性钝质粗,语侏言嗝;
男女之间,一窍不识。
一两日内,即便成亲。花烛之夜,掌珍见新郎太小,心下十分不快。又听他语言不清,口嗝练缠,念一字出口,非三五声还不肯住。正是:若去买桐油,先擂三通鼓。
掌珍听了,愈觉不乐,况年长知味,见姊妹们夫妻相好,未尝不羡慕的。今日有家,满望亲尝摹写一番趣味,谁想这小小孩童,晓得什么枕边恩爱,被底风流?一上床,纳倒头竟自睡熟了。
叫那掌珍的腮边珠泪,就是断了线头一般,颗颗滴将下来,道:“这样东西熬得他大,我却不做了泉下鬼么?”心下虽是这等不快,却又转想道:“我闻得男子自十三四岁,就会干事了,他或害羞,也未可知。到等我去试他试。”没奈何,脱了衣裳,去毕达脚后睡了,见毕达不动。把只小脚儿去搁在毕达的腿上,毕达也不动。掌珍又把只手去摸毕达的腿。毕达只是不动。掌珍摸得高兴,直摸到阴囊边,见小小一对卵儿,如鸡卵儿大。因就捏那活儿,不上一二寸长。掌珍叹口气道:“这般东西,怎煞得火?”复又掉下泪来道:“我直恁命薄!”
诗曰:
怅怅儿夫小,炎心难咽何;
鹊桥如可驾,即欲渡银河。
不说掌珍的怨恨。再说毕达有个同窗朋友,叫做瞿雪,年纪仅十八岁,生得身材矮小,性格聪明,善滑稽,打六国乡谈,如出一口,在毕家读书。父母趁选秀女,也与他寻一个妻室。拜了花烛,只见新人只得十一二岁,不肯进房间睡。其婆的劝道:“我儿,不妨今日应个好日,同一同房。再歇两三年,与你做大亲。”
女子只得进了房,见被帐枕席,俱铺设得齐整,那里知道有甚利害?竟自睡了。那瞿雪却恨道:“我爹娘好没正经,怎寻这样小小老婆与我?叫我空指望今晚试笔,谁知道是这个东西,把我一腔子炭火,何处发泄?”恨恨的坐了半刻,既而道:“弄虽弄不得,看是看得的。我也不曾亲见这东西,是横生的直生的?待我去瞧瞧看!”竟揭开了那被来。女子见揭开被,慌了,把两只手去掩着那小牝儿。瞿雪道:“我不弄你,我只要看看儿。”扯开了那手儿一看,真如一个馒头儿,圆圆突起,囗囗囗(此处删去十一个字)。瞿雪不看则已,看了那点火有万丈来高。女子见他看不了,害羞,把个被儿蒙了头。瞿雪看之不已,把个指头去拨拨儿,挖挖儿,又将些津吐去涂涂儿。见缝儿有些开意,他那里顾得,轻轻跨上女子身上,把这如铁硬的本钱只一顶。可怜这女子直喊起来。瞿雪忙拔出囗囗囗(此处删去九个字),慌慌张张跳下床去躲了。公婆听得,忙携灯来,看见女子晕倒不做声,小物儿两开,血流满席。婆苦道:“天杀的,动不得的!”其公道:“莫喊!被人耻笑!你好生在此伴他,延医调治,打发那畜生馆中去。”因此瞿雪在馆。
诗曰:
笑煞书生忒恁狂,怜香惜玉未曾尝;
他年重会巫山上,犹认横糊血未乾。
瞿雪虽在馆中,却想那件甚是无比,只恨弄得不爽快。挨至黄昏,毕达读完晚书,来掌珍脚后睡着。掌珍日间偷觑那些阳物,自家一发宁耐不住,想道:“其物虽小,只贴贴儿,沾些阳气也是好的。但这小厌不得过来,却如之何?”乃向床头摸一个梨头,吃得嗖嗖有声。毕达道:“你你你吃些什么?”掌珍道:“好东西!”毕达道:“拿拿些与与与我吃。”掌珍道:“你要吃过来。”毕达只得跑将过去。掌珍以口布去与他吃。那毕达道:“我我我不要这残的吃。”掌珍叹一口气,道:“咳!”停了一会,掌珍将手去摸摸毕达的本钱,就如烂葱头,一毫硬郎的气儿也无。急得那掌珍又气又恼,一时性发,把本钱用力一扯。毕达就是那杀猪的怪叫起来,道:“我我我再不与你同睡了!”掌珍道:“不来睡倒妙。”毕达被掌珍腾倒不过,到晚就怕同睡。
诗曰:
不快新娘意,都缘刺不投;
风流如此苦,何事觅风流?
一日,毕达走到瞿雪房里来,瞿雪笑迎着:“大哥,恭喜娶得个好大嫂。”毕达蹙额道:“莫莫要说起,我爹娘没要紧,娶这一个与我!你你你是晓得我这一件事是不谙的。那那那人到恨我,把我十分凌辱。”瞿雪道:“怎么样凌辱。”毕达道:“说说说也羞人!不是踢,就是摘,把把把我本钱几乎扯断了。叫叫叫我睡在床上,如卧针毡。”瞿雪道:“兄,是你自不是。想这一窍有甚的难谙。摸着那洞儿,将本钱蛮管塞进去。待他进了洞,便抽打起来,自得妙境。”毕达笑道:“大哥,怎奈我这件东西是怕见的,一见了愈缩将进去,如何还动弹得?”因问道:“大哥,你也恭喜,娶得大嫂得意么?”瞿雪摇手道:“说不得!说不得!你的苦大,我的苦小。看起来,与兄换个聘才好。”两人大笑而散。
却说瞿雪便提了心,道:“这呆物,把个美娇娘空在那里。我小瞿有了本事,却又闲在这里。要不两相耽误?不如趁小毕未动手之先,新人点得火着的时节,早早去下手,不怕不是我开荒!”就留心学那毕达的声音,学得酷肖,但开口说话,同堂学生都道小毕来了。凡一切楼上楼下,转弯抹角所在,穿房入户的去处,一一的看在眼里,访在肚里,只等机会到时,便就行事。
忽一日,毕达戚戚不悦。瞿雪携了他手道:“大哥有甚不悦?”毕达道:“真真真悔气,讨着这个东西!苦苦苦死埋怨我到害了他,不不不知我害他甚的?恨恨恨一声,把我咬一口,叫叫叫我如何同得床睡?”瞿雪道:“恁般利害,兄的性命也要磨杀。”
毕达掉下泪来道:“正是这般!我几番对爹娘说,到反骂我不成器。我我我也无法处治,要借你房中权宿两夜,且安枕睡一觉着。”瞿雪道:“这着尽好,可对老嫂说了出来么?”毕达道:“还还还对他讲?他也不要我,随他怎的罢了!”瞿雪道:“大哥之计甚妙,且冷落他几天,自然回心转意了。”不觉天晚。读了晚书,毕达竟不进去,就在瞿雪房中安寝了。瞿雪道:“我在外边打铺,你连日辛苦,不要惊动。”他便停一会,见内外人静,摸将进去。
诗曰:
设下机谋鬼不知,盗开锦帐偎娇枝;
欢娱此夕虽偿足,究到临头祸怎知。
却说那瞿雪身原不长,又缩短些,偷了毕达的衣服打扮起来,响响落落进内,上楼把门关了,摸到床边,竟自脱了衣服,挨入被内,贴着里床睡了。掌珍见他来睡,便把脚来一踢,道:“睡进些!”假毕达道:“嗄。”把身子向里束一束,口里捣鬼道:“我我我今朝造化,得丸药吃,这本钱就长大了许多。”掌珍道:“胡说!恁么药吃了,这般得快?”假毕达道:“你你你不要咬我,我过来与你看。”掌珍道:“我不咬你,快过来我看。”假毕达就爬过去,与掌珍一头儿睡了,就去扯他的手来摸。掌珍摸着,却一惊道:“这药甚好,吃了就长大这许多!一把捏来不惟火滚热,且突突的乱跳。”掌珍拿住不肯放手。假毕达道:“又又又教我个干法。”掌珍道:“怎样干的?”假毕达道:“待待待我来干与你看。”假毕达就爬起在掌珍身上,将他两股扒开,囗囗囗(此处删去二十一个字),把个硬掘掘的东西,向里只一搠。那掌珍把屁股一缩,道:“贱短命,放慢些!如何不顾人的疼痛?”假毕达便慢慢的,扯风箱的相似。扯了一会,见掌珍闭目气足,假毕达道:“想是这会不疼,有些好意思了。”便将那物尽了根。两个搂紧了,缓送一回,急耸一回。一个是干柴,一个是烈火,将有一二个更次,弄得掌珍满身酥快,遍体汗流,才住了手。假毕达道:“娘子,这入法中你的意么?”掌珍笑道:“这是那个教你的?真是个恩人!你明日须要去拜谢他。”两人搂紧了,睡至五更,假毕达道:“我我我尚有余兴,再试一试如何?”掌珍道:“晚些罢,此时我的里头有些疼哩!”假毕达道:“恐药性过了,那物仍旧小去。”掌珍道:“这个何难?既有此好药,多赎他几丸就是了。”那时假毕达已搂紧,忙叠过去。
掌珍口虽说是晚些,心里也是要的,已凑过来。两个如滚球狮子一般,一个翻上,一个翻下。又约有一个更次,听得鸡儿已叫,假毕达道:“先生要读早书,我要去了。”遂丢了手起来。掌珍道:“晚间早进来些,千万莫要忘记赎药!”假毕达应一声,竟开了门,忙忙踅到书房里来,真毕达尚睡着未起。你道那掌珍因甚笑纳不疑?一不曾与毕达敌体,不晓得肥瘦;二做女子时,也闻得吃些要药,就阳物大了;三声音宛似毕达,所以不疑。
诗曰:
已堕奸人阱,名花此夕残;
只缘初配错,遗恨在天壤。
瞿雪自夸妙计,一连进去三四夜,两人竟忘怀了,笑谈不已。其婆道:“我媳妇与我儿子初甚不合,今如此言笑,想过得好了。等我去看看。”提了灯儿,开门过来。此时假毕达仰面睡了,叫掌珍把那牝儿套在茎上,如狗子吃奶的,吞进吐出的玩耍。猛听得门响,有人叫道:“毕达我的儿,娘来了。”假毕达就把掌珍一掀,提了衣裳奔到门边,开门就跑。跑得心慌,一脚一空,一个翻跟头,一直跌到楼梯脚下,也不进书房,竟奔出大门而去。其母见儿跌下楼去,只道是害羞,忙提了灯,叫老官人寻到书房,道:“我儿,你不曾跌坏么?”毕达道:“儿不曾跌,在此睡了三四夜了。”父母惊道:“楼上睡的是谁?”毕达才放声大哭,把前后摘打,不容他睡,没奈何,在外权睡的事情说了一遍。其母大恨,奔上楼将掌珍打骂一番,连夜叫原媒发回娘家。殷富问女儿详细,掌珍哭道:“夜夜读完书进房来睡,这一夜老婆子拿灯来,他便跳下楼去。停一会,说来睡的不是他的儿子。言语身材难道有个不晓得的?明明是脏埋人,好离我另娶。把我打得浑身青紫,我死了罢!”又哭将起来。媒人又接口道:“毕家亲母道:‘我毕家何等人家,可做这丑事!’”掌珍母亲骂道:“老妇,你毕家大人家,我殷门也不小!”叫殷富:“你明日进状,断不要饶了这畜生!”瞿雪走回家去,思量躲避,闻得殷家告了毕家,毕家又牵连瞿雪;又闻岳丈恨他弄坏了女儿,也告在官。两下差人扑捉,安身不得,一道烟走了。害父母空用银子,至今此案未结。你道嫁得好女儿,讨得好媳妇么?不论年庚应配不应配,一味乱塞,全不想儿女心肠,致生出许多风波来,岂不可叹?故择配不可不慎。
一片情卷三终
新镌绣像小说一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