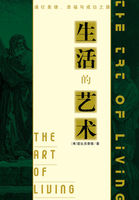过去的事情就永远地过去了吗?在成为记忆的积淀中,一些事物远了一些事物则更为接近。对于小提琴的记忆我从不认为它会遥远或消失。就像拉琴的人,他苍苍的白发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闪着银质的光芒。十多年了,老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我相信他会活着,就像他的琴声,这一生我都不会忘记。
琴是属于懂音乐的人,不懂音乐的人只能远远地望着。我至今不明白已近耄耋的老人为什么能与琴融合的那么贯通那么密切。我永远不会忘了他,因为不能忘记,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有时比爱情更有意义。
那个冬天,对我来说有点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想不到多年努力的我,依旧改变不了像流水样流去的命运。我再也无法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永远的战士,我将不得不告别一生钟爱的军营,一切重头开始。由于情绪的低落,工作也不再像从前主动,精神也显得萎靡不振,干什么事都有气无力。我无心接受战友的箴言,把领导的关心和谈话当作耳旁风。如果一直这样我不知道将来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子,然而在我接到命令不久的一个夜晚,一场偶遇改变了我的认识,让我重新站立起来。
离我所住营房不远的教学楼前有一片树林,我们非常熟悉,像老朋友,我和战友在训练或休息的间隙经常到那里走走,听一听风,看一看树身上留下仿佛眼睛的疤痕,疲惫就会减少,偶尔心情不畅到它里面说说,心情就会好很多。那天晚上,也许是因为心情太过失落,我一边走一边满脑子胡思乱想,也没有注意自己的脚步。
“嗨。”正走着,突然的一声断喝叫住了我,“年轻人,有什么想不开吗?”
我直直地定了下来,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林边上,再往前一步就可能跨进用来排水的渠中。我回过头循发声处望去。明亮的月光下,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正站在离我不远的林边上。
“能让人沉迷到可以忽视一切,不是爱情就是事业。”老人慈爱地说,“看你是个老战士了,想来是事业吧。”
我向着老人走过去,他的满头白发让我感到格外亲切。老人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我仿佛看到了最亲的亲人,忍不住把心中的委屈和苦闷都向他说了出来。很多时候,人总是愿意把内心的痛苦说给素不相识的人,因为素不相识,才无所顾忌。老人冷静地听着,不说话,脸上也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相见就是缘分,年轻人,我给你拉个曲子吧。“沉默了好一会儿,老人突然轻声地说道。
我这才注意老人竟随身带着用来盛提琴的匣子。我没想到老人竟是来这里拉小提琴的。我无数次说过自己对音乐的无知,我说不出老人拉的是什么曲子,也无法评判他的技艺。当他躬着背用颈夹起小提琴的时候,我的心里已充满感动。琴声优美伤感,不像舒曼的《小夜曲》,虽舒缓、深沉,却有小夜曲没有的幽怨。我望着老人,看着他不停颤动的肩膀和手腕,仿佛听到了他对似水流年的无奈以及对另一些事情说不出的哀怨和思念。
我有些迷惑,不清楚老人为何要一个人带着小提琴来这里,难道他的心里也有不可向别人倾诉的苦恼,或者还是什么东西不能舍弃?我由不得仔细地打量着他。老人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他正沉寂在自己的琴声里。老人的年龄我说不准,身体看上去并不坏,从他那略显挺拔的身材,觉得并不像个普通的人。正打量着,琴声突然从原先的低沉、幽怨,变得清亮悠远起来,宛若奔腾不息的江水,不仅满含生命的不屈更饱含着对命运的抗争,像迎激流而上的船只,不时地溅起一串串情感的水花……
风缓缓地刮着,几片凋零的落叶随风飘落地面。我静静地听着,虽然不明白什么是音乐的感染力,我还是感到了生命的美丽,心也慢慢地宽广和坚强。老人静静地拉着琴,认真而投入。我突然明白了老人为什么不用道理给我说教,面对生命,他的音乐让我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人生。人们常说希望在不远的拐角处,无限曲折才是最美的魅力。
此后不久,我回到故乡,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老人。如今十多年过去,尽管仍是挫折不断,即使下岗在家,我再没像从前那样灰心和失去信心。那时年轻。我知道年轻是一种优势,但年轻常会失于轻率。我一直在记忆中保留着老人,保留着他那晚深情投入的姿势。
有人说,一曲好的音乐,绝不只属于一个人。我不这么认为,就像每个有梦想的人,痛苦也许格外相似,幸福却不尽相同。老人在那晚的演奏,对别人或许谈不上什么,对于我却完全不同。
小提琴——永不遥远的独奏,当你从远方看到更远的远方,生命的海拔将会抵达另一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