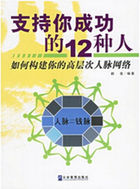懂得审美的欣赏者也不仅仅是看那几笔墨痕,也是由此及彼,进入另一境界。
现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精通老庄,深探义海,妙悟禅宗,统归六艺”,于诗书画造诣极高,被称为奇才。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泰斗,华夏国宝。马公长居西湖,晚年就住在“花港观鱼”的蒋庄。1967年在此“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兹”。终年85岁。
马公佛学深湛,佛学界许多人常登门求教。艺僧弘一法师李叔同虽年长马公几岁,但出家前后都以师事之,终生不辍。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陪同前苏联国家领导人伏罗希罗夫拜访马老。陈毅元帅也曾登门拜访,陈毅是中午去的,正下着雨。马公的管家说马老正在午睡,陈毅就站在门外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直到马老起来,留下了一段陈帅“马门立雨”的佳话。
长住西湖边的还有一文化名人,大画家丰子恺。丰子恺是李叔同的学生,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他向马公书信求教书画学问时,因马公论艺术多禅理,怕自己看不懂,就要求马公在正文外作注释。看来丰子恺对禅可谓不甚了了。
1938年马公看过丰子恺的画后,在给他的一首论画诗中注道:“华严偈云,心如工画师,能出一切相。三界唯心,亦即三界唯画。若问画是色,法无色界,作么生画?答曰,空处着笔。”
马一浮认为:“此为子恺说法,于此悟去,便得画三昧,亦是诗中上乘。”所谓“三昧”,是梵文音译,大致意思是精深的道理、真谛。“得画三昧”就是得到作画的精髓。
所谓“三界唯心”,并不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的“唯物论”、“唯心论”的“唯心”。而是说人的心量广大,容得下天地宇宙,三界都在你心里。佛教把宇宙中的存在分为“三界”,即三种存在形式,有色界、无色界、欲界。色即物质,欲即欲望。
马一浮所说的意思是,三界都在心中,画也在心中。画是用笔墨颜色画的,是色界。但作画的人追求的意境却在画外,画外无色。是无色界。
“作么生”是禅宗用语,即怎么样或怎么理解。所谓“空处着笔”,就是于空灵之心境着笔。“法无色界”,也即“师心”。心境空灵,所以无色。道家称之谓“师法自然”。所谓“师心”,也就是依内心所感悟的境界入画。所以说,一切画卷皆由心出。
还有一次,丰子恺请马公去看他的画展。看后,马公不满意。他说:“丰画笔墨痕迹太重,亦是未臻超脱,未能空灵。名家杰作,令人望去几乎不知是画,此乃空灵之妙也。”禅宗强调心性,于画而言,一切技巧均无法替代心性的作用。心性本虚空,笔墨痕迹太重,显然就离心性远了,就不空灵了。空灵之中,蕴涵风情万种。
显然,马一浮认为,丰子恺离这一超脱之境界还有距离。这“几乎不知是画”的画,便是禅境。境界是画家追求的实境,笔墨倒属其次。这就是“实相无相”。就禅而言,无相之实相是自性真心。就诗画而言,无相之实相是诗画者的寄托。笔墨不到,笔墨也无法到,真实境界是笔墨无法画出来的。正如心性实相无法说一样。
马一浮谈画史,提到吴昌硕时说:“至于晚近海派吴昌硕辈,气味恶劣,不可向弥矣!”找到几幅吴画印本,认真细看。无资格评点,但感觉是不清爽。
由马一浮论丰子恺,想起了北宋苏东坡谈唐代王维。苏东坡和王维,于中国诗书画历史上,可说至今仍是不可逾越的两座巅峰。王维开以禅入诗入画之先河,可谓文人画的开山鼻祖。与之相对,便是工匠画,毫无神韵境界可言。王维和苏东坡,两人都是大师级的禅宗居士。
苏东坡论王维的诗画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是画外之相,弦外之音。不著一笔,尽得风流。而这风流却无一字可说,无一笔可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风流,也就是超凡脱俗的境界。
苏东坡在一首论画诗中道: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若照此搜寻,当今国画,用中国毛笔画画的,画匠汗牛充栋,画家羚羊挂角。诗也是这么一副嘴脸,基本上也就是押韵的大白话,与画伯仲之间。关于禅与诗,在《每逢佳处辄参禅》里多说几句,这里就不扯开去了。
禅非宗教,是人生态度,人生智慧,是净化心灵的艺术。更是高深的艺术哲学。唐宋时,认为人无禅意便庸俗不堪。而心灵不俗,才能诗画不俗。
台湾女画家吕无咎说自己留学巴黎时,许多法国画家向她讨教中国画理。一天,一位年事甚高的印象派名画家拜访她时,拿来一部《六祖坛经》向她请教。她翻开一看,自己竟然一无所知。便只好说没读过。那位老画家大吃一惊问:“你们中国有这么好的绘画理论,你都不学,跑到我们法国来究竟想学什么呢”?这位洋画家真的是读懂了《坛经》。
这位洋画家以为《坛经》是绘画理论,依我读《坛经》的理解,也就是六祖慧能在《坛经》中所说的“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离念;无住者,人之本性。”慧能所说一切,都没离开无念、无相、无住。实相无相。
马一浮先生评丰子恺画所说的,正是无念无相无住。“无念”“无相”这两个概念,不读禅也能理解。“无住”,就是了无挂碍,清净无染的自性真心。
要说佛学和禅宗对国画和诗词的影响,也就是“直指人心”。画者如此,欣赏者也如此,方可完成整个审美过程。
经云:“当得一切法实相,当得一切法非虚妄相。”非虚妄相即实相。这里所说的“法”,非法律之“法”,而是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或景物。我们所见的,是虚妄的。为什么?因为内心世界感受到的才是真实的。内心世界里的是“实相”,“实相”不可见,所以说“无相”。实相即心性,心性无相。
马一浮给丰子恺的论画诗里还说:“人生真相貌不得,眼前万法空峥嵘。”因丰子恺题自己的画为“人间相”,所以马老有此诗句。你真的画出人生真相了吗?
《坛经》说“无相为宗”,“无住为用”。所谓“无住”,就是不执着心外的虚妄。也就是禅宗经典《金刚经》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心外的景物容易画,“无相”的世界就难画了。马老先生说“于空处着笔”,就是画出无相。
画家只画出人所能见的,一幅画只能说是画了一半。因为这笔墨的作用不是将山水草木呈现给人,目的是由此及彼,将人引入画不出的境界。正如一篇好的文学作品,呈现给读者的不是密密麻麻的方块字,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否则,看画不如看摄影,读文学作品不如在大街小巷看人来人去。
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生活际遇,同样的所见所闻,每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却是不一样的,所以才有那句“人人眼中所见,人人心中所无”。诗文如此,书画亦然。
这就是《坛经》所说,“心不随境转”,而是“心能转境”。欣赏者不住于画者笔墨之相,不随画家的笔墨转,而是转入心境,进入笔墨所无的境界。《坛经》又说,“心随境转即凡,心能转境则圣”。就欣赏国画而言,“心随境转”则俗,“心能转境”则雅。反之,画者亦然。“心随境转”之“境”,是指外界景况,而非心境之境。
无论画者还是欣赏者,若于禅理一无所知,这一审美过程就无法完成。
想到杭州西湖,有康熙所题“西湖十景”。康熙和雍正,都是精通佛学禅理的人物。虽说苏东坡有“西湖天下景,识者无贤愚”的诗句,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看法去认识欣赏西湖。但康熙题景,仍定有禅意。否则,这个风雅自诩的皇帝档次也太低了。
西湖十“景”,实为西湖十“境”。画西湖的人很多,至今未见佳作,原因就在于只知画“景”而不知画“境”。也就是说,不知“空处着笔”。
比如康熙所题“柳浪闻莺”。若画二三杨柳,两只黄莺,题作“柳浪闻莺”,不如就题为“两个黄鹂鸣翠柳”。又比如康熙题的另一景“南屏晚钟”。若画一个和尚月下撞钟,题为“南屏晚钟”,还不如题“和尚撞钟”。所谓“闻莺”,与“晚钟”一样,都只是耳闻其音,而无法眼见其声,均属“无色”界。
画者若不明白禅宗“见色明心”“观音入理”法门,法无色界,于空处着笔,不画也罢。
中国画和诗词鼎盛于唐宋,波澜于元明,式微于清,和禅宗的兴衰休戚相关。若无禅宗的影响乃至参入,中国诗画当是另一面孔,这是毋庸置疑的。
风流却在诗画外。得其风流者,即得诗画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