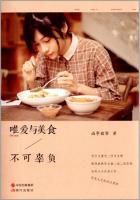我们说,一个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抹不去祖先打下的烙印。这烙印就是文化烙印。文化是民族之魂。
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许多人的反应就是诗、词、戏、曲、琴、棋、书、画,或者拘于时地的民风习俗等等,那些只是传统文化的种种表现,是流而不是源。我们说,一个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抹不去祖先打下的烙印。这烙印就是文化的烙印。
文化是民族之魂。没有文化的凝聚,人再多也不可能成其为一个民族。
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一书中说:“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
“杂货店”——佛学,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杂货店这一称谓的首创,是禅宗六祖慧能下五世法孙仰山慧寂禅师。他说,他这里说禅,因人而宜,“一如有人将百种货物与金宝作一铺货卖。我这里只是杂货铺。有人来觅鼠粪,我亦拈与他。有人来觅真金,我亦拈与他。”
“药店”——道家,社会出了问题,按事物发展规律,顺其自然,予以解决。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之初,都有一个无为而治的阶段,与民休养生息。
“粮油店”——儒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如一日三餐,不可或缺。
有了这三家店,人生和社会所需就全有了。这只是个比喻,其实三家店提供的,是同一类日用必需品:精神食粮。
我以为“三家店”不如“三家村”更为贴切。
因为说到“三家店”就容易想到买卖,想到竞争,想到许多的不如意。“三家村”就不一样了,它令人联想到的是和谐、宁静、朴实的劳动和子孙后代的衍续,是其乐融融的生命存在。
道家和儒家是本土文化,是夏、商、周三代三千年的精神结晶。儒家文化生发于黄河流域,道家文化生发于长江流域。而后一南渐,一北上,涵养中华九州。
正如人体缺什么补什么一样,文化也同此理。儒道两家缺乏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以及对种种生命现象的探究。说的准确些,是缺乏系统的关注。于是便外来了佛学。值得注意的是,你来了还得我需要。同时外来的文化还有好些,最终都没成气候,唯有佛学成了一家人。乃至后来,佛学在它的本土印度隐退后,世界上就只有中国和由中国传播的佛学了。
在中国大一统之前的春秋战国,学派蜂起,百家争鸣。而儒家和道家始终居主导地位。到后来,大致也就只有儒、道两家了。
佛教是在中国结束战乱,真正实现大一统的西汉末期进入中国的。来的正是时候。佛教到中国,至今已两千多年。
从西汉到唐,大约五百多年。这五百年间,外来的佛学与本土文化经历了不停顿的冲突、磨合、改造、融汇,直到成为地道的中国本土化了的佛学,被士大夫阶层所热衷的佛学——禅宗。除了必修的儒学和兼习老庄,士大夫们无不读禅。虽说还有其他如净土宗等等的存在,但几乎已是禅宗天下(中国佛教百分之九十是禅宗)。乃至野老妇孺动不动也会斗斗禅锋。
禅宗的出现,很快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先最突出的表现和贡献,是在文学艺术上。传统文化的三家,说儒、释、道三家,严格准确地说,应该是儒、禅、道三家。
援禅来入诗文书画,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唐朝的王维。他的诗、画,直指人心,旨在意境。沿着这一轨迹发展到后来,可说完全改变了中国诗画的走向。就诗歌而言,王维被后人称为“诗佛”。
被改造接受的佛学,当然不可能取代儒、道,三家既互通有无,又各自独立,各有各的价值取向。还说唐诗。另两家的代表便是李白、杜甫了。李、杜不可能不读禅,这从他们为数不多的禅诗可知。只是人生自我的价值趋向,使他们不想成“佛”。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以道家人物自许,诗歌大多飘飘欲仙的李白,被称为“诗仙”。而“儒冠多误身”,诗意多为忧国伤时的杜甫,被人称为“诗圣”。
李、杜、王是同时代人,前后都经历了“安史之乱”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岁月沧桑。这三个人铸就了唐诗的三足巨鼎,展示了唐诗的最高成就和辉煌。也许,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家村”格局,最早得以体现的当是这唐诗时代的诗坛“三家村”了。
传统文化熏染出来的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自相矛盾的人格冲突中。儒家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进取之路”,而道家则告诉他们如何“无用”、“无为”,顺其自然。儒家“亚圣”孟子搞调和,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至于儒、道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粮店”、“药店”作用,那是帝王术,与我们无关,我们管不着。
儒、释、道,三家之“道”无处不在,天天都和我们在一起。春种秋收,吃饭穿衣,待人接物,社会伦理,都是道。道无所不在,而又不为人知。所以《易经》说:“百姓日用而不知。”
禅宗给人的,是个人内心的自我完善,所谓“明心见性”。它的社会作用,便是净化心灵,进而净化社会。若说可见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学艺术上。
悠悠千古三家村,不只是白云深处的墟落。说不完的中华风采,尽在“三家村”。三家合流,才有中华大文化。
有人问马祖道一的弟子大珠禅师:“儒、释、道三教同异如何?”
大珠禅师答:
“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则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异也。”
从宏观把握,三教是相同的,讲的都是人性,自性真心;从细微处着眼,或具体运用,就会有很大差异。角度不同,着眼处不同,则一分为三。只有人自己的迷悟不同,不在于儒、释、道有什么不同。
毋用讳言,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它的不足之处,正如某些糟粕,某些劣根性。只不过,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永远不可能是个人的意志,只能是历史的取舍。
多年来,一直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读了不少儒家道家的经典。近年则对佛学和禅宗兴趣大增。人称佛学为“义海”,言其广博深湛。果然,一进入就出不来了。读读写写,就有了几十篇。
此前,也看过几部他人读禅读佛的文章,大多说佛门和禅宗的历史故事,或是读禅感悟。所以我在读读写写时,尽可能地有点自己的味道,也就是文化味,儒、释、道三家聚会,诗、文、书、画混为一谈。
写这些文字,本意是加深理解,帮助记忆。后有一家报纸专栏约稿,这里的文字陆续发表了一些。因为是给报纸写,不能说太多的佛禅。后来想到出版,动机,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略尽绵薄。哪怕只有一个人读,也算是文化普及了。出版前,将为报纸写的文字又作了修改和补充,话也说得明白了一些。
没有儒家和道家,就不会有中国化了的佛学,更不可能有禅宗。对传统文化必须兼容并作为一个整体了解把握,才谈得上发扬光大。否则就会有失偏颇,支离破碎,大文化就面目全非,不成其为大文化了。
现在有个现象,说到传统文化,只说孔子,很少说老子、庄子,对佛禅更是几近不提,似乎稍一涉足就有迷信之嫌。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对道家和佛学的一无所知,于是对什么是迷信也一无所知。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能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不可剥离的内容,自有其深刻的民族心理因素。正如我们民族的创世纪者是女娲,是盘古,而基督教民族的创世纪者是上帝。
我们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果只有孔子一个人,绝对是谈不上博大,也谈不上精深的。倘若如此,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我们的巍巍大中华,还有什么可谈?
我们常说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的“儒文化圈”。许多人都以为,儒文化圈里只有儒学一家。其实,这个圈内的各国各民族,对道和禅同样信奉。“儒文化圈”只是代名,总体来说,还是“三家村”文化圈。
禅宗对中国文学艺术影响很大,这是有目共睹的。禅宗的宗旨是明心见性,求之本性,得之真心,也可说就是艺术的宗旨。源于心地,印于心田,才有文学艺术对人心的潜移默化作用,而不是直白的说教。至于为实现这一宗旨的许多方法和原则,更是早就直接被运用于文艺创作实践。如含蓄、空灵、直指人心、非理性、非逻辑等等。而要理解这宗旨和方法,不能不了解基本的佛理禅风。
儒、释、道三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锻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同时也调鼐出我们独有的文化艺术。正因为是民族的,才成为世界的。了解艺术化了的禅宗,有助于了解儒家、道家的艺术观,有助于了解民族文化的整体,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如果说对儒家、道家精神一无所知,而能深入禅庭的,则纯属无稽之谈,无有是处。
读禅,读来读去说来说去,永远说不清的是“悟”,是“明心见性”。什么是悟,什么是明心见性?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对此概念没有解释过,六祖慧能也没有给弟子们解释过。但是,那个境界如如不动的存在着,是毫无疑问的。只有到达那个境界的人自己知道,但也说不出。就像梦里捡到一颗明珠,醒来想拿给人看,那明珠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所以禅宗有言:悟了还同没悟。只是这“还同没悟”与“没悟”有天壤之别。
都说禅宗是智慧,而什么是智慧呢?说得清吗?去问智者,智者也无言以对。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什么是智慧,只有神才说得清。
儒、释、道三家,释、道都有其本体,唯独儒家没有。所谓本体,简单的说,就是对天地万象源头的思考。
佛学的本体是“心”,所以又把佛学称为“心学”。“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禅宗“非宗教第一义”,一切源于心,归于心。离开“心”这一本体,佛教和禅宗便无从谈起。
道家的本体是“道”,道生一,一生二,累之至于无穷。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玄之又玄,变化无穷,能产生和统摄万物的,就是“道”。
儒学无本体论,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它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虽说儒学“五经”中包含了《易经》,《易经》可作哲学书来读,易经的本体是“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至无穷无尽。这“太极”和道家的“道”,好像是一回事。但《易经》并非孔子的著作,儒家的思想也并非由“太极”产生,所以不能视为儒学的本体。
老、庄思想和“易(变化)”结合,就是两晋南北朝的“玄学”。在士大夫阶层,谈玄之风盛极一时。所以同样玄之又玄的佛学一进国门,就与士大夫们一拍即合。而士大夫们都是儒家弟子,儒学的参与,与道家一起,便给完全中国化的佛学——禅宗的生发、发展、开花、结果,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悠悠千古“三家村”,是高山仰止的文化殿堂,是发掘不尽的艺术宝库。禅宗汲取了儒家、道家精神的精髓,是完完全全中国化的佛学。从禅门入“三家村”,大概不失为一览“三家村”宝库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