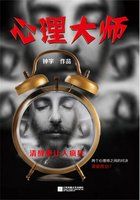话说平儿听迎春说了,正自好笑,忽见宝玉也来了。原来管厨房柳家媳妇之妹,也因放头开赌得了不是。这园中有素与柳家不睦的,便又告出柳家来,说他和他妹子是伙计,虽然他妹子出名,其实赚了钱两个人平分,因此凤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因得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与怡红院人最为深厚,故走来悄悄的央求晴雯、金星玻璃等人。金星玻璃告诉了宝玉。宝玉因思内中迎春之乳母也现有此罪,不若来约同迎春讨情,比自己独去单为柳家的说情又更妥当,故此前来。忽见许多人在此,见他来时,都问:“你的病可好了?跑来作什么?”宝玉不便说出讨情一事,只说:“来看二姐姐。”当下众人也不在意,且说些闲话。
平儿便出去办累丝金凤一事。那王住儿媳妇紧跟在后,口内百般央求,只说:“姑娘好歹口内超生,我横竖去赎了来。”平儿笑道:“你迟也是赎,早也是赎,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你的意思得过去就过去了。既是这样,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去赎了来,交与我送去,我一字不提。”王住儿媳妇听说,方放下心来,就拜谢,又说:“姑娘自去贵干,我赶着拿了来,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儿道:“赶晚不来,可别怨我。”说毕,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
平儿到房,凤姐问他:“三姑娘叫你作什么?”平儿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气,叫我劝着奶奶些,问奶奶这两天可吃些什么。”凤姐笑道:“倒是他还记挂着我。刚才又出来了一件事:有人来告柳二媳妇和他妹子通同开局,凡妹子所为,都是他作主。我想家人媳妇如此,也是常事;况且你素日又劝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并可以闲一闲心,自己保养保养也是好的。我因听不进去,果然应了此话,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自己反赚了一场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随他们闹去罢,横竖还有许多人呢!我白操一会子心,倒惹的万人咒骂!我且养病要紧,便是好了,我也作个好好先生,得乐且乐,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凭他们去罢。所以我只答应着知道了,也不在我心上。”平儿笑道:“奶奶果然如此,便是我们的造化。”
一语未了,只见贾琏进来,拍手叹气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儿我和鸳鸯借当,那边太太又怎么知道了?才刚太太叫过我去,叫我不管那里先迁挪二百银子,做八月十五日节间使用。我回:‘没处迁挪。’太太就说:‘你没有钱,就有地方迁挪。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说没地方,前儿一千银子的当是那里的?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这会子二百银子,你就这样?幸亏我没和别人说去!’我就总没有言语。但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来要寻事、奈何人?”凤姐儿道:“那日并没一个外人,但晚上送过来时,有谁在这里来着?”平儿听了,也细想那日有谁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说话时没一个外人,但晚上送东西来的时节,老太太那边傻大姐的娘也可巧来送浆洗衣服。他在下房里坐了一会子,见一大箱子东西,自然要问,必是小丫头们不知道,说了出来,也未可知。”因此便唤了几个小丫头来,问:“那日是谁告诉呆大姐的娘的?”众小丫头慌了,都跪下赌咒发誓,说;“自来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有人凡问什么,都答应不知道。这事如何敢多说?”凤姐向贾琏道:“倒别委屈了他们。如今且把这事靠后,且把太太打发了去要紧。宁可咱们短些,又别讨没意思。”因叫平儿:“把我的金项圈拿来,且去暂押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贾琏道:“越性多押二百,咱们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没处使钱。这一去还不知指着那一项赎呢!”平儿拿去,吩咐一个人,唤了旺儿媳妇来领去。不一时,拿了银子来,贾琏亲自送去。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和平儿猜疑,终是谁人走的风声?竟拟不出人来。凤姐儿又道:“知道这事还是小事,怕的是小人趁便又造蜚言,生出别的事来。就算都不打紧,那边正和鸳鸯结下仇了,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给琏二爷东西,那起小人眼馋肚饱,连没缝儿的鸡蛋还要下蛆呢,如今有了这个因由,恐怕又造出些没天理的话来,也定不得。在你琏二爷还无妨,只是鸳鸯正经女孩儿,带累了他受屈,岂不是咱们的原故?”平儿笑道:“这也无妨。鸳鸯借东西看的是奶奶,并不为的是二爷。一则鸳鸯虽应名是他私情,其实他是回过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孙男弟女多,这个也借,那个也要,到跟前撒个娇儿,和谁要去?因此只装不知道。纵闹了出来,究竟那也无碍。”凤姐儿道:“理固如此。只是你我是知道的,那不知道的,焉得不生疑呢?”
一语未了,人报:“太太来了。”凤姐听了诧异,不知为什么事情。平儿等忙迎出来。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只扶着一个贴己的小丫头走来,一语不发,走至里间坐下。凤姐忙奉茶,因陪笑说:“太太今日高兴,到这里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儿出去!”平儿见了这般,着慌,不知怎么样了,忙应了一声,带着众小丫头一齐出去,在房门外站住,越性将房门掩了,自己坐在台矶上,所有的人,一个不许进去。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
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内掷出一个香袋子来,说:“你瞧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那里得来的?”王夫人见问,越发泪如雨下,颤声说道:“我从那里得来?我天天坐在井里呢!拿你当个细心人,所以我才偷个空儿,谁知你也和我一样。这样的东西,大天白日摆在园里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头拾着。不亏你婆婆遇见,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遗在那里来着?”凤姐听得,也更了颜色,忙问:“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叹,说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馀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再女孩子们是从那里得来?自然是那琏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你们又和气,当作一件顽意儿——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和我赖!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拣得;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拣着,出去说是园内拣着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
凤姐听说,又急又愧,登时紫涨了面皮,便依炕沿双膝跪下,也含泪诉道:“太太说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辩我并无这样的东西;但其中还要求太太细详其理:那香袋是外头雇工仿着内工绣的,带子、穗子一概是市卖货。我便年轻,不尊重些,也不要这劳什子,自然都是好些的。此其一。二者这东西也不是常带着的,我纵有,也只好在家里,焉肯带在身上往各处去?况且又往园子里去,个个姊妹我们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来,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见,我有什么意思?我就年轻不尊重,亦不能糊涂至此。三则论主子里头,我是年轻媳妇,算起奴才们来,比我更年轻的又不止一个人;况且他们也常进园,晚间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们身上的?四则除我常在园里之外,还有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比如嫣红、翠云等人,皆系年轻侍妾,他们更该有这个了;还有那边珍大嫂子,他不算甚老,他也常带过佩凤等人来,焉知又不是他们的?五则园内丫头太多,保的住个个都是正经的不成?也有年纪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时半刻,人查问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门上小幺儿们打牙犯嘴,外头得了来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没此事,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请细想。”
王夫人听了这一席话大近情理,因叹道:“你起来。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轻薄至此?不过我气急了,拿了话激你。但如今却怎么处?你婆婆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说是前日从傻大姐手里得的。把我气了个死!”凤姐道:“太太快别生气!若被众人觉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静气暗暗访察,才得确实;纵然访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这叫作‘胳膊折在袖内’。如今惟有趁着赌钱的因由革了许多的人这空儿,把周瑞媳妇、旺儿媳妇等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里,以查赌为由。再如今各处的丫头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闹出事来,反悔之不及。如今若无故裁革,不但姑娘们委屈烦恼,就连太太和我也过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一则保得住没有别的事,二则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这话如何?”王夫人叹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从公细想,你这几个姊妹也甚可怜了!也不用远比,只说如今你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来着!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别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通共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像个人样,馀者纵有四五个小丫头子,竟是庙里的小鬼!如今还要裁革了去,不但我于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虽然艰难,难不至此。我虽没受过大荣华富贵,比你们是强的。如今我宁可自己省些,别委屈了他们。以后要省俭,先从我来倒使的。如今且叫人传了周瑞家的等人进来,就吩咐他们快快暗地访拿这事,要紧!”凤姐听了,即唤平儿进来,吩咐出去。一时,周瑞家的与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现在五家陪房进来,馀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
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详细勘察,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方才正是他送香囊来的。王夫人向来看视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无二意,今见他来打听此事,十分关切,便向他说:“你去回了太太,也进园内照管照管,不比别人又强些?”这王善保家的正因素日进园去,那些丫鬟们不大趋奉他,他心里大不自在,要寻他们的故事又寻不着,恰好生出这事来,以为得了把柄;又听王夫人委托,正撞在心坎上,说:“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话,论理这是该早严紧的。太太也不大往园里去,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像受了封诰是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儿?不然,就调唆姑娘的丫头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谁还耽得起?”王夫人道:“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的丫头原比别的娇贵些。你们该劝他们。连主子们的姑娘不教导尚且不堪,何况他们!”王善保家的道:“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调调,大不成个体统!”
王夫人听了这话,猛然触动往事,便问凤姐道:“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说得,后来要问是谁,又偏忘了。今日对了坎儿,这丫头想必就是他了。”凤姐道:“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却是晴雯生得好。论举止言语,他原有些轻薄。方才太太说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说。”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这样,此刻不难叫了他来,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麝月,这两个笨笨的倒好。若有这个,他自然不敢来见我的。我一生最嫌这样人!况且又生出这个事来。好好的一个宝玉,倘或叫这样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因叫自己的丫头来,吩咐他:“到园里去,只说我说有话问他们,留下袭人、麝月伏侍宝玉,不必来,有一个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来!你不许和他说什么。”小丫头子答应了。
走入怡红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觉才起来,正发闷,听如此说,只得答应了。他们素日这些丫鬟们都知道王夫人最嫌调妆艳服、语薄言轻者,故晴雯不敢出头。今因连日不自在,并没十分妆饰,自为无碍。及到了凤姐房中,王夫人一见他钗亸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次见的那人,不觉勾起方才的火来。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便冷笑道:“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宝玉今日可好些?”
晴雯一听如此说,心内大异,便知有人暗算了他,虽然着恼,只不敢作声。他本是个聪敏过人的人,见问“宝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实话对,只说:“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宝玉在一处,好歹我不能知道,只问袭人、麝月两个。”王夫人道:“这就该打嘴!难道你是死人?要你们作什么?”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说园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拨了我去外间屋里上夜,不过看屋子。我原回过我笨,不能伏侍。老太太骂了我一顿,说:‘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么?’我听了这话才去的。不过十天半个月之内,宝玉闷了,大家顽一会子就散了。至于宝玉饮食起坐,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又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我闲着还要作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从此后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为实了,忙说:“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费心。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们进去,好生防他几日,不许他在宝玉房里睡觉。等我回过老太太,再处治他!”喝声:“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晴雯只得出来。这一惊一气非同小可,一出门便拿手帕子握着脸,一头走,一头哭,直哭到园门内去。这里王夫人向凤姐等自怨道:“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这样妖精似的东西,竟没看见!只怕这样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际,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调唆着邢夫人生事,纵有千百样言词,此刻也不敢说,只低头答应着。
王善保家的道:“太太请养息身体要紧,这些小事只交与奴才们。如今要查这个主儿也极容易,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冷不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只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东西,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王夫人道:“这话倒是。若不如此,断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因问凤姐:“如何?”凤姐只得答应说:“太太说的是,就行罢了。”王夫人向王家的道:“你的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于是大家商议已定。
至晚饭后,待贾母安寝了、宝钗等入园时,王善保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入园,喝命:“将角门皆上锁!”便从上夜的婆子屋内抄检起,不过抄检出些多馀攒下的蜡烛、灯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这也是赃!不许动,等明儿回过太太再动。”于是先就到怡红院中,喝命关门。当下宝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心里不舒服,忽见这一干人进来,不知为何,直扑了丫头们的房门去,因迎出凤姐来,问是何故。凤姐道:“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因大家混赖,恐怕有丫头们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去疑。”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王善保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细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都叫本人来亲自打开!”袭人因见晴雯这样,知道必有异事,又见这番抄检,只得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并匣子,任其搜检一番。不过是日常动用之物,随即放下,又搜别人的。挨次都一一搜过。
到了晴雯的箱子,因问:“这一个是谁的?怎么不开开让搜?”袭人等方欲代睛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端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看了一看,也无甚私弊之物。回了凤姐,要往别处去。凤姐儿道:“你们可细细的查,若这一番查不出来,难回话的!”众人都道:“都细细翻看了,没什么差错东西。虽有几样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东西,想是宝玉的旧物件,没甚关系的。”凤姐听了,笑道:“既如此,咱们就走,再瞧别处去。”说着,一径出来,因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要抄检的原来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检抄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的人来?”凤姐点头道:“我也这样说呢。”一头说,一头到了潇湘馆内。
黛玉已睡了,忽报这些人来,也不知为甚事,才要起来,只见凤姐已走进来,忙按住他,不许起来,只说:“你睡着罢,我们就走。”这边且说些闲话。那个王善保家的带了众人到丫鬟房中,也一一的开箱倒笼,抄检了一番。因从紫鹃房中抄出两副宝玉常换下来的寄名符儿、一副束带上的披带、两个荷包并扇套,套内有扇子。打开看时,皆是宝玉往年夏天手内曾拿过的。王善保家的以为得了意,遂忙请凤姐过来验视,又说:“这些东西从那里来的?”凤姐笑道:“宝玉和他们从小儿在一处混了几年,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这也不算什么罕事,撂下再往别处去是正经。”紫鹃笑道:“直到如今,我们两下里的东西也算不清。要问这一个,连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王善保家的听凤姐如此说,也只得罢了。
又到探春院内,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这些丑态来,遂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意问何事。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连日访察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爽利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探春冷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有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说着,便命丫鬟们把箱柜一齐打开,将镜奁、妆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凤姐陪笑道:“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妹妹别错怪我。何必生气?”因命丫鬟们:“快快关上!”平儿、丰儿等忙着替侍书等关的关,收的收。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的收藏,要搜你们只管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自己去领!你们别忙,往后自然连你们一齐抄的日子还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家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这些的,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凤姐只看着众媳妇们。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奶奶且请到别处去罢,也让姑娘好安寝。”凤姐便起身告辞。探春道:“可细细的搜明白了?告诉你,明日再来,我就不依了!”凤姐笑道:“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看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日敢自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探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说:“都翻明白了。”
那王善保家的不过是个心内没成算的人,素日虽闻探春的名,“那是为众人没眼力没胆量罢了,那里一个姑娘家就这样起来?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么?”他自恃是邢夫人陪房,连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何况别个!今见探春如此,他只当是探春认真单恼凤姐,与他们无干,他便要趁势作脸献好。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罢,别疯疯癫癫的——”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你打谅我是同你们姑娘一样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你可就错了主意!你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说着,便亲自解衣卸裙,拉着凤姐儿细细的翻,又说:“省得叫奴才来翻我身上!”凤姐、平儿等忙与探春束裙整衣,口内喝着王善保家的说:“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癫癫起来,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劝探春休得生气。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气,早一头碰死了!不然,就许奴才来我身上翻贼赃了?明儿一早,我先回过老太太、太太,然后过去给大娘赔礼,该怎么着,我就领!”
那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意思,只得窗外站着,说:“罢了!罢了!这也是头一遭挨打。我明儿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罢。这个老命还要他做什么!”探春喝命丫鬟道:“你们听他说的这话,还等我和他对嘴去不成!”侍书等听说,便出去说道:“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们的造化了!只怕舍不得去。”凤姐笑道:“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探春冷笑道:“我们作贼的人,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他还算笨的,背地里就只不会调唆主子!”平儿忙也陪笑解劝,一面又拉了侍书进来。周瑞家的等人劝了一番。凤姐直待伏侍探春睡下,方带着人往对过暖香坞来。
彼时李纨犹病在床上。他与惜春是紧邻,又与探春相近,故顺路先到这两处。因李纨才吃了药睡着,不好惊动,只到丫鬟们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没有搜出什么东西,遂到惜春房中来。因惜春年少,尚未识事,吓的不知当又有什么事,故凤姐也少不得安慰他。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金银锞子来,约共三四十个,又有一副玉带板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入画也黄了脸。因问:“这是那里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诉真情,说:“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因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烦了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说:“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你要打他,带他出去打罢,我听不惯的。”凤姐笑道:“这话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这个可以传得,什么不可以传得?这倒是传的人的不是了。若这话不真,倘是偷来的,你可就别想活了!”入画跪着哭道:“我不敢扯谎。奶奶只管明日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若说不是赏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无怨。”凤姐道:“这个自然要问的,只是真赏的也有不是。谁许你私自传送东西的?你且说是谁作接应,我便饶你。下次万万不可!”惜春道:“嫂子别饶他,这次既可下次。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样呢。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凤姐道:“素日我看他还好。谁没一个错?但只许这一次;第二次犯了,二罪俱罚!但不知传进来的是谁?”惜春道:“若说这传进来的人,再无别个,必是二门上的张妈。他常肯和这些丫头们鬼鬼祟祟的,这些丫头们也都肯照顾他。”凤姐听说,便命人记下,将东西且交给周瑞家的暂拿着,等明日对明再议。于是别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内来。
迎春已经睡着了,丫鬟们也才要睡,众人叩门,半日才开。凤姐吩咐:“不必惊动小姐。”遂往丫鬟们房里来。因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孙女儿,凤姐倒要看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心看他搜检。先从别人箱子搜起,皆无别物。及到了司棋,箱子中搜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说:“也没有什么东西。”才要盖箱时,周瑞家的道:“且住,这是没有什么?”说着,便伸手掣出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并一双缎鞋来;又有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时,里面有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帖儿。一总递与凤姐。凤姐因管理家事,每每看开的帖子并账目,也颇识得几个字了。便看那帖子,是大红双喜笺帖,上面写道:
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万收好!
表弟潘又安拜具
凤姐看罢,不怒而反乐。别人并不识字。王家的素日并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这一节风流故事,见了这鞋、袜,心内已是有些毛病;又见有一红帖,凤姐又看着笑,他便说道:“想是他们胡写的账目,不成个字,所以奶奶见笑。”凤姐笑道:“正是,这个账竟算不过来。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该姓王,怎么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见问的奇怪,只得勉强告道:“司棋的姑妈给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凤姐笑道:“这就是了。”因道:“我念给你听听。”说着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了一跳。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错儿,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孙女儿,又气又臊。周瑞家的四人又都问着他:“你老可瞧见了?明明白白,再没的话说了。如今据你老人家,该怎么样?”这王家的只恨没地缝儿钻进去。凤姐只瞅着他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笑道:“这倒也好,不用你们作老娘的操一点儿心,他鸦雀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一个好女婿来,大家倒省心!”周瑞家的也笑着凑趣儿。王家的又气又愧,便自己用手打自己的脸,骂道:“老不死的娼妇,怎么造下孽了!说嘴打嘴,现世现报在人眼里!”众人见这般,俱笑个不住,又半劝半讽的。
凤姐见司棋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倒觉可异。料此时夜深,且不必盘问此事,又怕他夜间自愧,去寻拙志,遂唤两个婆子,监守起他来。带了人,拿了赃证回来,且自安歇,等待明日料理。谁知到夜里又连起来几次,下面淋血不止。至次日,便觉身体十分软弱,起来发晕,遂掌不住。请太医来,诊脉毕,遂立药案云:“看得少奶奶系心气不足,虚火乘脾,皆由忧劳所伤,以致嗜卧好眠,胃虚土弱,不思饮食。今聊用升阳养荣之剂。”写毕,遂开了几样药名,不过是人参、当归、黄芪等类之剂。一时退去,有老嬷嬷们拿了方子回过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闷,遂将司棋等事且不办。
可巧这日尤氏来看凤姐,坐了一回,到园中去又看过李纨,才要望候众姊妹们去,忽见惜春遣人来请,尤氏遂到他房中来。惜春便将昨晚之事细细告诉与尤氏,又命将入画的东西一概要来,与尤氏过目。尤氏道:“实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只不该私自传送,如今官盐竟成了私盐了。”因骂入画:“糊涂脂油蒙了心的!”惜春道:“你们管教不严,反骂丫头!这些姊妹,独我的丫头这样没脸,我如何去见人?昨儿我立逼着凤姐姐带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边的人,凤姐姐不带他去,也原有理。我今日正要送过去,嫂子来的恰好,快带了他去,或打,或杀,或卖,一概不管!”入画听说,又跪下哭求,说:“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从小儿服侍的情常,好歹生死在一处罢!”尤氏和奶娘等人也都十分分解,说:“他不过一时糊涂了,下次再不敢的。你看他从小儿伏侍你一场,到底留着他为是。”谁知惜春虽然年幼,却天生的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任人怎么说,他只以为丢了他的体面,咬定牙断乎不肯,更又说得好:“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每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派上了。”尤氏道:“谁议论什么?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姑娘是谁?我们是谁?姑娘既听见人议论我们,就该问着他才是!”惜春冷笑道:“你这话问着我倒好。我一个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还有一句话——我不怕你恼——好歹自有公论,又何必去问人?古人说得好:‘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何况你我二人之间!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管你们。自此以后,你们有事也别累我。”尤氏听了,又气又好笑,因向地下众人道:“怪道人人都说这四丫头年轻糊涂,我只不信。你们听才一篇话,无原无故,又不知好歹,又没个轻重。虽然是小孩子的话,却又能寒人的心。”众嬷嬷笑道:“姑娘年轻,奶奶自然要吃些亏的。”惜春冷笑道:“我虽年轻,这话却不年轻!你们不看书,不识几个字,所以都是些呆子,看着明白人,倒说我年轻糊涂!”尤氏道:“你是状元、榜眼、探花,古今第一个才子!我们是糊涂人,不如你明白,何如?”惜春道:“状元、探花里头难道就没有糊涂的不成?可知你们也有不能了悟的。”尤氏笑道:“你倒好,才是才子,这会子又作大和尚了,又讲起了悟来了!”惜春道:“我不了悟,我也舍不得入画了。”尤氏道:“可知你是个冷口冷心的人!”惜春道:“古人曾也说的:‘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教你们带累坏了我?”尤氏心内原有病,怕说这些话,听说有人议论,已是心中羞恼激怒,只是在惜春分上不好发作;又听这些话,不免说:“那里就带累了你了?你的丫头有了不是,无故说我,我倒忍了这半日,你倒越发得了意,只管说这些话。你是千金万金的小姐,我们以后就不亲近,仔细带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将入画带了过去!”说着,便赌气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来,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还清净!”尤氏也不答话,一径往前边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