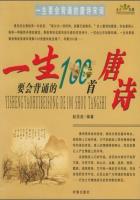黄昏,最后一抹胭脂红晕染着道口边这家理发店。女理发师弯着细长的腰,专心致志地在客人的头上实施她的美丽计划。
我静静地坐在瘦高的镜前。带点燥热的晚风挤进来,夹杂着小街上特有的气息,泊在我的鼻腔。我皱皱眉,额上的“五线谱”忽然间特别清晰起来,甚至有些刺目,如同阳光下的尖刀。
当那把蝶一样的剪刀终于幸临,在我蒿草似的乱发丛中飞舞时,我像一具被人碰到的玻璃人,哗地碎了。那些飘落的头发,仿佛营养不良的蔬菜,灰白灰白的。真的,白色的头发,幸灾乐祸地掉了一地。
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疼,如同被心上人狠狠咬了一口,却装做一脸的幸福。白发依然不动声色地飘落,一切与它们无关。我想起了观棋的人,输赢只在一笑之间。忽然觉得时间果真走得太快。
一直戴着年轻的桂冠自信地走在人流中,一年,一年,又一年,现在,我才不能不面对一道加减法,累积的是一去不回的时间,减去的是那么可爱的青春。年轻的面具,说没就没了,滴水不存。
女理发师敏锐的目光停留在我头发日渐稀疏的额头,尽管只是一刹那间,可是已经弄疼了我。我垂下眼帘,掐指一算,校园的塔松,该离开我十六年了。
十六年来,我在忙乎什么呢?也许只是做着一片极普通的叶子。是的,一个人只是森林瀚海之平凡一叶,别人看到的往往是森林的美丽;而叶子,只有自生自灭,寂寞绽开,黯然凋零。尤为遗憾的是,绿叶落尽后,树上展露的不一定是累累果实,往往是秋风冷枝。
其实,我希望人能活出一种情境,那样的人生充满了张力。情境当由以下几种具象构成:边关羌笛之悲、疆场马嘶之壮、九寨水流之静、闺中小语之柔。或许,红尘十丈,蒙蔽了我们心灵释放的窗口;生活流水单调乏味,疲惫的情状令我们憧憬粉碎,可是,任何时候,我还是奢望人生跳出最美的弧线。
没有谁体谅到我此时波澜起伏的心情。理发师当然也不会,那张仿如罗丹雕刻出来的脸,永远棱角分明,隐隐藏着一丝矜持。灰白的头发从“蝴蝶”的羽翼滑落下去。
一朵朵枯萎的花,在向看花的主人挥手告别。我如是胡思乱想。
一个生在坊间的人,忽然被生命、光阴、生死、价值这样类似的哲学思考缠绕成了一个不成样子的人,好像被五花大绑推搡着押往菜市口的犯人,神情凝滞,目光迷离。
他什么也回答不了,干脆坐在黄昏的小街上闭目养神。
一地的白发,从一个生长了三十多年的脑袋上掉落的,令他的主人什么也不敢想,什么也不敢看。他只有惭愧和抱歉。
“蝴蝶”停止了飞舞。我睁开眼睛。女理发师淡淡地道:好了。真的好了,原先那一头乱发,竟被她巧手侍弄得平平整整。令人纳闷的是,头上黑油油的,已看不出那种灰白的情形。看看地上的白发,我觉得它们有些像叶子的归宿。
天已全黑了。我沿着小街,慢慢朝道口那边的家走去。
2006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