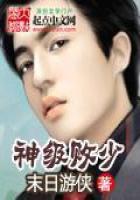云沫随即抬眼,颇有趣味地问道:“张大人,你是不是得罪过哪路会武功的高人,或者把人家的孩子溺死了!?”
此话一出,灵堂顿时又是一片寂静,甚至比解剖验尸那会儿还要沉默。
楚天阔扶额,觉得自己不到三十岁的眉头上绝对起了皱纹,了解案情时有这么问的吗?你这是审问犯人吧!就算犯人的动机真的是张诚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他好歹也是百姓心目中公认的好官,这个云沫就不能旁敲侧推吗,或者直接私底下问也好呀!官儿做得越大越要面子,现下还这么多佣人,就这么一句捕风捉影的话,传出去了绝对和昭王何蕊那档子事儿一样,最后连孩子都出来了,御史弹劾,皇上责备,张诚该疯了吧!
更何况,屋里还有三个刚死了儿子的疯……女人,张诚得罪了高人也好,溺死过人家孩子也好,总之不就是说罪魁祸首是他吗,这三个女人还不恨死这个枕边人?
果然,张诚一愣之后便是愤怒,让谁莫名其妙的按一句“溺死人家的孩子”的罪过,谁都要炸毛,然后那三个女人也看向张诚,神色复杂,一屋子下人满脸都是“原来是老爷造的孽”的感慨。
所以,这话能随便说吗,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楚天阔算是看明白了,眼前这个少女,心里没分寸啊!就跟喜堂上,怎么就敢煽动群臣让皇上作废赐婚的圣旨,不向皇上告退就抬着嫁妆出门,明知刺杀者来头不小,还宰了人家挂在各家门口,第二天上朝时皇上那个脸黑得,尸体都挂在宫门上了,能不气么?还有在济世堂里宣布开什么侦探事务所,怎么看都是突然来了兴致临场决定的吧!
想想这些,又看看背靠在棺材上的少女,正兴致满满地冲着张诚挤眉弄眼,还拿着验尸单当扇子给自己有一下没一下地扇风,当年科举写策论写得妙笔生花的楚探花郎脑子一白,词儿穷了。说这个人啥好呢?
不分场合,不知轻重,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不拘小节,无法无天,想起来一出是一出……?
张诚努力平复了一下心境,狠狠地瞪了一眼屋里的下人,示意他们闭嘴,没好气地冲着云沫说道:“张诚辅佐皇上登基,为朝廷效力,十几年来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但该杀的都是该杀之人,我问心无愧!”
“哦,”云沫胳膊肘子抵在棺材盖上,托着下巴点点头,莫名地带了几分不气死人不偿命的口吻说道:“我知道,这是官方说法,但实际呢?”
“什么实际?这就是实际!”张诚脸都绿了。
云沫安慰道:“别急别急,好好想想,没有人从来没做过亏心事的,就连我小时候还打碎过爹爹的冰瓷花瓶,嫁祸给了我大哥呢!”
“刺啦!”院子里一棵树上传来轻响,屋内的人自然没有听到。
云隐把手中的刚撕下来树皮捏成了沫,面瘫的冰山脸上带了丝丝皲裂,当年那个花瓶是你打碎了嫁祸给大哥的?那混蛋以为是我陷害了他,追着我揍了一个月!小妹,你很好!
突然感觉到不远处一丝陌生的气息波动,云隐一个眼神示意和他一起来的隐一守好云沫,然后毫无踪迹地追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