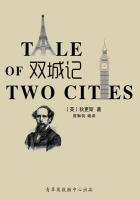命运,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真是一个不可琢磨的东西,谁能够看透?谁又能够驾驭?
话说回来,我的三爷爷此次坚定信心寻寻觅觅从怀化找到洪江来,主要是因为杨氏宗族要大修家谱了。我的三爷爷不甘心自己一家成为无后之门。他早就听说过我奶奶曾为杨家生过一个儿子,所以,从未来过廖家大院的他不辞辛苦到处打听着找上来了。他决心要将杨家有后的事实证明给世人,其实也就是证明给他生活中的人看,以洗耻辱。在那个年代,人们思想封建严重,家无男丁会被世俗的人们骂为“绝代户”,是莫大的伤心与耻辱。
我的奶奶告诉我的三爷爷,当年她虽新婚才三天,但确实怀上了孩子,而且在年末平安产下了一个儿子,并按杨家的辈分取名杨隆翰。儿子曾是她全部的寄托。
可是,世事如风云突变,转眼间,全国解放。接着,就闹“土改运动”。那是一段风声鹤唳的年代,她因为丈夫不明不白失踪,被指有潜逃的嫌疑,因此背上了不好的成分。在那个年代成分就像贴在一个人脸上的标签,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尽管之前丈夫曾是共产党,为抗日作出过贡献,但是现在却没人能站出来为他证明。而廖家大院也因为出了一个国民党的军官,遭受了血雨腥风的洗礼。廖家大院从此成了大杂院,东西厢房都被那些无比光荣的贫下中农分割,这其中就包括那个曾监守自盗的诸枭员。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处处都在上演着疯狂的一幕幕,作为九百六十万分之一的洪江,只不过是中国一个小小的舞台而已,重复着大舞台上那无数的一幕幕。小人得志的诸枭员为了己之私欲,常常故意刁难我的奶奶和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我的奶奶为了儿子不至于因为家庭的背景特殊而影响他的成长,为了他不背上“地富反坏右”的恶名,忍痛割爱将他托付给了一个家在安江的远房亲戚,从此以后,他的名字不再是杨隆翰,而是廖名祥,是一对贫下中农的后代。
期间,我的奶奶曾有几次偷偷摸摸地去看过她的儿子。在吃过中饭之后,她反扣上门,一个人悄悄地从后门出来,连夜赶到安江。看上一眼儿子后,乘着天尚未大亮,又匆匆忙忙地离开儿子赶回洪江。来回一百余里的路,她日夜兼程披星戴月,那是怎样的一种苦啊!辛酸、痛苦、迷茫、彷徨几乎将她推下绝望的悬崖,是母爱支撑着她熬过了那苦涩的岁月。本来期望有朝一日时局稳定了,能将儿子接到身边来,可是,那时天下的局势就如那汪洋大海恶浪滔天。区区洪江就如那汪洋中一条小小的船,在狂风巨浪中飘摇不定,看不到岸。巨浪接踵而至,“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一浪更比一浪凶险。那是一个指鹿为马指人为牛鬼蛇神的黑白颠倒的年代,它容不下我奶奶对亲人的柔情,如油煎火炙般生生隔断了她与儿子的感情。
等到时局明朗天宇澄清时,已是1976年,传说“轰隆”一声春雷响,一举粉碎“四人帮”。紧接着,全国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奶奶为了自己,为了亲人,为了家族,也加入了请求平反昭雪的行列。数年的奔波与上访,终于换回了一纸平反书,数十年的冤屈在那一刻终于能够扬眉吐气了。我的奶奶才敢在1982年的夏天,一个朗朗晴日下,正大光明地来到安江探望自己的儿子。
那时候,三十多年的农村生活已将我的爹爹磨炼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样样农活都做得漂亮内行,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我奶奶望着眼前的儿子,五官端正精致,眉宇间隐隐约约可寻到有廖家与杨家的遗风,让她感到欣慰。皮肤因为长年在太阳下曝晒已成古铜色,双手因为常年使用粗糙农具而骨节突出。若不开口说话,我的奶奶感觉眼前站立的还是她想象中的儿子,让她感到亲切无比。可是,只要我的爹爹一开口说话,用那地道的安江方言说起他地里的辣椒红了,今年的黄瓜比往年的更甜……听到这些,我的奶奶就感觉眼前的儿子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也越来越陌生了。
她想起了三十多年前为儿子举办的“抓周”家宴,那白白胖胖的小手从圆盘中抓起算盘的时候,家人都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然而,造化弄人,没有人会想到,三十多年后,她儿子那双曾经抓过算盘的手如今骨节粗壮如钳子,天天触摸的是锄头犁耙等农具。世事无常!世事无常啊!三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瞬,然而,对一个生命来说,却足以改变它的轨迹。我爹爹的生命之根早已远离洪江,深深地扎入了安江那片让他洒下无数汗水的土地。离开了安江的那片土地,他会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我的奶奶因此满怀惆怅,她带不走她的儿子了,只有将我带回她的身边,就当是对她儿子的赎罪。也许,在她的心里,她不希望再过若干年,她的孙女丫头也变成了一个粗鄙的村姑。
我的三爷爷听说我的爹爹在安江,执意要去安江找我的爹爹。我的奶奶没有阻拦他,毕竟都是亲人,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啊!历史的滚滚洪流永远阻断不了世间的亲情。
我的三爷爷找到安江那个小小的农家院落,见到我乡下的爷爷和娘娘后,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毕恭毕敬客客气气地对他们致以问候。然后,语气委婉,措辞有度地对二老说:“感谢多年以来二老对侄儿隆翰的悉心照顾,如今,我想让侄儿认祖归宗,还望二老能成人之美。杨家所有的人都会对二老感恩戴德,永远铭记。”这些话说得不亢不卑,有节有理。
我乡下的爷爷娘娘听到这通情达理的话,半晌说不出话来。虽然,忠厚老实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别人家的儿子,别人有权力要回去,可是,从感情上讲,却是无法割舍。他们记忆的闸门“哗”的拉开,想起儿子刚来到他们身边蹒跚学步的情景;第一次开口叫他们爹娘时的情景;三年困难时他们为了把粮食留给正在长身体的儿子吃,自己跑到山上挖树根吃;大冬天里为了能给儿子改善伙食,他们跑到冷水刺骨的田里为他掏泥鳅……这些往事如洪水般涌入脑海,让他们情不自禁老泪纵横,一遍一遍地抹着眼泪。我的爹妈都是孝顺之人,见此情景,连忙安慰起二老,答应不会离开他们。然后,又对我的三爷爷承诺,每年都会去怀化看望他们,这才让三位老人平衡下来。
我的爹爹从那以后,每年的清明都会去怀化扫墓,逢年过节还要去探望我的三爷爷满爷爷。尽管他们几十年来杳无音信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血缘关系拉近了他们的距离,让他们知道,对方是自己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最终,在那最新修订的杨氏家谱中,我爹爹以杨隆翰之名续上了杨家的香火,了却了我的三爷爷的夙愿。
12
我发现,自从1982年以后,我们家就会时不时出人意料地来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而且还都是我的亲人。
就在我的三爷爷离开后不久,正是中秋节时,廖家大院又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有了前几次的经历,我隐隐觉得这个人也是我的亲人。这个人西装革履,穿着利落,虽然是年近古稀之人,但是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他站在大门口,向院内凝望了很久。我走上前去,问他:“你找谁呀?”他回答我说:“妹朵,告诉你家大人,我要买这个院子的西厢房。”我说:“这房子不卖!”他执拗地说:“我就是想买那西厢房。你去跟你家大人说说吧。”真是一个奇怪的人!我一边往里走一边在心里想着,进屋去向奶奶禀报:“奶奶!奶奶!门口有一个奇怪的老头,他说要买咱家的西厢房。我告诉他咱家房子不卖,他还是说要买。”我的奶奶一听愣住了,一会儿“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口里不停叫着:“二哥!二哥!”一边慌忙地跑出去。有一片刻,我看到他们两人近在咫尺却都不敢相认,仿佛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
确实,来者不是别人,如我奶奶所料,正是当年将西厢房卖掉后被我的曾祖父痛打一顿,后来又失踪了的开虎。当年,他并不是故意失踪,而是因为,有一个在洪江做生意的浙江富商在过年时想回老家了,但是路途遥远,为了安全起见,他找到开虎求他做保镖,报酬可观,足可以让开虎从此翻身。两人谈妥,为了不让人跟踪而图财害命,开虎不能跟任何人说起,这就让他不辞而别了。
这一别就是千山万水,遥遥数十年。这其中又发生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有多少久别重逢后的思念之情急需倾诉!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啊!最后,还是我的奶奶挽着她二哥的胳膊,走进中堂,给他端上一盆洗脸水,让他略洗风尘,再递给他一杯茶。看着他一边喝茶,一边说:“走,二哥,我带你到塘坨市场去,我们去买个鸭子,我给你炒你最喜欢吃的甜炒鸭。”然后,我看到我的奶奶像小孩子一样牵着她二哥的手欢快地走出院子,朝塘坨市场的方向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院子里望着他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巷子尽头。
此时此刻的洪江,天蓝蓝,风轻轻,山含情,水含笑,连青山绿水都因为人间亲人的久别重逢而被打动,变得那么的美丽动人!我的奶奶与她的二哥穿街过巷,引来了众街坊邻居们好奇的眼光,他们都问我奶奶:“这老头是谁啊?”我奶奶高声地回答:“我二哥回来啦!”这更让大家震惊无比,没想到几十年杳无音信的人会突然出现。一直以来,大家都以为他已不在人世,如今他却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怎不让人吃惊?两人在洪江城里穿街而过,身后落下一路的惊叹。
等他们说说笑笑地回来时,手上提着两篮子东西。除了菜以外,还有许多小吃,什么南街的五香瓜子、东街的卤豆腐、五外婆的酸萝卜、王婆婆的灯盏粑粑……真让我大开眼界,我这才知道洪江竟然还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它们刺激了我的味蕾,让我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常满大街地去找这些美味小吃。
因为是中秋节,依着洪江的风俗,家家户户都要吃鸭子。下午时,就可闻到满城越来越浓的甜酱炒鸭的香味从大街小巷里飘出来,伴随着桂花的清香,整个洪江城都氤氲在浓浓的香气中。
我发现,我奶奶做的全是我二舅公喜欢吃的菜——奶奶让我称他为二舅公。那洪江甜酱鸭,必是用酱园春的甜酱炒吃起来才会香甜宜人;那酸辣干鱼仔必是本地沅江中的小麻鱼,炸起来才会又香又脆;那腊肉必是邹记的腊肉,油亮喷香……两人一边在厨房里烧菜,一边絮絮叨叨聊起了过去。
且说开虎护镖出浙江,本以为来回十多天就可以了,没必要向家里禀报。可是,意外的事发生了。当他安全地将那位浙江富商范老板送到家时,没想到范老板因为年事已高,加上长时间的舟车劳累,竟然突发脑中风偏瘫了。眼看自己辛辛苦苦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家业将会毁在自己手中,他心有不甘。这一路来,他也观察到了开虎是一个讲义气守信用的人,出于对开虎的信任,他极力挽留开虎帮自己经营生意,并承诺股份各占一半。这条件打动了当时一无所有的开虎。从此,开虎就开始了他的另一种生活。他恪守信用,苦心经营,生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他已是义乌小商品城一个身家数万的老板了。这么多年以来,他朝思暮想的是回家,然而,动荡不安的局势,政治上的风吹草动,都阻断了他回乡的路。直到1982年,一切风平浪静了,他才敢回来,回到家园来探望亲人。
说完了自己的经历,二舅公左顾右盼,目光扫过他数十年前住过的西厢房,停留在摆放在中堂内的我的曾祖父曾祖母的遗像上。“想念父母妻儿了吧?”奶奶问道。二舅公神情凝重了,他默默地点了几下头。奶奶说:“你的妻儿他们一会儿到了下班时间就会来,但是,父母是再也不可能与你说话了。”
接着,奶奶向二舅公简单地说起了过去。
全国解放以后,紧接着是“土改运动”,我的曾祖父跟洪江城里大多数的商户一样,将自己的资产折算成了股份并入了合作社,并将房子的大部分出让给了贫下中农们住,这其中就包括了那个曾经因为在药店里监守自盗而被解雇的诸枭员。从那以后,廖家大院成了一个鸡飞狗跳人声嘈杂的大杂院。
最为可恶的是,自以为出身根正苗红的诸枭员小人得志十分猖狂,经常会使些诡计欺负一家老老少少。宅心仁厚的曾祖父曾祖母慈善为怀,从未计较。“你知道在过去的十来年里,你现在坐着吃饭的这个地方都是谁坐在这儿吗?”我的奶奶问她的二哥。二舅公问:“是谁?”“是鸠占鹊巢的诸枭员!”奶奶说,他俨然像个主人一样大摇大摆地住在这个大院里。这还不出奇,“文化大革命”时,他成了革委会主任,呼风唤雨,打砸绑斗,淫威影响了半个洪江城。那诸枭员因为曾在曾祖父的医所谋事,所以,他知道廖家大院里有一套祖传秘方。他曾几次带人撞入二老的住处搜寻过,但都一无所获。二舅公说:“肯定是你凤丫头收藏好了。”奶奶说:“是的,是我收藏好了。我就把它们藏在诸枭员住的东厢房的后面,他永远都不会想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秘方就近在咫尺,与他仅仅一墙之隔。”有道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的奶奶用她的智慧应付着诸枭员这个小人。
为了让家里有数百年历史的原本盛装贵重药品的瓷器不至于被砸毁,她还全部给抹上了红色的油漆,就像毛主席语录本一样红的红色,然后再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包括诸枭员和勇往直前的红卫兵们谁都不敢再砸了,这才让家里那些珍贵而又脆弱的古董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