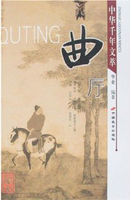我不敢问一头牛的去向
那天,走过市郊的小村庄,
暮然间望见一头牛躺在青青的草坡上
——小时候,我曾放养过的那头老黄牛呢?
它现在是否还活着,
而且还像当年那样强壮?
我依然记得,每个黄昏,
从不同的乡亲手里接过它时,
它的身上布满黑色的鞭痕,
它望着我,眼泪汪汪。
曾在无数个有月亮的夜晚,
我静静地陪在它的身旁,
听它愉快地啃着青草,
看它不时抬头,向我深情回望。
只是如今,只是如今,
我不知道,也不敢问,
它的去向。
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一日
青草莓一样的少女
丰满的叶片掩映着的青草莓,
是乡村的一些刚成年的少女,
天生丽质,青嫩欲滴。
平淡的日子里,
青草莓总是耐心地,
将散落的阳光一一拾起。
古老的乡间歌谣,悠扬地,
漫过长满青草的田埂,
青草莓微苦的心扉里,
便生出几分可人的柔情蜜意。
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山岗上有一棵大树
像一柄具伞,
挡住了炽热的阳光,
绿叶如舌,在风中轻唱。
清风从村口吹进来,
带着栀子花的馨香。
只要有这棵树,
作为生命的背景,
心,便会长出碧绿的翅膀,
成为一只鸟,在山野上盘旋,
再也没有任何奢望。
真想筑巢,一辈子在这棵树上。
即使是短短的一天,
也胜过城里一生的时光。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三日
大山里飘出的歌谣
生在草里,结在树上,
自由自在地在空气中流淌。
不需要任何表演,
挥镰割稻,荷锄除草,
就是最古典最优美的舞蹈;
不需要任何表情,
脸上纵横的纹络,
散落点点的夕阳。
是泉水从岩石孔中宛转流出;
是晨风抚摸山林的轻响;
是鸟儿在灌木丛中欢声雀跃;
是野花散出淡淡的芳香。
——大山里飘出的歌谣,
是一个人心里想,
整座大山放声唱。
二〇〇〇年八月七日
布谷鸟的歌
“快插快割,快插快割”,布谷鸟唱着这样的歌,歌声贯穿农夫艰辛的劳作。——题记
浸着鸟鸣的半阙歌声,
在唐诗宋词里开始成长,
和蔓延。一只鸟从里面飞出来,
栖息在春天的枝叶上。
歌声,沿着大地的筋脉滑行,
直抵幼苗顶端的高度。
可以想象鸟声,与幼苗有多么亲热,
以及苗尖与大地日益明显的距离。
火热的歌喉,唤醒,
沉睡了一冬的铁锄。
随着一声原始的吆喝,
农具破土而入,
走进幼苗拔节的内核。
布谷,你在枝繁叶茂的舞台上,
奏响浸着泥土温热的乐曲,
久久回荡在农夫恭听的姿势里。
你饲养过庄稼和土地的歌,
奔跑在,高山和流水,
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
最终被定格为,
乡村朴素的风景。
二〇〇一年五月十日
渡船
乡村的记忆里,渡船,
是一部线状的古书。
搁浅的,是岁月的橹声,
以及号子,平平仄仄的桨影,
斑驳了船夫手上的老茧,
和昏黄的鱼灯。
船歌里的抑扬顿挫,
源自船夫脸上的纹络。
那是船永不迷失的方向,
一段桥,一段日子,
船在河水的流唱里,
翻译哲学,诠释生活。
渡船,走得出河流,
走不出船夫的掌心。
渡船,是乡村的脐带,
紧紧拴着船夫的一生。
二〇〇一年五月十八日
感受你的柔情之后
感受你的柔情之后,
便有一种漂泊的欲念。
隔河而望,暮江里的竹筏,
载一弯浅浅的新月,泊在,
柳影渐暗的脆弱梦城。
河水蜿蜒远去,
从此我知道,我注定要在,
岁月的流程里,走过迟来的雨季。
注定要用折断的篙和破碎的桨,
写下浪漫的履历。
让心的渴求,与山情水意,
在苍茫地对视中,
如醉,如痴。
许多年以后,捡拾记忆时,
你会久久怀念,
那只泊在暮江边的竹筏,
和那曾经溅湿你,
生命之舟的冰凉水意。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日
回乡
心灵,打开你尘封的门,
天堂在前,花瓣绽开芬芳,
在浸满月色的黄昏。
我从遥远的地方,走向你,
开花是纯洁的宁静。
我的热恋与梦想,温柔了,
又一次甜蜜的回乡旅程。
二〇〇二年二月八日
我认识一棵树
我认识一棵树,
它站在山前,山在湖边。
它从不插手俗务,
只是旁观。
我惊讶它的安静,
多年来它始终一声不吭,
一片叶子飘落到湖面,
甚至没有泛起波纹,
我却听见一声惊叫,
成为树的一圈年轮。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老屋里的灯
与你重逢时,
我便已交出灵魂。
我将世界上所有的黑,
藏在体内,
风,不能吹灭我的原罪。
不能示人的私欲,
在顷刻间燃烧成灰。
你将我的哀愁投到地上,
我的身影被你摇曳着,
我毕竟不是透明的水。
你是我双手合十时生出的火焰,
让我身心合一,充满欣慰;
你是我最古老的地址;
我将自己邮寄给你,
沐浴你的温暖之后,
我还得从原路返回。
二〇一四年二月六日
古老的春天
我十岁那年的早春,
有一天明月初升,
村里的人都围坐在打谷场上,
看露天电影。
银幕上,一个肩扛枷锁的受苦人,
正缓步走向刑场。
他的悲伤,他的坚毅,
印在每一张发呆的脸上。
这时,天上正在发生月食,
满地人影渐渐变淡渐渐消失,
受苦的人走到了闸刀下,
我第一次发现了光阴流逝的秘密。
二〇一四年三月六日
牛是神圣的动物
在我的故乡,牛是神圣的动物,
如果它没有失足摔下山崖,
我们就不会有机会吃到牛肉。
有的时候,牛掉进深谷,
很久之后才被人发现,
它就会静静地躺着,慢慢地腐烂。
一头牛腐烂后,
能生出一窝窝牛头蜂。
金色的牛毛变成带毒的刺,
那是牛头蜂的利器。
而它肚子上的褐色花纹,
就是牛生前,
被抽出的一道道鞭痕。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
狗死之后
在我的故乡,狗死之后,
尸体不会被埋葬,
人们把它送到向阳的山坡上。
据说,趁着太阳落山,
它会沿着阳光退缩的的路线,
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家园。
它要照顾所有的反刍动物,
还要巡视主人的瓜田,
它用大门口的一泡尿,
提醒所有人——
它已经死了,而今剩下的,
只是几根枯骨和一腔忠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我的黑色蝴蝶
很多年了,故乡,
都在替我照看着一群精灵,
那是我豢养过的黑色蝴蝶。
在童年的村庄,在少年的孤城,
它们扇动着透明的翅膀。
在春天,浸染了诗意、花香;
在夏天,锻造了体魄、衷肠;
在秋天,铸就了傲骨、正气;
在冬天,学会了叛逆、飞翔。
而我知道,还有一些蝴蝶,
一直跟在我身后,
踩着我的影子,漂泊到异乡,
被一重重山水挽留,
被一簇簇花草羁绊,
在未尽的旅途上,
餐风饮露,化蛹成殇。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往事
红蜻蜓在窗外翩翩起舞,
我在屋里想入非非。
趁我背一首宋词的时候,
她点乱了一池春水。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状态
当城市像监牢一样将我围困,
我就决定像一颗麦粒那样单纯,
像一柄剑那样锐利,
像一只骆驼那样坚忍。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日
我需要一个声音喊我回乡
我需要一个声音喊我回乡。
可以是风吹树林的轻响,
可以是父亲的鼾声,母亲的咳嗽,
也可以是门前竹林里的鸟唱。
这个城市汇聚了两条大江,
却没有一条溪水为我流淌;
街道上长满奇怪的事物,
却找不到五谷杂粮。
此刻我在江边,脖子越伸越长,
渐渐承受不了思想的重量。
身后是人声鼎沸,
灵魂像流浪狗一样迷茫。
其实我只需要三间草房:
窗前有月光,门前能晒太阳。
我是一个儿子,天气转凉时,
我要把父亲种下的稻谷收进谷仓。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